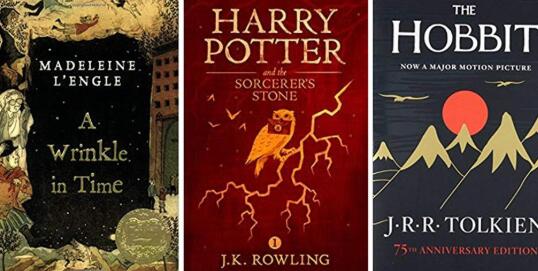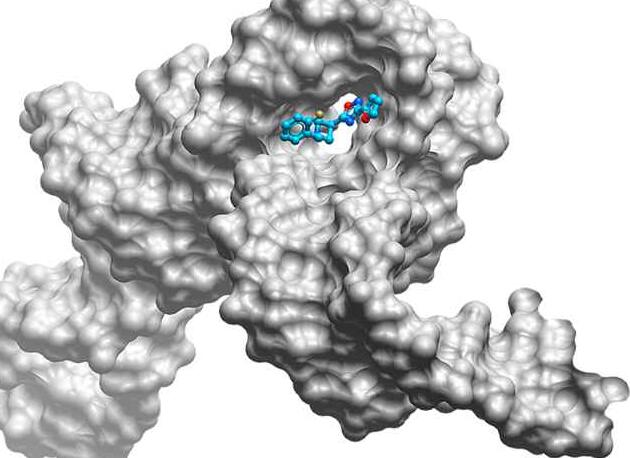《十竹斋笺谱》之凤子
《十竹斋笺谱》之挂角
《十竹斋笺谱》之香雪
十竹斋笺谱笺画
十竹斋笺谱饾版雕版
编者按:《十竹斋笺谱》是明末清初十竹斋主人胡正言采用当时最先进的饾版拱花水印木刻技艺刊刻的一部笺纸笺画总成,系统涵盖了中国文人士大夫生活全景,行为准则、审美规范、道德追求、精神理想尽在其中,所引掌故典籍从《诗经》《尚书》《史记》《汉书》,到唐诗、宋词、元曲以至名人传记、神仙传说,无所不包。南京市依国家图书馆藏郑振铎捐明代初刻版为底本复刻了《十竹斋笺谱》。
自明代万历年间开始,欧洲、日本、美国等地都有爱好者收藏和研究《十竹斋笺谱》。18、19世纪,有大量《十竹斋》作品进入日本,在日本催生了很多热爱中国版画的人士。2019年7月,日本将举办“《十竹斋笺谱》东方文化艺术周”活动,其中《十竹斋笺谱》雕版水印展将展出相关作品一百余件。本刊特刊发范景中教授从艺术史角度研究《十竹斋笺谱》的专文。
一
万历二十年前后,徽州墨商方于鲁和程君房分别出版了《方氏墨谱》和《程氏墨苑》。这两部墨谱虽是兜售隃糜之香的争胜之作,却也都在小小的玄工墨象上“瞻穹窿,浥玄德,经纬变化,无不胪列”。实际上,它们起到了以墨谱在文人书房传播古典知识的作用。那些古典知识当然是文人眼中的普通知识,但这些普通知识能得到当时的名流像王穉登诸人的另眼相看,显然不在墨上的文字,而在那些精美的图像,它们出自丁南羽、吴左干等画家之手,由徽工精刻,本身就是高水平的艺术品。
大约十年后,王圻、王思义父子刊印大型的插图本百科全书《三才图会》,全书共一百零六卷,包括天文四卷,地理十六卷,人物十四卷,时令四卷,宫室四卷,器用十二卷,身体七卷,衣服三卷,人事十卷,仪制八卷,珍宝二卷,文史四卷,鸟兽六卷,草木十二卷。书前冠有四通序言,第一通开篇就是:
天下之道,见于言者,六经尽之矣。见于象者,羲之画,河之图,洛之书,尽之矣。然洪荒之初,文字草昧,自龙图告灵而后,画继之,畴又继之,六经益瞠乎后耳。是图又为吾道开山,宜与六经并传不刊者也。
这位作者是被汤显祖誉为容温而肃、度宽而严、位高不亢、志大弥坚的时任应天(苏州)巡抚周孔教(1548—1613),他把图像的地位看得如此之高,大概不是一己之见,而是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阶层的一种普遍觉醒。这种觉醒大概是由一种对文明的殷忧引起。我们细读《三才图会》的四通序言,它们都表达了一种意见,文字所表达的古典知识在他们眼中不过是普通知识,而图像所再现的知识则不普通,若不珍惜,恐有泯灭的危险。明人构造宇宙的知识体系,集中于皇家编纂的《永乐大典》。但以图像建立一个图文知识融合的有系统的普通知识,用现代美术史的术语说,是要建立一个图像志(ico nography)的知识体系。《三才图会》的出版,标志着这一目标的大规模的实现。然而,《三才图会》也有一个明显的缺陷,由于卷帙过于庞大,它不可能请名家名工精心制作,比起方、程二家的墨谱,艺术水平相形见绌。
二
万历年间,金陵是中国出版业最集中、最发达的地方之一,不仅印刷的书数量大,而且艺术水平也高。三山街和太学前一带是全国书籍的重要销售中心。天启崇祯间有两位活跃于其中的刻书家胡正言和吴发祥,他们俩不知是否来往,但在印刷的技术上肯定互有影响。从情境逻辑的角度出发,他们想必都看过《三才图会》,而《方氏墨谱》《程氏墨苑》那样的书无疑会摆在他们的案头。由于文献缺如,我们了解吴发祥太少。但对胡正言,不仅知道他的生卒年,知道他字曰从,知道他是安徽休宁人,居南京鸡笼山侧,有室名十竹斋,还从《胡曰从书画谱引》得知,他从事印刷之前就制过墨,造过纸:“始为墨,继逃墨而为印,为笺,为绘刻。墨多双脊龙样,印得松雪、子行遗法,笺如云蓝、麦光,尽左伯乌丝栏之妙。”像方、程两家的墨谱,不仅那些图像会让他们印象深刻,那种借墨谱氤氲于文人书房以传播图像知识的策略,也一定震动过他们的心灵。尔时,他们正在研究饾板和拱花的技术,这两种技术代表了中国传统印刷的高峰,他们正决意克服三种困难:
盖拱花饾板之兴,五色缤纷,非不烂然夺目,然一味浓装,求其为浓中之淡,淡中之浓,绝不可得,何也?饾板有三难:画须大雅,又入时眸,为此种第一义;其次则镌忌剽轻,尤嫌痴钝,易失本稿之神;又次则印拘成法,不悟心裁,恐损天然之韵。去其三疵,备乎众美,而后大巧出焉。
为了把书籍做成艺术品,他们全力以赴。程家珏《门外偶录》记述胡正言十竹斋中经常雇有刻工十数人,而不以工匠相待,他们朝夕研讨,十年如一日,以至胡正言和这些良工“十指皆工具也。指肉捺印有别指甲,指尖有别于拇指也。初版尤可见曰从指纹,岂不妙哉!”
有了这样高超的技术,胡正言在结撰起稿《十竹斋书画谱》的过程中,受墨谱的启发,和吴发祥一样,自然想到了笺谱,想到要把笺谱做得比墨谱更棒,让它成为文人苦读疲劳后的一种艺术欣赏,一定魅力无穷,那就像后来李于坚描述的:
时秋清之霁……绿玉沉窗,缥帙散榻,茗香静对间,特出所镌笺谱为玩,一展卷而目艳心赏,信非天孙七襄手曷克办此。
尤其当他们考虑到笺谱在嘉靖、隆庆之前犹制作朴拙,到了万历中期(1595年左右)才稍尚鲜华,而他们正赶上兴盛之际,也许趁势“汇古今之名迹,集艺苑之大成,化旧翻新,穷工极变”,推为极艺,正是良机。于是,吴发祥在天启六年(1626年)先行刊印了《萝轩变古笺谱》,以一百七十余幅精雅版画,分画诗、筠篮、飞白、博物、折赠、琱玉、斗草、杂稿八类,并将飞白和琱玉二类用拱花印制。颜继祖在《小引》中赞美说:“尺幅尽月露风云之态,连篇备禽虫花卉之名,大如楼阁关津,万千难穷其气象,细至盘盂剑佩,毫发倍见其精神。”
甲申之变后的翌年(1645年),胡正言的《十竹斋笺谱》成书,内容较吴发祥的笺谱更为增色,收图近三百幅,分四卷三十三组。卷一收清供八幅、华石八幅、博古八幅、画诗八幅、奇石十幅、隐逸十幅、写生十幅;卷二收龙种九幅、胜览八幅、入林十幅、无华八幅、凤子八幅、折赠八幅、墨友十幅、雅玩八幅、如兰八幅;卷三收孺慕八幅、棣华八幅、应求八幅、闺则八幅、敏学八幅、极修八幅、尚志八幅、伟度八幅、高标八幅;卷四收建义八幅、寿徵八幅、灵瑞八幅、香雪八幅、韵叟八幅、宝素八幅、文佩八幅、杂稿十六幅。
此处不厌其繁地胪列这些画笺的名目,意在与我们前面述及的墨谱和《三才图会》做一比较。显然,它们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有意用图像建立古典的知识体系,尽管这些知识在当时不过是流行于知识界的普通知识。不过,笺谱还有一个重要的指向,就像郑振铎先生所说的:臻彩色木刻画最精至美之境。它上版之前就要求画稿:“是谱也,创稿必追踪虎头、龙眠,与夫仿佛松雪、云林之支节者,而始倩从事。”而付梓开板则是:“镌手亦必刀头具眼,指节通灵。一丝半发,全依削鐻之神;得手应心,曲尽斫轮之妙。乃俾从事。”至于印手:“更有难言,夫杉杙棕肤,考工之所不载;胶清彩液,巧绘之所难施。而若工也,乃能重轻匠意,开生面于涛笺;变化疑神,夺仙标于宰笔。玩兹幻相,允足乱真。”这些语言虽然夸张,有修辞的情念,是文学性的“艺格敷词”,但却指出了从画家、画刻稿的人,到刻工、印工,至少有四道关口,而且还有一位指挥者从中斡旋,缺了哪一项都不可,它是一种作坊的集体创作。正是这种通工易事让《十竹斋笺谱》的幅幅图像“或恬静若夕阳之明水,或疏朗开阔若秋日之晴空,或清丽若云林之拳石小景,或精致细腻若天方建筑之图饰”。尽管从规模上,《十竹斋笺谱》绝不能望《三才图会》之项背,甚至跟《程氏墨苑》也难以比肩,而且在版画的尺幅上也是戋戋小物,然而在品味上,在印制的高妙上,《十竹斋笺谱》则卓拔而上,达到了古典美的高度。而所谓的古典,不仅指艺术的图像,也指所绘的内容。郑振铎先生曾敏感地指出,它“表现现实或不足,而备具古典美之特色”,的确具眼,因为它是以古典美来传播古典知识,从某种角度看,可作为《三才图会》的一个精选版,是一部小型的图像志。
三
《十竹斋笺谱》首先是一件艺术精品,精雅得让人爱不释手。然而正如贺拉斯(Horace)《诗艺》(ArsPoeti ca)告诉我们的,好艺术要autprodessevolunt,autdelectarecus todies(给人教益给人愉悦)。我们现在就谈一谈《十竹斋笺谱》的教益一面,在谈之前,先看一段插曲,在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Christie)的侦探故事中有这么一段:
女凶手出现在克拉里奇(Charidge)举办的上流人士午宴上,她装扮成她的受害者,而受害者的死,她当然尽可能不想让人知道。她不愧是个装蒜老手,所以她的罪恶计划起初一帆风顺,不过,有一点她却疏漏了:要在克拉里奇的宴会上获得成功就需要古典文化的教养。贵宾中有人提到帕里斯的裁判(JudgementofParis),即那个导致了特洛伊战争(TrojanWar)的可悲而未遂的裁决。“什么,巴黎的裁判?”女凶手用玲珑悦耳的音调问道,“我看,巴黎已经不行了。现在牛的是伦敦和纽约。”(引自贡布里希:《理想与偶像》)
女凶手由于没有弄清楚一个典故,一个有教养的人的普通知识,而最终导致罪行的败露。这段插曲出自《埃奇韦尔勋爵之死》(LordEdge wareDies),它用令人难忘的情节让我们不必费神去对普通知识(generalknowledge)下定义:普通知识实际上也是不普通的知识。如果我们翻看《十竹斋笺谱》,除了感到让人爱不释手的愉悦之外,却大都看不懂所谓的“披裘公”或“田荆”那两三个字的简单说明,那么我们可能也会对贯休的“我欲使诸凡鸟雀,尽变为鹡鸰;我欲使诸凡草木,尽变为田荆”(《上留田》),或者对“分离累岁,多萦棣萼之情;相聚一堂,实切荆花之喜”,觉得似懂非懂,这就有割断跟自己的文明联系的危险。而熟悉这种知识的人,在某种场合他们不加思索就能挥笔写出:荆枝擢秀,棣萼生光。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贡布里希把那种源于古典的普通知识领域称为“隐喻之源”(sourcesofmetaphor)。
每种文化都有人们喜用的隐喻之源,它不仅促进了成员之间的交流,也为文明的塑形做出了贡献。在西方,不知道一些古希腊神话,不了解一些《圣经》故事之类的普通知识,就很难进入他们的文化。同样,没有一些像《十竹斋笺谱》所举的“田荆”和“融梨”之类的知识,也很难进入中国的古代文明。如果说,我们已看不懂笺谱中的这些图像,那么可悲的只能是我们自己。古典的文明正在年与时驰,意与岁去,悄然地与我们日行日远。就此而言,我们已然处在与自己祖先文明断裂的边缘。在晚明,《三才图会》和《十竹斋笺谱》之类传播普通知识的书籍是否已预见到这种危险,不妨另做研究。但当今切身感受到的是,我们的古典文明所培育的隐喻之源正在渐渐枯竭。
古典教育强调的是知识的吸收(assimilation),不是知识的获得(ac quisition);不是占有知识,而是化穆沾洽,以成文明,让我们的举止得体,谈吐优雅,超越俊造,如出本能,抵达的是偏爱原始性所谓的“野老吐何力之谈,郊童舍不识之歌”的境地。潘诺夫斯基谈拉丁文的scientia与eru ditio之间的区别说:
scientis,意指一种智力的拥有而非一种智力的过程,可以等同于自然科学;eruditio,意指智力的过程而非智力的拥有,可以等同人文学科。自然科学的理想目标似乎有点像掌握(mastery),而人文学科的理想则似乎有点像智慧(wisdom)。
西方的人文教育与中国的古典教育庶几近之,也是东海西海,心愿攸同,难怪这两种教育,都极力推崇经典。实际上,不正是那些经典创造了普通知识么?不读经典不仅仅使我们的语言粗糙干瘪,表达不出深意和厚重,我们的价值观也会遭到颠覆。《十竹斋笺谱》所画的“邺架”“挂角”,不光是一些普通知识,它们也是阐释人生和人类责任的永恒参照,是我们生活的最有价值的重要的内容。由于我们的文明是书籍和图像造就的文明,这些普通知识不论有多少缺陷和局限,毕竟总是在提醒我们:
在一个世纪中,具有清澈的思想风格和优雅的鉴赏能力的启蒙者,总是少数。留传下来他们的著作,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要感谢古典时代的少数作家,全靠他们,中世纪的人才能从黑暗了五百年以上的迷信和无知的生活中逐渐摆脱出来。
为了克服现代主义者的势力俗气,再没有比古典文学更为需要的了。(爱因斯坦语)
那些古典作品展现的浩瀚,犹如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河灿烂,若出其里,我们应该仰望,应该敬畏,应该学习,而不能拘守一隅,成为托马斯·阿奎纳(ThomasAquinas)所害怕的那种homouniuslibri(只读过一本书的人)。
在晚明,学术气氛的松弛,不少学人感受到了普通知识的衰落。生活在杭州的高濂是位戏曲家、养生家和藏书家,他的不断扩容的活跃的书房自然陶冶了他的志向,他说:“余嗜闲,雅好古。稽古之学,唐虞之训;好古敏求,宣尼之教也。好之稽之,敏以求之,若曲阜之舃,歧阳之鼓,藏剑沦鼎,兑戈和弓,制度法象,先王之精义存焉者也。岂值剔异搜奇,为耳目玩好寄哉!”他说的这些名目也是《十竹斋笺谱》所要稽考和再现的图像。因此,高濂的志向也是胡正言的心声,他们与前述的方程二家的墨谱、王氏父子的《三才图会》汇为一道清流,都为复兴普通知识出了一份力量。
四
《十竹斋笺谱》最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它不是用大段大段的文字,而是用精致高雅的图像去表达普通知识,因而,它为普通知识提供了一部图像志。所谓图像志是美术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一般说来,是对图像所表现的题材或主题进行确定、描述和解说;主要手段是文献考证,它要为图像找到与之匹配的原典,以说明其来源和旨意。这种工作有时容易有时困难,尤其对一幅大型绘画,要确定其题材或主题往往不易,而一旦将其确定并要读解出它的象征和意义时,我们就进入了所谓的图像学。
读者也许会问,《十竹斋笺谱》不过是一些花鸟竹石器物之类的笺谱,有必要费心耗力去寻求其图像志的来源么?正好郑振铎先生有一段评论,间接地涉及这个问题,他为了说明《十竹斋笺谱》的艺术成就,把它和之前出版的《十竹斋书画谱》(约1627年)做了比较:
在技术上,较之《书画谱》似又更进一步。“拱花”之术在《书画谱》里不曾用过,在这里却大量地使用了。《书画谱》的范围很窄,只限于花鸟果木、梅竹兰石,但《笺谱》则范围广大得多,眼界大宽,以至包括了不少的古人韵事嘉言。其表现的方法,则完全推翻了陈陈相因的“据事直写”的死硬的刻法,而运之以精心,施之以巧术,灵活清空,脱尽俗套,却又表达内在的情调和故事的主题,毫不失之虚幻不切。《笺谱》凡四卷:第一卷收“清供”、“华石”、“博古”、“画诗”、“奇石”、“隐逸”、“写生”等,共六十二幅。像“画诗”那样地以画写诗,是《书画谱》里所未曾有的。其中云影波花皆用“拱花”法印出,尤为匠心独运。“隐逸”十种,写古逸士列子、韩康、安期生、黄石公、陆羽诸人,是很成功的写“人物”之作;第二卷收“龙种”、“胜览”、“入林”、“无华”、“凤子”、“折赠”、“墨友”、“雅玩”、“如兰”等,共七十七幅。其中“无华”一套,凡八幅,全用“拱花”之术,初视无物,细看乃知其精。“凤子”八幅是彩色套印的最美艳的种种蝴蝶的飞翔之态;第三卷收“孺慕”、“棣华”、“应求”、“闺则”、“敏学”、“极修”、“尚志”、“伟度”、“高标”等七十二幅,全是人物画却通体不着一个人物,全用象征之法,以一二器物代表全部的故事,如写季札解剑,则只画了一把宝剑,写陈蕃下榻,则只画一榻之类。这是一个创造性的画法,未必要推广,却是一种聪明异常的技巧;第四卷收“建义”、“寿徵”、“灵瑞”、“香雪”、“韵叟”、“宝素”、“文佩”、“杂稿”共六十八幅。“宝素”和“无华”相同,也是以“拱花”术压印出没色的古鼎彝圭璧之类。这类“宝素”、“无华”大约最适宜用于“诗笺”,以其不碍挥毫也。“韵叟”八幅,以简笔法写种种动态的人物,着墨不多,而人物的神韵直跃然纸上,可算是此时最好的人物画之一部分。
这段话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十竹斋笺谱》的艺术,而且也让我们注意到一个问题,这就是它用象征手法,“以一二器物代表全部的故事”。那么,这一二器物究竟代表什么故事?这正是图像志的工作,而这一二器物也恰恰就是图像志中的属像(attribute)。所谓的属像,我们可以把它简单地定义为:人物带着的或伴随人物出现以确定人物身份的符号,例如观世音的杨柳枝或圣彼得的钥匙等等。借助这种符号,比如借助杨柳枝,我们就可以把观世音和以象为属像的普贤菩萨或以狮子为属像的文殊菩萨区别开来。同样,借助钥匙,我们也可以把彼得和以剑为属像的使徒保罗或以十字架为属像的使徒腓力区别开来。
民国年间,鲁迅和郑振铎先生曾合编《北平笺谱》,后郑振铎先生又出版《十竹斋笺谱》,对这一艰巨的工作,郭绍虞先生评价说:“自鲁迅、西谛二氏合编《北平笺谱》,中土之木刻文化赖以不坠,蜚声国外,视同珍籍,自是始辟中国版画之学。此学既建,西谛复加以发展,独力重印《十竹斋笺谱》,虽历尽艰辛,而终底于成。读其序语,情溢于文,感良师益友之助,成旷古无伦之业,踌躇满志,亦差慰其心力之劳悴矣,第惜鲁迅先生不及睹其成耳。”正如郭绍虞先生所评,《北平笺谱》和《十竹斋笺谱》的刊刻实乃“旷古无伦”的事业。
相关推荐
猜您喜欢
- 证券从业考试备考经验「证券从业考试其实不难 附学习建议」
- 邮政银行永州分行「邮政银行发行国债吗」
- 证券分析师分析报告「2020证券分析师胜任能力考试」
- 《黑白漫画古典女神壁纸图片》(韩国漫画免费)(全文在线阅读)
- Mindtree获得Magnet 360
- FACEBOOK CLOCK为2015财年印度收入27%
- Suresh Prabhu推出印度铁路知识门户
- Infosys宣布三个增强的服务产品
- rolta印度Q1FY'16 PAT涨13.1%
- CCI在2-3周内对其对Jaypee探讨的最终决定:ashok chawla.
- TCS赢得了Pegasystems的业务转型奖
- 印度和欧洲需要合作知识产权:Rajiv Aggarwal.
- 在收购Cintel Systems时,8k英里折叠〜2%
- 本季度SERJ解决方案收购的首次收入:Suresh Venkatachari.
- FICCI和BSA为印度的海关官员推出了IPR工具套件
- RIL与Petroleos Mexicanos签署M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