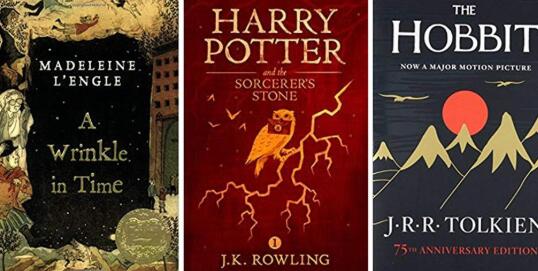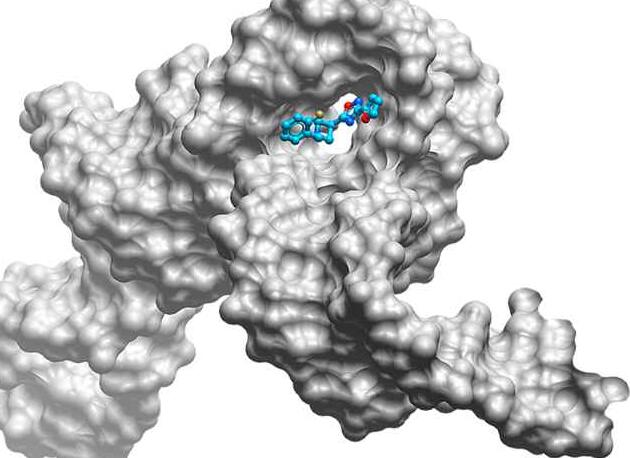谈到政府对教育投入占GDP4%这个话题,我要先谈谈自己的经历。
我于1940年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市嵊州甘霖镇一个贫农家庭。我家在1949年解放前无田无地,是属于赤贫家庭。父母带着我们兄弟姐妹一家7口人,住在连厨房都没有的一间小房子里,有时连饭都吃不饱。即便是那样的环境,当地的求学风气却很浓,无论多穷,大人都让孩子读书,我父母受这种思想的影响,送我到甘霖镇小学读书。我在那里度过了快乐的小学时光。
由于家里贫穷,我小学毕业后辍学在家。两个月后,抵不住读书的诱惑,父母把我送到离家十多里外的一所初级中学继续就读。因交不起住宿费,我和另外两个小同学租了一间农民的小房,每周星期日从家里和学校之间往返二十多里,肩挑油盐柴米到农民小屋,自己做饭,同窗共宿,完成初中学业。
为了补贴家用,也为了供我继续读书,母亲到浙江绍兴一中一位老师家中当保姆。同年,我考入了浙江绍兴一中读书。绍兴一中的第一任校长是蔡元培先生,教导主任是鲁迅先生,它是当时浙江省五所重点中学之一。我在绍兴一中纯正的学风中度过了高中,期间由于家境贫寒,学校给了我甲等助学金,经济上保证我高中毕业。
1952年,国家组建了很多新的大学,当时北京学院路的八大学院:地质学院、矿业学院、石油学院、钢铁学院、农机学院、北京医学院、北京邮电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就是为国家国民经济发展培养专门人才而设立的。
1958年,我参加了高考,为了方便照顾家里和弟弟妹妹,报考了离家较近的3所大学。可是,等我收到千里之外的“北京航空学院录取通知书”时,傻了眼,太远了!路费怎么办?但又很兴奋,北京是首都,能到北京读书多幸运呀!
等我筹足路费赶到北航报到时,开学日期已过了一个星期。那一届,很多像我这样的穷苦子弟被招入北航读书。学校根据家庭贫困情况,制定相应等级助学金,帮助学生完成学业,我还是享受甲等助学金。
从中学到大学,一直都是国家在供我读书。
1978年,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教育的对外开放拉开了序幕。
那时,我已经由一个“吃不饱饭的娃”成长为一名既搞管理又搞教学的双肩挑干部。1980年,经过从严从优选择,我又有幸成为改革开放早期由国家送出国的留学生中的一员,前往英国克兰菲尔德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那时由于国家贫穷,外国人看不起我们,学校认为我们什么都不懂。但是,半年后,由于我们的出色表现,不仅被免除了学费,而且在实验室给我们每人配置办公桌,获得了学校教师的部分待遇。
说到这里,我要回头说一说那个4%了。
其实,4%不是我最早提的。从八届全国政协开始,北京工业大学原校长王浒委员就一直在说这个4%,后来大家拜托我继续关注。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政协全会,就当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的面说:“4%这个目标还没达到,是谁的责任?”李岚清当场表示:这个问题要解决。
2001年两会期间,江泽民总书记到医卫、教育联组会上听讨论。轮到我发言时,我再提4%,同时又加了一个新话题“高校扩招后教学质量下降”。记得江泽民总书记和我对话了20多分钟,这个内容媒体后来都有报道。
2006年,我在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言的主题还是4%。在大会发言中我通过翔实的统计数字说明政府对教育投入没有达到GDP的4%的现状和原因,并向政府呼吁和建议尽快实现4%。有人笑着说,“今年还是4%呀。”当了10年政协委员,我每年的提案和发言都与这个4%有关。
2012年,4%终于落实了。从1993年国家提出规划,4%走了整整20年。有人问我有什么感想,我说,4%的目标是实现了,但贵在坚持,教育是需要持续关注的。
在举国欢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之际,我最想说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的今天。我是新中国教育的直接受益者,全国政协给了我建言资政的平台,使我有幸参政议政,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也充分说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记者 郝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