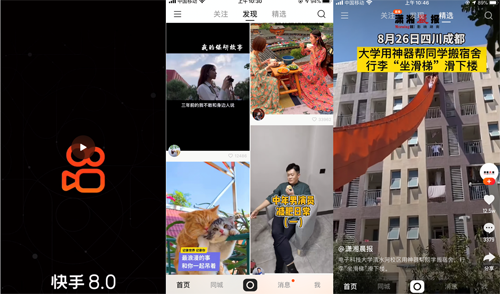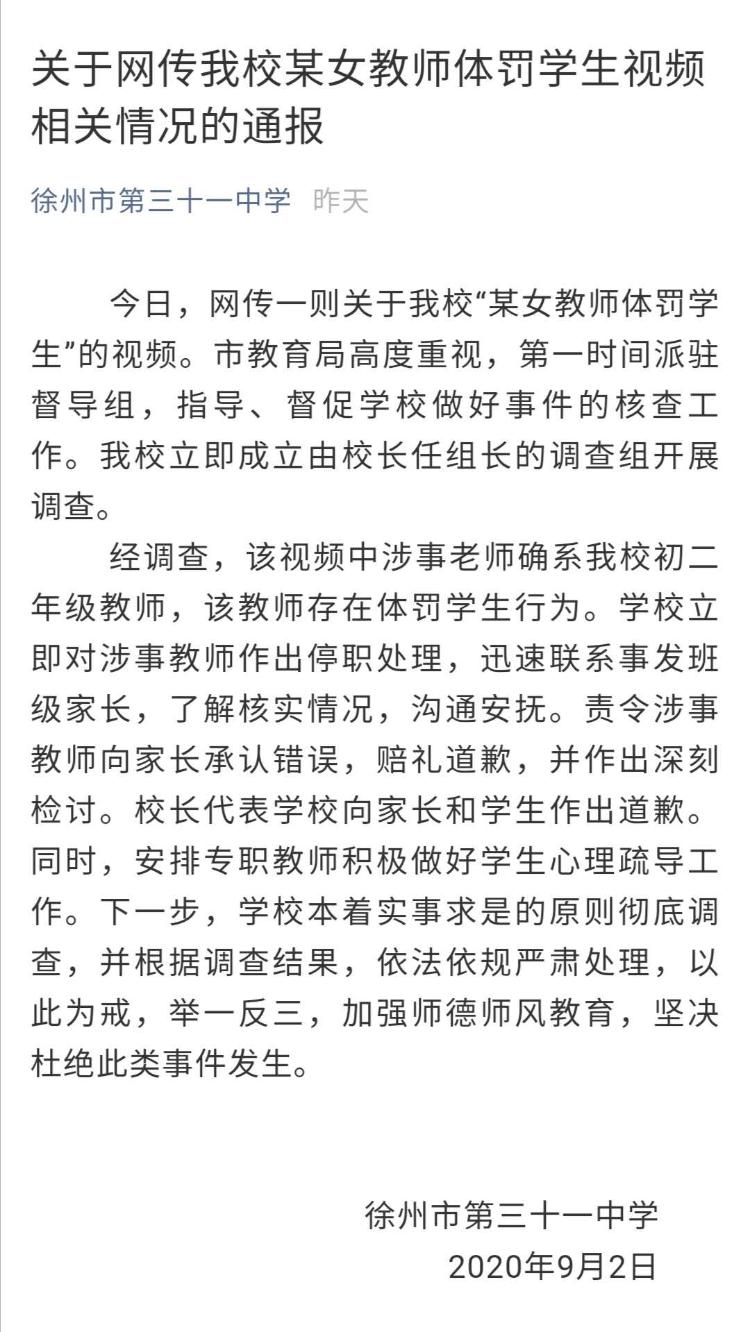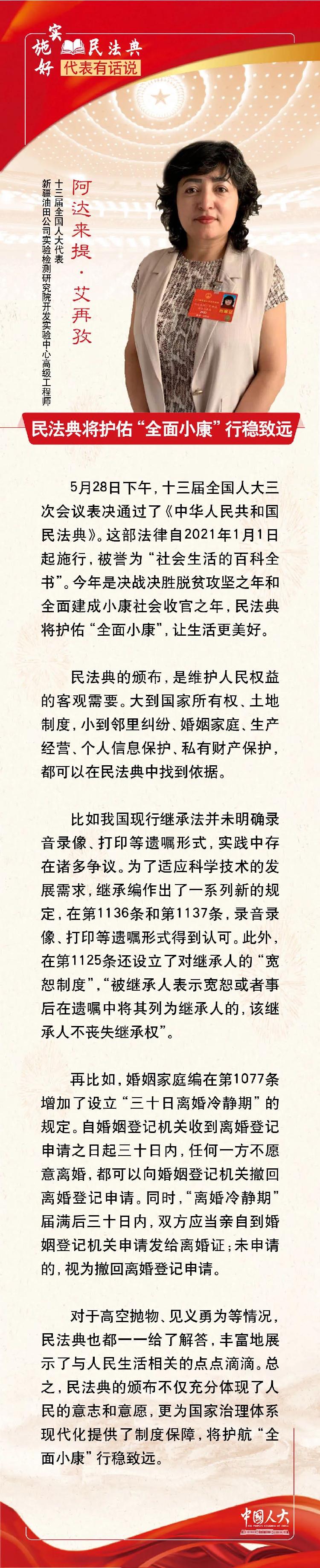化疗是癌症治疗的主要手段之一,但传统的化疗药物不具备肿瘤识别特异性,易误伤正常细胞,引起患者的严重不良反应。分子靶向药物是当前药物设计的重要方向。其中,单克隆抗体药物具有靶向性强、特异性高和严重不良反应发生率低等优点,但其分子量较大、单独治疗的效果有限。抗体偶联药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s,ADC)通过连接子将单克隆抗体与小分子化疗药物偶联在一起,用单抗为化疗药物装上“定位系统”,既拥有单抗的高度靶向性,又充分发挥化疗药物的杀伤力。
6月5日,致力于ADC开发的Iksuda Therapeutics公司研发团队负责人Jenny Thirlway博士在Genetic Engineering&Biotechnology News上发表一篇文章,探讨了ADC开发中涉及有效载荷效力及偶联稳定性的挑战和应对方案。

Jenny Thirlway博士提到,为了提高癌症患者的生存率,目前迫切需要在治疗方法上进行创新,以配合检测和诊断的进步。尽管在许多适应症方面已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最难治疗的实体瘤死亡率并没有显著改善。统计显示,食道癌和肺癌的10年生存率增长不到10%,胰腺癌则没有任何改善。此外,即使在黑色素瘤、乳腺癌、子宫癌等生存率有所提高的癌症中,仍需要副作用更少、更有效的治疗。
ADC是一类新兴的靶向治疗药物,有望提高传统化疗的治疗指标。其由三个部分组成:肿瘤抗原特异性单抗或抗体片段、有效的细胞毒性分子(也称载荷)以及结合前两个部分的连接子。
ADC抗体与癌细胞表面靶抗原结合,接着ADC-靶抗原复合物通过受体介导的内吞作用被内化,最后通过溶酶体打断ADC抗体部分与载荷部分之间的连接使其在细胞内释放有效的细胞毒性载荷(下图)。ADC的作用机制结合了抗体的靶向性和强效细胞毒性制剂,能够更有效和更具选择性地根除癌细胞,同时减少毒副作用。

实现ADC的潜力取决于优化ADC拼图三个“元件”的每个部分。而影响ADC临床成功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抗体的选择、异质性和靶点抗原表达水平、有效载荷效力和作用机制、结合策略以及可切割和不可切割连接子的选择。
此外,为了保证足够广的治疗窗口,结合物应在血浆中稳定,以防止毒素在全身循环中过早释放,而一旦在细胞中释放,细胞毒性有效载荷应足以根除肿瘤。
临床状况
目前,8种ADC已被批准上市:brentuximab vedotin(Adcetris®)、trastuzumab emtansine(Kadcyla®)、inotuzumab ozogamicin(Besponsa®)、gemtuzumab ozogamicin(Mylotarg®)、polatuzumab vedotin(Polivy™)、enfortumab vedotin(Padcev™)、trastuzumab deruxtecan(Enhertu®)和sacituzumab govitecan(Trodelvy®)。
其中Adcetris®、Polivy™和Padcev™通过马来酰亚胺连接子与微管蛋白抑制剂一甲基瑞奥西汀E(monomethyl auristatin E,MMAE)结合,Kadcyla®则通过马来酰亚胺连接子与微管蛋白抑制剂mertansine(DM1)结合。Besponsa®和Mylotarg®通过可酸裂解的连接子与DNA损伤剂calicheamicin结合,Enhertu®通过马来酰亚胺连接子与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deruxtecan结合。
迅速发展的管线反映出ADC技术的临床和商业潜力。2019年,有近90个ADC进入临床试验。
有效载荷开发
一种毒素必须具有足够的效力才能产生疗效。由于对肿瘤的定位不良和内化不足,靶细胞中的有效载荷浓度通常较低。ADC设计中,为获得最佳疗效,细胞毒性分子理想情况下要有亚纳摩尔级效力。毒素还应具有与连接子结合的功能基团,或能够被化学修饰以产生合适的位点,以便在肿瘤细胞中释放。另外,细胞毒素的生产成本应较低。
第一代ADC结合了常见的化疗药物,如甲氨蝶呤、长春花碱和阿霉素,但即使与抗体结合以增加特异性,它们也缺乏足够的效力。例如,尽管cBR96-阿霉素结合物在临床前研究中显示出希望并进展到II期试验,但其疗效不够,这主要归因于阿霉素有效载荷的效力不足。因为据估计,杀死一个细胞需要400–1200万个阿霉素分子。一般每个细胞抗原表达水平在100万份以下,这使达到毒素的临界浓度变得很难。
直到最近,大多数正在开发的ADC都使用了三种类型的毒素:calicheamycins(惠氏/辉瑞)、maytansines(ImmunoGen)和auristatins(SeattleGenetics)。这表明了在ADC领域找到合适的有效载荷非常困难。
Auristatin和maytansine类微管蛋白抑制剂已被广泛应用。Auristatin阻断微管蛋白组装,导致G2/M期细胞周期中止。Maytansine是从非洲灌木Maytenus ovatus中分离出来的一种天然产物,也是一种有效的微管蛋白组装抑制剂。尽管这些结合物已在一些适应症中得到批准,但它们在靶抗原表达较低或对微管蛋白抑制不敏感细胞的适应症中没有那么有效。因此,有效载荷的设计被推动,以解决微管蛋白ADC活性不足的靶标,如结肠癌。
DNA损伤剂是ADC开发过程中使用的另一类主要毒素,它使ADC的效力真正达到亚纳摩尔范围,一些类似物在低至皮摩尔范围内表现出活性。其中包括用于inotuzumab ozogamicin和gemtuzumab ozogamicin的有效载荷calicheamicin(一种抗肿瘤抗生素)以及包括duocarmycins、拓扑异构酶抑制剂、吡咯并苯二氮卓类(PBD)和吲哚啉苯并二氮卓类(IGN)在内的其它有效载荷。效力的增加也使靶向表达密度较低的肿瘤特异性抗原成为可能。由于DNA相互作用的有效载荷在非增殖细胞中很活跃,因此靶点可以扩大到包括肿瘤起始细胞(TIC)。
毒性和稳定性
最近,临床试验数据表明,含有PBD(自然产生的抗肿瘤抗生素,以序列特异性的方式与DNA小沟结合)的ADC在患者中引起了严重的毒性问题。例如,由于不良的安全性,靶向CD33的vadastuximab talirine的III期试验中止。
临床试验的失败导致了有效载荷的使用从交联剂向DNA烷基化剂的转变。如IGN,它具有与PBD相似的效力。交联IGN也有不利的毒性,但DNA烷基化IGN没有表现出长期或延迟的毒性。
在第一代ADC中,偶联稳定性是影响效力的第二个因素,随着开发的有效载荷的增加,这个因素变得更加重要。第一代ADC主要通过抗体结构中自然存在的半胱氨酸和赖氨酸残基结合有效载荷。然而,Mylotarg®中的酸裂解连接子与药物在循环中的非特异性释放有关。
第二代ADC的设计通常使用基于马来酰亚胺的偶联化学与含巯基的蛋白质(如白蛋白)偶联,但这有通过retro-Michael反应去偶联的倾向。
随着该领域的进展,偶联技术具有更高的稳定性。例如,开环马来酰亚胺可稳定对抗去偶联,以及基于乙烯基吡啶的PermaLink®技术不会出现retro-Michael反应。第三代ADC利用位点特异性偶联策略,如工程设计半胱氨酸和非天然氨基酸。
与目前的标准护理化疗相比,ADC在疗效和耐受性方面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益处。新出现的临床前和临床数据将继续指导ADC的进展,这些结果也将有助于有效载荷和偶联策略的不断创新,从而有可能提高在实体瘤中的疗效,并拓宽可治疗的适应症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