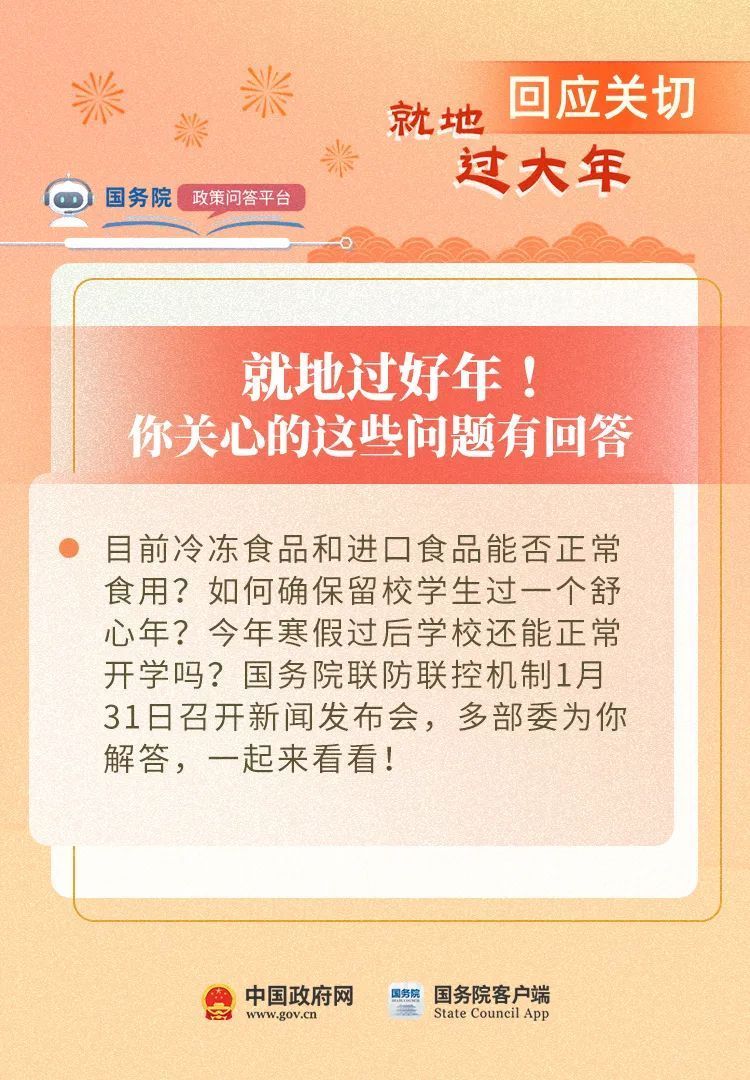中国为什么需要科学新启蒙
文/刘道玉
发于2021.2.1总第983期《中国新闻周刊》
近代自然科学诞生于欧洲绝非偶然,这是由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解放了人的思想,人们从以神为本转到以人为本。
因此,16到17世纪是自然科学从神学中独立出来并迅速得到发展的世纪,它有以下的特征:牛顿力学体系的创立,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发表,哈维的《心血循环论》的提出,伽利略发明了自然科学实验方法等。
19世纪末,美国实用主义盛行,以工程和技术发明而闻名,对基础科学研究并不重视。针对这种情况,美国著名物理学家、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任会长亨利·罗兰在美国科学促进会上作了《为纯科学呼吁》的演讲,被称为是美国科学的“独立宣言”。
他在呼吁中说道:“人们将应用科学与纯科学混为一谈,这并不是罕见之事,特别是在美国的报纸上。为了应用科学,纯科学必须存在。假如我们停止科学的进步,只留意科学的应用,我们很快就退化成中国人那样。多少代人以来,他们都没有什么进步,因为他们只满足于科学的应用,却从来不追问他们所做的事情的原理。这些原理就是构成了纯科学。中国人知道火药的应用已经若干世纪了,如果他们用正确的方法探索其特殊的应用原理,他们就会获得更多的应用的同时发展化学,甚至物理学。因为他们只满足火药爆炸的事实,而没有寻根问底,中国人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的进步……”
罗兰的演讲,可以认为是对美国当时科学界一次科学启蒙。至于对我国科学理论缺失的评论,我个人认为是击中了我国科学落后的要害。其实,中国近当代科学的状况,与当时美国的情况有极为相似的地方,如果中国想要走出科学迷茫的窘境,也必须再进行科学的新启蒙。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次思想启蒙,那就是1915年陈独秀先生在《新青年》上提出了“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即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也是新文化和五四运动向封建势力进攻的两面旗帜。但是五四运动的具体目标达到了,思想启蒙却半途而废,无论科学还是民主都没有在民众中扎根。
科学一词虽然在唐代就有了,但它是泛指科举之学(简称科学)。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日本科学启蒙大师福泽渝吉把Science翻译为科学,康有为等又将其引入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一词才开始使用。由此看来,中国古代并没有科学意识,也没有科学的传统,于是科学理论落后就不是偶然的了。即使在当今,为数不少的科学工作者,仍然分不清科学与技术的区别,甚至“文革”中“理论危险论”的余毒尚存,这就是中国需要进行科学新启蒙的必要性。
那么,科学与技术的区别是什么呢?1911年,梁启超先生在《学与术》一文中精辟地诠释道:“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科学促进会主席彼得·格鲁斯说:“基础科学研究回答这是什么,或者这是为什么;而应用研究回答的是这有什么用。”纵观中国学术界,不仅科学观念薄弱,而且大学与研究机构之间分工不明确,有时互相串位,致使中国科学理论落后。为了使中国科学立于世界先进之林,必须进行科学新启蒙,让一部分科学家,不受晋升职务、评奖的影响,全心投入基础理论研究,这样才能在重大科学理论上有所突破。
(作者曾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武汉大学校长)
《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第5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编辑:陈海峰】
相关推荐
猜您喜欢
- 引资总量再创历史新高 中国吸引外资仍“磁力”十足
- 既要工作,也要诗和远方 看年轻一代的职业选择(中国青年观察②)
- 中国品牌汽车走俏中东(专家解读)
- 中国发布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
- 接种中国疫苗!多国领导人“带头”做了同一个选择
- 中国疾控中心:新冠疫苗接种量累计超2400万剂次
- 央视财经热评丨中国出手稳定国际货运
- 国际机构何以对中国经济投下“信任票”
- 中国连续第12年成马来西亚最大贸易伙伴
- 抢了“欧盟第一”,总理说:我最相信中国疫苗!
- 接种中国疫苗!多国领导人“带头”做了同一个选择
- 中国建成全球最大5G网络:地级以上城市全覆盖
- 中国多地两会热议“双循环” 谋局“十四五”
- 地方华侨权益保护工作上新台阶 中国立法护侨步伐不止
- 百年征程从这里启航——探访中国共产党诞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