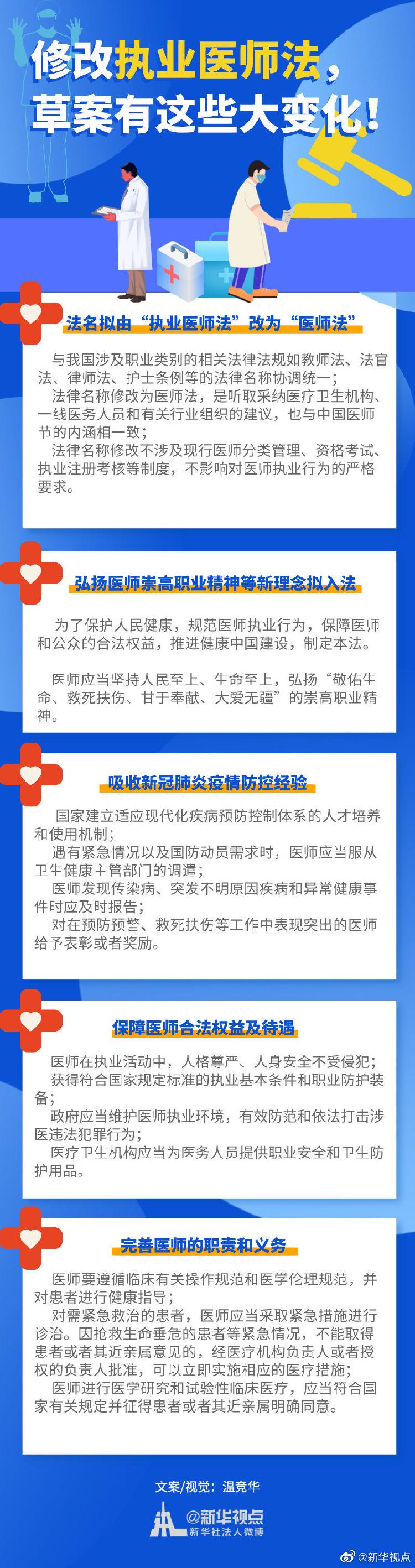中新社北京1月20日电 (记者 张素)这并非人们第一次聚焦“代孕”。但因涉事者郑爽系公众人物,赴美“代孕”所生一子一女被曝光,更涉嫌弃养等“次生犯罪”,引起各方高度关注。
通俗理解的“代孕”即“借腹生子”,属于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一种。“我国法律不允许任何形式的‘代孕’。”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的法律学者唐兴华援引今年起施行的民法典指出,“代孕”活动目前主要在部门规章层面进行了明确规定,如果从法律的层面分析,可以认为“‘代孕合同’不符合中国现行医疗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不符合现行的医学伦理和公序良俗,故‘代孕’交易活动在法律上应作无效评价”。
上海普世万联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周晓颖撰文介绍,目前国内与“代孕”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两个,分别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其中明确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和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仅就这次曝光的个案来说,多位法律人士认为难以断言涉事者因“代孕”而“违法”。原因是中国人前往国外“代孕”规避了国内的法律风险。但正如评论指出,作为中国公民,因为“代孕”在中国被禁止,就钻法律空子,这绝不是遵纪守法。
人们之所以对涉事者如此愤怒,也因为在公开的对话录音中多次出现“堕胎”“弃养”“送养”等言论。有律师表示,是否构成遗弃罪需根据“代孕”生出孩子的国籍确定适用相应国家的法律。
唐兴华对本社记者表示,“代孕”活动不属于受法律保护的民事合法行为,在这个前提下,以“代孕”为目的的上、下游行为,在法律上都应给予否定评价。尽管国内未对因“代孕”产生的弃养行为有专门的、较高层级的立法,但从现行法律逻辑上对该行为的评价必然是否定性的。
事实上,非法代孕在国内屡禁不绝,由此引发的法律争议频现。例如以“代孕”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发现,2018年类似判决有40宗,2019年为81宗,2020年已增长至124宗。
日前一起因“代孕”遭“退单”导致所生孩子无法上户口的案例引发关注。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信金国归纳出司法实践中因“代孕”产生的主要纠纷类型有:孕母分娩后不愿将孩子交给委托“代孕”的夫妻;委托“代孕”的夫妻离婚,在子女的抚养权问题上产生纠纷;“代孕”中委托方的夫死亡,孩子的爷爷奶奶、母亲之间对子女的监护权产生纠纷;“代孕”孩子被弃养;在境外进行“代孕”,能否在国内进行管辖和处理等。
信金国表示,目前的立法仅属于行政性规章制度,只能对组织、操作“代孕”行为的医疗机构进行没收违法所得、吊销机构或者医生执照等行政处罚,如果造成严重后果才能对机构、医师处以“非法行医罪”。“代孕”导致的一系列问题都处于模糊状态,意味着“代孕”在国内面临的风险非常大。
周晓颖也认为,仅有管理办法和原则,但对有需求的家庭来说“法不明文禁止即可为”,成为他们寻求“代孕”的借口。“我国亟需建立和健全相关立法,有法可依才能保障妇女、孩子、家庭的权利。”她说。
诚然,“代孕”涉及生育、法律、伦理、道德等诸多领域,“规范代孕”与“坚决反对”两种声音争论不休。唐兴华表示,是通过立法从根本上杜绝“代孕”,还是通过立法对“代孕”予以规范,在制度设计层面是两种不同逻辑,“如何面对、如何选择,有赖于我们在立法层面作进一步系统研究”。
毫无疑问的是,中国现行法律框架下不支持一切形式的“代孕”,但因非法代孕行为所暴露出法律空子亟待“补缺”。
比如出台一部国家层面的辅助生殖法。由于现行管理办法和原则在实践中执法力度较低,包括不少卫生部门官员在内,多方呼吁将其推动上升到法律层面,加大对“代孕黑产”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
再如围绕非法代孕所生子女的保护。唐兴华表示,尽管国内现行法律对“代孕”不予保护、不予认可,但孩子享有的人格尊严和基本权利不会因是“代孕”所生就与其他方式生育的孩子有丝毫差异,应推动对于“代孕弃养”等重大问题的立法,以契合民法典时代的立法理念。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熊燕撰文建议,在坚持“分娩者为母”的传统规则下,适当考虑已经形成事实的抚养状况,从而设置分娩母亲的失权期限,并严格限制意愿父母的亲子关系否认权,由社会对意愿父母的监护行为实施监督,可能更有利于实现对“代孕”所生儿童的充分保护。(完) 【编辑:张燕玲】
相关推荐
猜您喜欢
- 变异株传播力如何?公众应如何做好应对?权威专家解读
- 中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继续强化“人物同防”
- 中国科协:国际科技共同体应携手推动世界公众科学素质提升
- 检察官章春燕当选CCTV2020年度法治人物
- 2019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揭晓
- 君实生物回复上交所:关于公司的公众号报道内容全面失实
- 君实生物回应自媒体公众号报道:属严重失实报道
- 武汉坚持“人物地”同防 全力严防疫情输入
- 2020年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聚焦促进全球科学抗疫
- 2020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将聚焦全球科学抗疫
- “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抗疫特别人物发布
- “冒名顶替”入刑,是对公众关切的回应
- 中国全国科普日连办16年参与公众逾19亿人次
- 中国已建947所农村中学科技馆 服务公众逾452万人次
- 加强科普宣传提升公众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