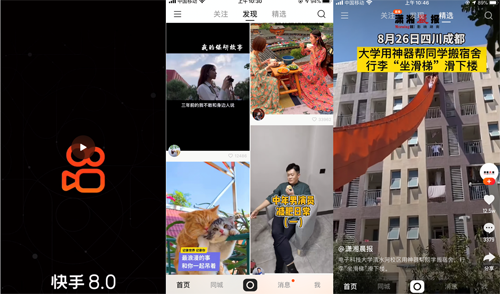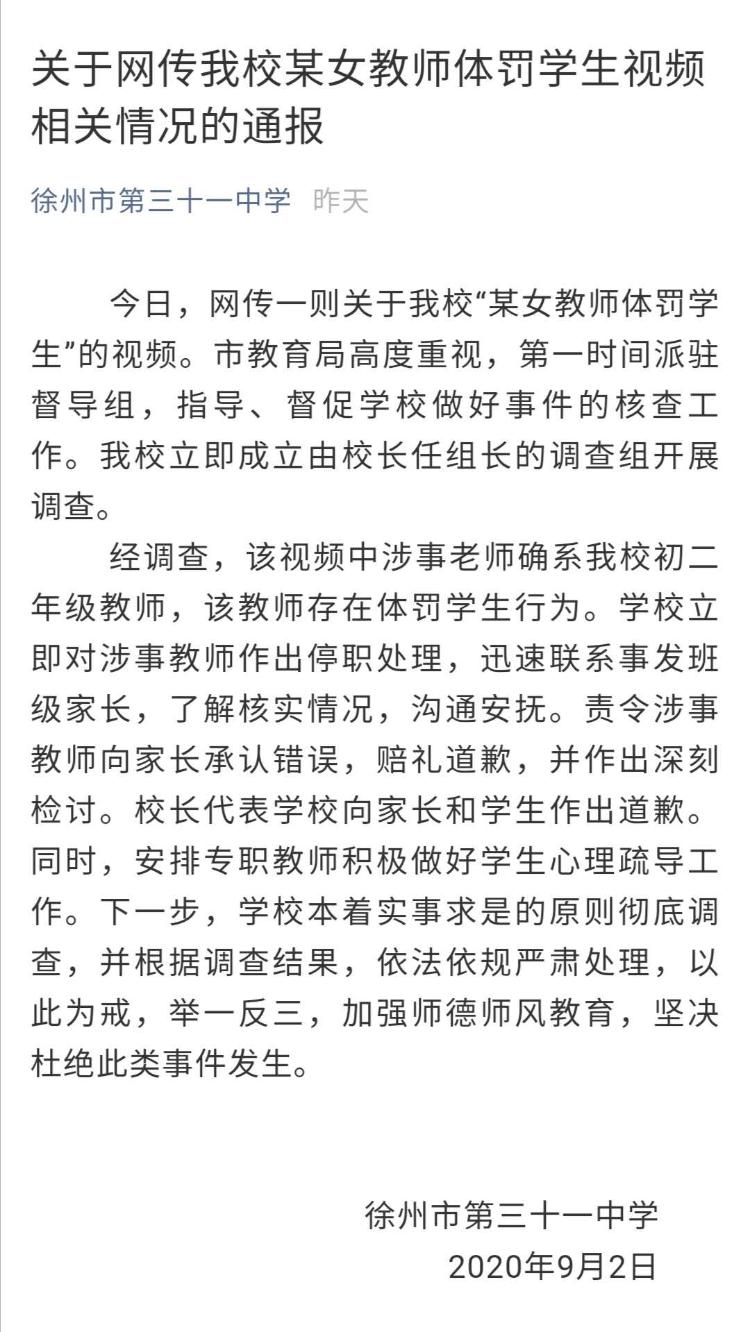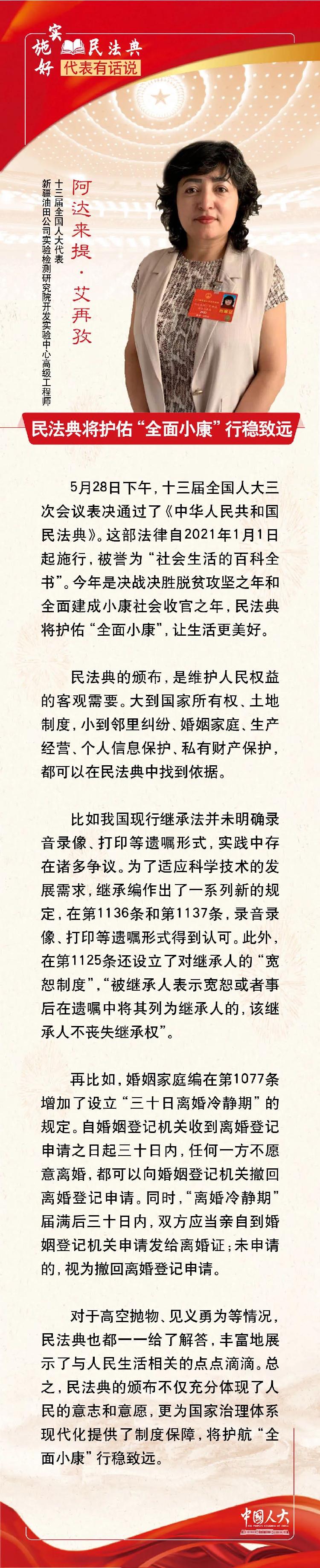政府败诉案背后的北京“民告官”改革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胥大伟
发于2020.7.13总第955期《中国新闻周刊》
2019年,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四中院)的一次判决,对地方政府“敲了警钟”。
赵强在北京市怀柔区庙城镇庙城村承包土地,用于种植果树。因当地棚户区改造项目,果树被强制清除,赵强于是将怀柔区政府告上法庭,请求法院确认清除行为违法。在庭审上,怀柔区政府辩称“不是我干的”,涉案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实施主体和建设主体为银地公司,银地公司委托拆除公司实施项目范围内的拆除工作是民事行为,而非行政行为。
然而北京四中院最终判决怀柔区政府败诉。法院认为怀柔区政府的“授权”行为属于行政委托,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由委托的行政机关承担。政府没有证据证明强制清除行为履行了做出决定、告知权利等法定程序,违反了法定程序。
此案也被业界认为,规制了地方政府采取“授权”等方式和名义规避违法行政责任承担的行为。
事实上,政府机关败诉早已不是“新闻”。近些年来,各地行政诉讼案件增长迅速。以北京四中院为例,2019年,该院受理一审行政案件1749件,是2014年北京市法院受理同类行政案件总数的8倍,作出实体判决的案件中,行政机关的败诉率为12.6%。北京四中院副院长程琥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不能将败诉率与法治政府水平简单“挂钩”,应科学看待政府败诉率。
政府的败诉风险点
2014年12月30日,北京四中院挂牌成立,成为全国首批跨行政区划法院,并实行行政案件的集中管辖。这也是中国探索“民告官”改革的试水之举。
每年一度的司法审查报告,是评估这项改革的一次契机。近日,北京四中院发布了《2019年度行政案件司法审查报告》,这是北京四中院连续第五年发布“民告官”领域相关“白皮书”。
从北京四中院公布的数据来看,2019年,行政机关败诉率相较于2018年上升了1.2个百分点,但近五年的审判数据显示,行政机关败诉率总体呈下降趋势。
程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一年的败诉率变化,既有必然性,也存在一定偶然性。因为判决政府败诉,都是基于案件中政府的行为,这就导致败诉率的变化存在偶然性。程琥举例,地方政府的一个工程,可能就会涉及一批案件,因涉诉案件基数大,一旦大量案件败诉,当年政府的败诉率也会骤增。而类似村务公开的案件,也同样存在着案件量多,一旦大面积败诉,导致政府的败诉率上升的情况。
有着多年审判经验的程琥梳理发现,政府败诉的原因主要有行政机关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行政行为明显不当和履行法定职责不到位等。
行政审判庭庭长陈良刚透露,从北京四中院的相关统计数据来看,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是行政机关败诉的最主要的风险点。以信息公开案件为例,当公民申请公开某个政府信息,政府答复说这个信息不存在,因此没法公开。法院就会要求被告政府机关提供对这个信息进行查找检索的证据,来证明这个信息确实是不存在的。“但有时候政府机关在这方面证据是不充分的,甚至说可能就没有什么有效的证据来证明它进行过检索。”这将产生一个明显的败诉风险点。
政府履责是政府另一个高败诉风险领域。北京四中院以往的案件中,就有一例典型案例。此案的原告曾给当地区政府寄了一封要求信息公开的申请信,信封写明某某区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收,但他错把办公室的“公”写成工人的“工”。区政府以没有专门的信息公开办公室为由,做了退件处理。
在庭审中,区政府答辩称,原告写的机构不存在,因此没法履责。而审案法官分析,原告已经写明了某某区人民政府指向是这个区政府,至于说区政府哪个具体的部门来进行处理,它属于区政府自己内部的一个分工。法官最终认为,原告给政府提出履责申请的事实清楚,政府退件处理属于不履行法定职责,最后承担败诉的责任。
程琥发现,一些案件中,有的领导干部喜欢“乱拍板”,导致决策之后出现大面积的违法。有的行政机关制定的一些规范性文件,与上位法冲突导致败诉。而近年来,地方政府将执法权进一步下放至基层,也增加了政府应诉、败诉的风险。
近期,中国多地法院相继公布了行政案件的司法审查报告。2019年,以陕西省政府为被告的一审行政案件中,政府败诉率为38.60%。云南、青海两省,行政机关败诉率分别为25.60%和21.35%。而2019年,深圳两级法院审结生效的行政诉讼案件中,行政机关败诉率仅为6.2%,呈现出行政机关败诉率的东西部差异。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王敬波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不能绝对化地来看政府的败诉率。地区的案件总量这个“分母”,决定了政府败诉率的升降。不同地区之间的政府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存在差距,也会造成地区间政府败诉率的数值差异。此外,信息公开、房屋征迁等群体性案件,政府败诉比率也相对较高,这也是影响政府败诉率的重要因子。
在王敬波看来,政府的败诉率可以作为评价一个地区法治化水平的“参照物”,但它不是一个绝对化的指标。
告官要见官
2020年4月22日,北京四中院在线公开审理原告孙某某诉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土地权属争议案,房山区区长郭延红作为被告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此案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北京首例区长远程出庭应诉的行政案件。
在北京,区长出庭应诉,并非个案。2019年11月,北京市民叶先生等三人认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送达程序违法,起诉朝阳区政府,要求撤销该决定书,朝阳区区长文献作为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十几天后,北京市西城区市民张先生因对公房承租人变更行为不服,将西城区政府起诉至北京四中院,西城区区长孙硕出庭应诉。
程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近些年来,北京四中院一直在持续推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并实现区政府主要负责人出庭应诉全覆盖,区政府负责人出庭应诉常态化,区政府工作人员出庭率100%,以改变“告官不见官”的局面。
“我们不会和政府机关在个案上进行互动,这会影响案件的公正审判。”北京四中院行政审判庭庭长陈良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明确需要政府负责人出庭时,法院会给被告行政机关发送负责人出庭通知书,并要求被告行政机关提交相应负责人的职务证明材料,确定出庭的部门,坐在相应的席位上,进行开庭程序。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黄永维近日表示,行政纠纷不是普通的法律纠纷,而是“官”民纠纷。实践证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有效纾解了“官”民的对立情绪,实质化解了大量的行政纠纷。受访法官亦表示,领导官员的出庭应诉,可以促进矛盾的解决,对原告而言也是一种姿态和安慰。
今年7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若干问题的规定》施行。这部司法解释对“告官要见官”做了进一步的制度完善,将“行政机关负责人”范围适度扩大。除了正职,新的司法解释将“参与分管被诉行政行为实施工作的副职级别的负责人”写入。
然而现实中,行政机关负责人的出庭率依旧不高。在今年大连、西安等地发布的行政案件“白皮书”中,都点出了行政负责人出庭率过低的问题。以西安为例,2019年一审行政案件行政负责人出庭率仅为4.15%。学者认为,行政负责人出庭率与当地官员素质和法治化水平有关系。
要求政府负责人出庭应诉并非易事。程琥以北京为例,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北京有16个区,区长每天都很忙,很难抽身去应诉某个案件。此外,不少行政机关负责人并非法律“科班出身”,对行政诉讼并不了解,这使得他们对出庭应诉存在胆怯。而区长出庭应诉往往社会关注度高,动辄十几个政府部门负责人在场旁听,加上案件全程网络直播,更加放大了紧张情绪。
北京四中院行政审判庭法官张岩是一名资深行政审判法官。在她的印象中,这些年,北京的区长们出庭应诉变化巨大。从一开始区长只参与案件最后的陈述,到如今,从举证质证到辩论再到最后陈述,都全程参与。
一位北京的区长还曾对张岩表示,他希望出庭应诉一个败诉风险高的案件。区长出庭应诉不再是一个宣传噱头或政绩加分项,而是把行政诉讼作为一面镜子,去考察基层职能部门依法行政的水平。
点穴疗法
“民告官”案中,有一类现象让法官颇为头疼,即行政机关应诉准备不到位。
陈良刚说,一些案件中,政府机关往往只提供一份证据材料,“而每个案件都应该至少提供两份,因为法院要留存,还要给对方当事人一份。”还有的政府应诉人员提交证据材料时,常会忽略一些重要证据材料。
张岩发现,一些行政案件的庭审中,应诉的政府工作人员虽然比较了解自己的工作,但常常“听不懂法官在问什么”。这使得整个庭审过程中出现这样的一幕:应诉被告觉得“一肚子话法官不问”,而法官觉得“我问你的话你怎么就听不懂?”
行政案件的应诉,政府机关往往会采用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加律师或代理人的模式。但有的委托代理人对案件事实缺乏基本了解,在法庭上陷入被动;政府部门应诉人员与代理人之间常常出现沟通不足的情况,使得他们往往怕出庭时讲错话,而选择“出庭不应声、应诉不应答”。
最近出台的最高院司法解释,为避免出现“出庭不应声、应诉不应答”现象,作出了制度安排,其中明确“出庭负责人应当对涉诉事项具有一定程度的决定权限”,要求“负责人应当就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发表意见”。
王敬波认为,行政机关负责人不是专业的律师或者法务人员,让他们在庭上“唇枪舌剑”并不符合实际,“行政案件如何能够更好的解决,既要考虑到原告一方的合法诉求,也需要能够符合行政上的一些规则,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做了探索。”
程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北京四中院与各区政府之间一直在进行良性的“府院互动”。张岩将这种“互动”,称之为点穴疗法。北京四中院对行政机关败诉案件全部制发了司法建议书。行政案件不能“一判了之”,法官们希望通过司法建议书告诉政府为什么败诉,错在哪。
多位受访的法官认为,每一个败诉案件对政府都是一个触动,败诉意味着政府的行为被画了一个“叉”,是一个否定性评价。而政府败诉背后的司法监督,将进一步倒逼政府依法行政。
提高行政诉讼案件审判的独立性,加强对政府的司法监督,是这一轮改革的初衷。程琥认为,地方法院的“人、财、物”由当地政府负责保障,当地法院又来“审”当地政府,这就容易导致出现地方保护和行政干预。跨行政区划法院的设立和行政案件的跨区域集中管辖,就是旨在打破司法管辖区和行政管理区的高度重合所诱发的行政诉讼“立案难”“审判难”和“执行难”的制度性窠臼。
北京四中院主要管辖以区政府为被告的一审行政案件。相比于同样是跨行政区划的北京其他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四中院并不下辖基层法院。程琥认为,这一制度设计使得北京四中院独立审判的色彩更浓,“消弭了地方政府通过基层法院影响上诉法院的可能性”。
目前,中国只有上海市三中院和北京市四中院两家跨行政区划法院。王敬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跨行政区划法院是一个改革的探索,但现在改革并没有再往前推进。
现阶段各地行政案件审判体制改革,形式多样,效果不一。王敬波认为,跨行政区划法院相关改革应继续向前推进。多位专家建议,下一步的改革路径应考虑行政法院的设置,以解决法院的专业化和相对独立性的问题。
(文中赵强、朱斌为化名)
《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25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编辑:苏亦瑜】
相关推荐
猜您喜欢
- 北京开展有限空间专项执法检查 持续至9月11日
- 二战以来首次!CBO:美国政府债务明年将超过经济规模
- 【聚焦服贸会】北京成全球服务业发展领先城市
- 北京边检为复工复产出入境中外人员等提供“零等待”绿色通道
- 北京对入境特殊旅客根据医学筛查结果实行分类管理
- 北京:对入境人员集中观察14天并进行两次核酸检测
- 北京边检:利用大数据提供防疫精准预警
- 北京对直航国际航班开展全流程健康管理 抵京人员集中医学观察14天
- 2020年服贸会将在北京举办 服务贸易添彩百姓生活
- 北京首钢园区:参与冬奥筹办 着力转型发展
- “北京野生动物园游客疑似给动物喂口罩” ?警方:非故意
- 北京野生动物园游客喂动物吃口罩?动物园回应仍在调查中
- 北京自贸区创新服务中心预计11月投入使用 面向全球招商
- 广西民营经济发展合作会议在北京举办
- 北京将实施重症医学计划 提升突发应急事件救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