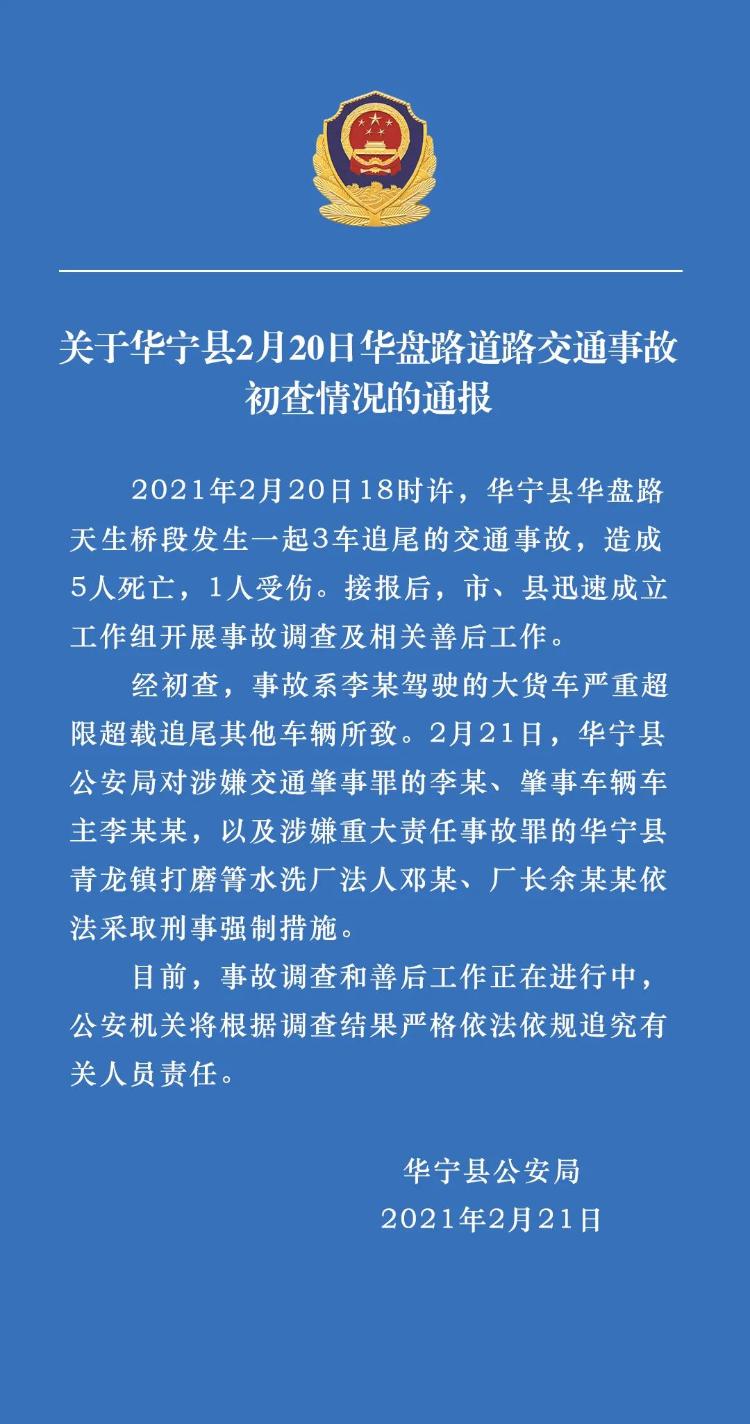网络空间不容犯罪藏身
相貌普通的黎一在“黑客”界是“大师级”的存在。在他眼里,一般的专业工程师与他“过招”无一不似“菜鸟”般被“秒杀”。
三年前,黎一在同伙温迪、袁鹏的协助下,利用上海一家理财公司网络系统存在的漏洞,先后从该公司理财平台窃取5000多万元。2020年6月18日,法院以盗窃罪作出一审判决,黎一、温迪均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记者从最高检获悉,检察机关近年来办理的网络犯罪案件以年均40%的速度攀升,2020年达到了54%。尤其是在战疫期间,检察机关办理的诈骗犯罪案件有三分之一是利用网络实施的。
专家分析,新型网络犯罪正通过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大数据等新技术被实施于各个环节,已经形成“黑灰产业链”和犯罪利益联合体,与其他违法犯罪活动分工合作、相互交织,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安全稳定。
新型网络犯罪特点:作案手段升级,分工日益细化
最高检网络犯罪研究中心主任谢鹏程告诉记者,新型网络犯罪与传统网络犯罪不同的是,这类犯罪呈现出明显的集团化、产业化、智能化状态,表现出跨部门、跨行业色彩,形成了盘根错节的网络犯罪黑色产业链。
北京市一位检察官告诉记者,在新型网络犯罪中,作案手段高度技术化且不断升级是明显特征,如“爬虫”“嗅探”“逻辑炸弹”等新型网络犯罪层出不穷。一些犯罪分子利用“嗅探”设备,远程劫持相同基站下活跃用户的手机号及短信内容,后利用实名制手机号与身份信息的关联性,进一步查询到被劫持手机号对应的身份证号,再通过“手机号(或身份证号)+验证短信”方式登录被害人注册过的一些移动支付平台,获取被害人的银行卡号,以网络游戏充值等方式窃取被害人钱款。这种新兴犯罪,使得犯罪分子可在被害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远程操控被害人的移动支付账户。
同时,新型网络犯罪的另一个特征是“分工日益细化”。在黎一侵入某理财平台计算机系统盗窃巨额资金一案中,黎一、温迪等人就有详细的分工计划。黎一负责寻找“软柿子”(目标),温迪负责筹备银行卡和设备器材,袁鹏负责物色持卡取现人员,且相互之间单线联系,多数互不认识,整个作案过程显然就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台本。
一位检察官告诉记者,较之于传统网络犯罪,新型网络犯罪的产业链条特征明显,产业链的上中下游犯罪分工明确。产业链上游提供技术工具,制作木马病毒,通过网页、邮件等形式“挂马”,诱导用户访问下载并在用户的电脑中种植木马软件,以此来获取用户电脑中的信息或者直接控制用户的电脑。产业链中游将获取的用户账号、密码等信息通过数据平台清洗后既可以用来盗取财产,也可以以用户信息为对象直接转卖获利,而其控制的“僵尸网络”在发动网络攻击时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产业链的下游则以盗窃、诈骗等形式将获取的数据变现。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惩治手段必须跟上
作为惩治网络犯罪的重要力量,最高检将打击治理网络犯罪作为重点工作,先后开展了多次有影响的行动。
针对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严重危害网络安全犯罪持续多发高发的情况,检察机关积极参与“断卡”“打击治理跨境赌博”等专项行动。“断卡”专项行动以来,依法严厉打击非法买卖电话卡、银行卡的人员,特别是重点打击专门从事非法收购、贩卖“两卡”的人员以及与之内外勾结的其他人员,共起诉8000多人;会同公安机关,深挖诈骗犯罪线索,共起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2.3万多人;针对假借创新名义在网络上实施的金融犯罪,最高检会同公安部督办重点案件,有力防范金融风险。
为系统性推进互联网治理,2020年4月,最高检还成立了由12个内设部门参加的惩治网络犯罪、维护网络安全研究指导组(下称“研究指导组”),并在最高检检察理论研究所成立网络犯罪研究中心,将这项工作作为一项重点任务谋划部署,推动形成惩治网络犯罪的检察合力。同时,最高检还出台了《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规定》等规范性文件,积极推动行业监管,加强源头治理。
记者了解到,“研究指导组”成立后,最高检汇集各方力量,加强统筹指导,在惩治网络犯罪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在疫情防控期间,最高检积极指导地方加强对涉疫网络诈骗、制售假冒伪劣防疫用品、哄抬物价等犯罪打击力度,释放出依法严惩的强烈信号、有力维护了防疫秩序和社会稳定。
同时,最高检还于2020年4月中旬召开了“严厉打击网络犯罪,共同防控网络风险”新闻发布会,发布检察机关打击网络犯罪指导性案例,针对手段不断翻新、危害越发严重的新型网络犯罪,表明了“网络空间不容犯罪藏身”的检察立场。
2020年“6·26”国际禁毒日前夕,最高检又发布了“强化法律监督 推进毒品犯罪检察治理”典型案例,专门介绍当前涉网毒品犯罪最新态势,突出阐释了利用互联网实施毒品犯罪案件情况,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
2020年11月,最高检围绕网络黑灰产业链条整治、App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问题,向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出“六号检察建议”,提出治理建议,旨在加强网络监督执法,共同推进网络综合治理。
此外,最高检还发布了一批依法严惩网络犯罪的典型案例,其中包括办理“杀猪盘”式网络诈骗,加强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办理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公益诉讼案件等。
有统计显示,2019年1月至2020年11月,检察机关共起诉网络犯罪案件5万余件14万余人,共起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非法利用信息网络、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等案件1.1万余件2.7万余人。
办案难点通过改革创新逐步破解
一年来,打击新型网络犯罪成绩明显,但办案现实也提出诸多挑战。由于网络犯罪具有“非接触式”特性,特别是新型网络犯罪的许多形态都是首次出现,这在很大程度上给侦查、取证以及认定带来难度。检察机关办案人员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前办理新型网络犯罪还有不少难点需要破解。
首先,电子证据提取难问题需要破解。司法实践中,由于电子证据海量、分布广,收集难度很大,侦查机关囿于技术水平限制、缺乏应对新型网络犯罪的经验以及对犯罪的预判不足,导致对电子证据的取证不够及时精准。
其次,法律认定难问题需要破解。由于新型网络犯罪在方式和手段上往往都是以前没见过的花样,且在司法实践中又缺少例证可循,给司法机关适用法律准确定性带来极大挑战。如“薅羊毛”“恶意刷单”“反向刷单”等行为能否以破坏生产经营罪认定、网络直播平台淫秽表演能否认定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深度链接是否侵犯著作权等问题在实践中意见不一。
第三,跨区域办案协作难的问题需要破解。虽然法律赋予了网络犯罪广泛的管辖权,但实践中还存在分散管辖、各管一段、协作不够顺畅等情况。
第四,国际司法协作机制还不够顺畅的问题需要破解。因为新型网络犯罪有非常明显的跨境特征,犯罪人员跨境流动、网络资源跨境使用、犯罪行为跨境实施,这些都对国际司法协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专家认为,“魔”“道”斗法,关键是见招拆招。对此,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2020年在最高检网络犯罪研讨会上建议增设利用计算机妨害业务犯罪的相关条款。他认为,有必要增设单独罪名,精准打击网络刷单炒信、在系统外干扰监测数据采样、擅自删除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等形形色色利用信息网络妨害业务的行为。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品新认为,要加大机制创新,推动建立基于资金大数据、企业工商大数据、网络账号注册大数据等可信数据库的查询与出证机制,建设全国办理涉众型网络犯罪案件的电子化证据共享机制,建立异地办理、跨境取证的高效协助机制。他建议最高检设立检察机关大数据证据实验室,为全国办案提供关于海量资金数据分析、海量物流数据分析、海量发票数据、海量轨迹数据及相关检验报告、鉴定意见审查的协助。
而对专门从事办案的人员来说,他们更多的是希望加强操作性建设。北京一名检察官希望对利用“爬虫”、VPN等新型技术手段侵权犯罪的法律边界进行明确。上海一位检察官希望完善专业化办案机制,发挥“捕诉一体”先发优势。还有的办案人员希望重新解读共同犯罪的行为共同说,并对内涵不清的一些罪名进行解读。
不少办案人员认为,“魔”“道”斗法,人才和装备特别重要。他们希望加强人才培养,用好系统内有计算机、法学双重背景的人员,盘活用好现有的检察技术人才;加强装备建设,配备先进“武器”,适应办案需要。 【编辑:王禹】
相关推荐
猜您喜欢
- 治不好网络霸凌是文明之殇
- 中国空间站首批航天员乘组已进入强化冲刺训练阶段
- 中国空间站首批航天员乘组正着重开展出舱活动等训练
- 漫评 | “末梢网络”激活社区治理新活力
- 拓展网络时代的关系理论
- 3D打印在三维空间重塑药品“灵魂”
- 空间站、风云卫星、长六甲火箭首飞……上海航天今年“好戏连台”
- 网络黑灰产为网络犯罪持续“输血供粮” 中国最高检强调“打财断血”
- 最高检:2019年以来起诉网络犯罪案件5万余件14万余人
- 最高检:办理网络犯罪案件应当把追赃挽损贯穿始终
- 中科院成立载人空间站工程空间应用系统核心舱任务试验队
- 长三甲系列火箭今年发射预计超10次 多型火箭联手开启空间站建设
- 空间站开建、探火、发射次数40+……2021中国航天有看头
- 中国空间站任务试验队出征 拟于今年春季发射空间站核心舱
- 2020年全国受理网络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1.63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