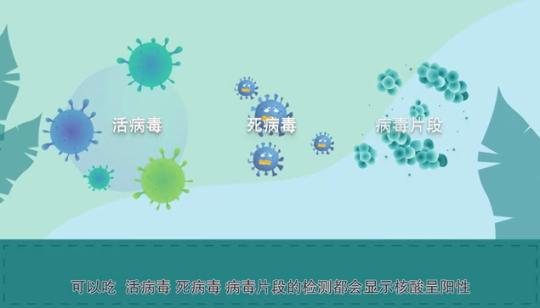用脚投票击中乡村教育发展“软肋”
“硬件”“软件”没有齐头并进
结束了在西北某农村初中为期1年的支教后,有近20年教龄的李明(化名)既高兴,又有些遗憾。
李明曾在这所乡村中学工作过6年。2009年调任时,该校有292名学生,29位教师,但办学环境简陋,只有几排平房,学生还在睡大通铺。
后来,李明听说,学校搬迁了新址,硬件条件大幅改善。2019年,他因职称评定的硬性要求,重返学校支教。李明欣喜地发现,该校有了5层教学楼,有了标准化运动场,电脑室、实验室等功能室配备齐全,宿舍、食堂焕然一新。
这不是“样板工程”。来自教育部的数据显示,在“十三五”期间,中央、地方共投入资金5426亿元,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全国有10.8万所学校从中受益,20万名建档立卡辍学学生动态清零。
当下,在不少农村地区,“最好最美的建筑是学校”已成常态。很多乡村教师都和李明一样,以“学校环境好了”“教师能力强了”“学生全面发展见实效”概述自己感受到的变化。
但是,在支教期间,李明还是留下些许遗憾——刚开学时,他定下计划,要让初三年级73名学生中的50人考上高中,一个学期后,他意识到相当一部分在读学生基础薄弱,就将目标打了“对折”,但最终,考分超过县一中录取线的还不到20人。
遭遇此次“滑铁卢”,李明分析,原因在于校内师生人数各减少了1/3,且流失的均为“精锐部队”。“学校的‘软件’并没有随着‘硬件’齐头并进”。
近段时间,在采访了西部十来所乡村学校后,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发现李明提及的现象并非个案——一些农村学校硬件设施不比城市学校的差,但城乡教学质量差距却越来越大。
师生“用脚投票”击中农村教育这一发展“软肋”。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义务教育城镇化率从2009年的51.04%快速攀升至2017年的76.48%,比当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高17.96个百分点。
部分农村学校教师、学生的“出走”与数据遥相呼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西部乡镇中学的校长告诉记者,其所在的学校,学生从1600多人减少到900多人;西部某乡村小学的一位教师告诉记者,2020年9月,她从一所村小调到乡上的中心小学,因为原本工作的学校只剩了二、四、五、六4个年级的9名学生。同期,该乡另一所村小直接被撤并,剩下的3名学生到中心小学寄宿就读。
学生少了,教师队伍随之出现一些新特征。这位西部乡镇中学的校长总结:过去是教师短缺,现在是教师满编,但全校88名教职工中,50岁以上的有近50人,教师队伍老龄化严重。
据他了解,在西部一些编制有空缺的学校,人员相对也不太稳定。除却留守的本地老教师,年轻教师大多是新分配的外地大学生,伴随其结婚、生子,岗位流动较为普遍。而在云南师范大学教授王艳玲参与的一项面向云南省30个县10356位乡村教师的调查中,也有近80%的受访者流露出流动(调动)及流失(改行)意愿;30岁以下青年教师的流动及流失意愿最为强烈。
“就像下棋没有好棋子”
农村学校师生流向城镇,从一方面来说,是城市化进程加速出现的必然选择。
在一所建在黄河岸边的乡村中学里,记者获悉,近5年内,该校的学生从500多人减少到100多人。校长分析,这与当地产业结构的变迁息息相关。
过去,该乡百姓以种枣为生,此后,因劳务产业投入少、见效快,他们选择乘船往返,在附近的城镇打零工。但近些年,黄河汛期变长了,每年有100多天,横渡的船只不开放,交通成本增加,村民往来不方便,收入骤减,索性举家搬迁,外出谋生。
从另一方面来说,农村学生流向乡镇的背后,是农村家庭平均收入的增加。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中国经济“成绩单”显示,当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7131元,与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差距继续缩小。
“荷包硬起来”的一些农村家长,有底气也有能力更重视教育。
一位西部中学生给记者算过一账:她和妹妹在县城读书,两人在校外租住,每年要付3000多元的房租,生活成本也比村里高。但父母常说,只要她们好好念书,有个好前程,花多少钱都不怕。
此外,城区就读的孩子有机会上各种课外班,“就像吃饭一样,不仅能吃饱,还能吃精、吃好,我们也想让孩子有更多选择”。一位农村家长说。
甘肃一位基层教师说,进城读书一度成为“时尚”,“家长一个接一个,一个看一个”。但当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用脚投票时,首先受到冲击的肯定是一些农村学校。
比如,农村学校班级变小,老师的教学任务看似减轻了,但也有人直言,教学难度上升了。一位小学教师反映,她所在的教学点,低年级老师要包班,虽然她只带5名学生,但各科目从导入、讲授新课到巩固练习一个教学环节都不能少。另外,农村孩子知识面较窄、参与课堂活动的能力有限,她在师范学到的专业知识很难落到实处。
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也日益凸显。一位校长提供了一组数字——在一所仅剩9名学生的村小中,有7名学生出自单亲家庭。因父母教育缺失、亲情缺位,他们会在学业、人际沟通、社会适应中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让老师“操更多的心”。
教学上,更是较难培育出“拔尖”的学生,对此,一位老师无奈地比喻:“就像下棋没有好棋子。”有少量老师的积极性因此受到打击。以西部某县为例,2020年,当地一中(县城中学)与二中(乡村中学)的中考录取分数线有60多分的差距,而在高考时,一中一本上线总人数超过350人,二中则不到10人。
差距之大,让乡村教师对自己子女的教育问题忧心忡忡。一位乡一级教育管理中心的主任告诉记者,每次有教师申请调动时,他都会找对方的亲戚朋友轮番动员,但老师们只要说一句话,就能让人哑口无言——农民的孩子都进城念书了,我们的孩子就要留在乡下吗?
“进城的孩子未必都有进步”
“流动的意义在于促进组织血液循环。”宁夏师范学院的薛正斌教授说。
从乡村到城市,14岁的丁丽娜(化名)就在流动中找到了“前行的路”。去年,她转学至县城中学,原本落后的英语成绩突飞猛进,人也变得自信起来,还被推选为班干部。
在外打工的父母察觉到了女儿的变化,妈妈便不再外出,一心照顾女儿的生活。她说,自己吃了没文化的亏,想要孩子争点气。
与此同时,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被纳入不少城市教育发展规划。教育部统计,“十三五”期间,有85.3%的随迁子女进入公办学校就读或享受政府购买学位。
在与父母朝夕相处的过程中,这部分进城的孩子留下了温情回忆。一位来自西海固地区、当过教师的诗人曾以《打工子女》为题,写下这样的句子:“作业本上的一排排对勾/像一把把锋利的镰刀/映在父母眼里/却是一片丰收的景象。”
然而,无序的流动也可能造成不良循环,甚至“堵塞”。
据薛正斌观察,此前,乡村教师无序“流动”到城市,不仅加大了地区、城乡之间教师资源的差距,老师本人或许也会因面对群体不同、教学任务不同以及受定势思维和个人习惯的影响,对新环境产生不适。
农村学生进城同样面临“水土不服”。甘肃某乡镇中学教师张浩直言,“每个人未必都有进步、都学有所成、都如愿以偿。”
张浩对其所在乡镇307名进城学生进行初步调查,分析后得出以下结论:将近40%的学生达到了家长的预期愿望;将近20%的学生进城后学习成绩下滑,思想消沉、堕落,成了家长的沉重负担;还有近5%的学生回流到了原农村学校。
农村生源不断流向城市, 也让城镇教师压力备增。甘肃一所县城教师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学校从6个班扩展到了16个班。学生多,老师就很难兼顾到每个人的所思所想,一些农村孩子容易在学校被“边缘化”,或因学习压力过大,产生一些心理问题。
一位县中教师则举例,班上有一名女孩住校期间网恋,每天打电话,影响了舍友的休息。双方争执时,女孩动手打了同宿舍的同学。按照校规,他告诉这名同学,如若再犯错误,她会被勒令搬出宿舍。不料,学生直接“威胁”他,要将“学校不让学生住宿”的消息发到网上去,“把事情闹大”。
另外,由于部分家庭管理的缺失或不到位,加上孩子们年龄小、自我控制能力差,一些农村孩子极容易被外面的各种因素干扰或诱惑。
这位老师告诉记者,有1名同学每学期至少会请1个月的病假,他提出去探望,但孩子一直不告诉他居住地址,辗转联系到孩子在外打工的父母后,对方也对孩子的情况不甚了解。高二时,这名孩子主动辍学,后续发展如何,他一无所知。
“在地化”重新振兴农村教育
“用脚投票”不是新现象,涉及人数众多,结果有好有坏,但不可否认的是,农村教育依旧面广量大,是中国基础教育的大头,承载着改变个人命运,推动社会发展的重任。尤其伴随“乡村振兴”全面推进,教育作为新发展格局中的优先要素,也要步入全面振兴阶段。
连续多年,已有更多政策向农村学校倾斜。西北某县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县特岗教师招考名额全部分配给农村基层学校;不足100人的学校按照100人下拨经费;城区学校富余学科教师到农村学校支教帮教,改善农村学校教师学科性短缺问题;大力推进互联网+教育模式,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在工资待遇上,乡村教师也颇受优待。以宁夏为例,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校教师每月最高可以拿到1100元的各类补贴。自愿到乡村学校支教的退休特级教师、高级教师,每人每年有两万元的补助。
但要真正解决农村教育新阶段呈现出的“薄弱点”,除对硬件设施、经费投入、课程资源等办学要素进行改革,还需对农村学校的职能定位、办学理念作出新的思考与判断。
西北师范大学讲师李晓亮博士分析,当下农村教育很难办好的一个原因在于农村学校是照着城市的一套在模仿,且一些模仿不到位。而伴随新阶段乡村教育职责使命的转变,“农村教育不光要让一部分人离开农村,还要考虑让一部分人留在农村,把农村建设得更好。”
“在地化”同样是华中师范大学信息化与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付卫东给出的建议。
付卫东以近年来在农村学校颇为盛行的互联网教学为例,他坦言,大城市的课程资源不一定适合乡村小学校。他建议,村小、教学点向镇上的中心校寻求支援,而县一级的教育主管部门也要有“一盘棋”的发展理念,明确不同学校的职责,在当地倡导“资源共享”,把校际之间、教师之间紧密地联系起来。
抱着相同的理念,一些基层教育主管部门在落实推进政策时,更加注重因时因地作出调整。
一位乡镇学区的校长透露,按规定是23名学生一个教师编制,但他所在学区会参照学校人数规模进行教师分配,人数过少的学校,两个班级配3名教师,70人左右的学校,每个班级配2名教师,百人以上的学校,两个班级配5名教师。此外,鼓励一些小规模学校抱团发展,以学区为“单位”,动员师资较为富余的学校的教师去教学点走教,填补科任教师空白,学区会为走教教师争取更多补贴、奖励。
一些高校、科研院所、公益机构积极投身乡村教育事业。通过东西部协作、对口帮扶等,乡村学校有了支教教师,乡村教师也有机会到发达地区参加培训甚至挂职锻炼,在交互体验中,共同探讨适合乡村的教学方法。
一些地区学生的“回流”是对这些尝试的某种“肯定”。安徽省阜南县教育局摸底发现,2017年,阜南县共有8275名农村学生从城区和外地“回流”到该县的乡镇学校。2020年,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权家湾镇赵家岔村小学也迎来3名县城“转校生”。据悉,两年间,该县村小学累计回流学生达170人。
当然,“在地化”还包含一项重要内容——培养一批扎根农村、甘于奉献、一专多能、素质全面的本土化的乡村教师。
一位村小校长则表示,“情怀”“激情”“敬畏”3个关键词是办好乡村教育的“核心”,只要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这样做,“时代的问题终会在时间中得以解决”。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豪 来源:中国青年报 【编辑:李赫】
相关推荐
猜您喜欢
- 这里乡村民宿有了40年产权!政府与企业共同探索破局之路
- 攻坚之星丨支月英:40年扎根乡村扶贫扶智
- 优先发展农业农村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共濮阳市委党校讲师 刘芳鸣
- 河南:培养新农人 建设美丽乡村
- 多地给出乡村振兴大礼包 快来看看有没有你家乡
- 【中国之治@文化解码】新媒体技术助力乡村治理
- 脱贫攻坚主战场贵州:产业振兴带动乡村全面振兴
- 都市里的美丽乡村——广东东莞市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调查
- 鹿心社:乡村振兴建设要尊重农民意愿 打造彰显桂风壮韵特色村庄
- 省人大代表王洪伟接受大河网采访做强农业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
- 市领导赴台前县调研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和学校疫情防控工作
- 司伟: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亟需解决资产管理问题
- 告别绝对贫困 中国接力乡村振兴改善民众生活
- 人民论坛网评 | 用新发展理念指引乡村振兴
- 以有效乡村治理助力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