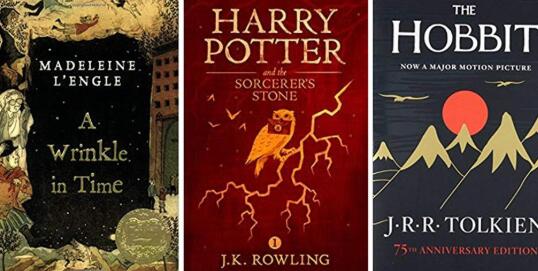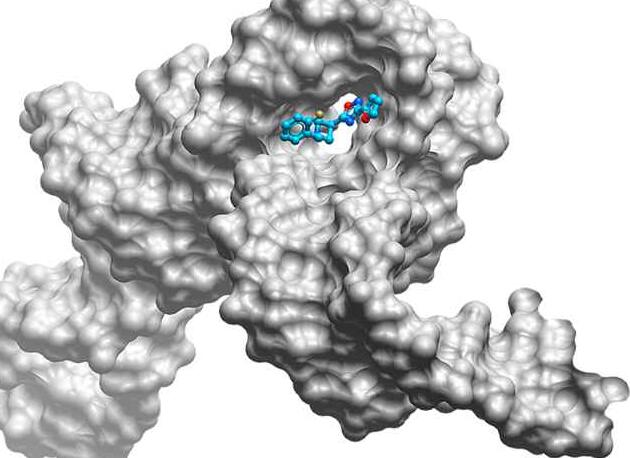文 | 邵宇 陈达飞
本文为“国家信用:公债陷阱、货币权力与现代货币理论”专题开篇。原文首发:澎湃新闻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世界陷入“公债陷阱”[1],政府债务杠杆率都达到了二战结束以来的峰值——均已经超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认定的60%可持续水平,但并未发生主权债务危机。人们甚至将后危机时期的“长期停滞”归因于过于保守的财政政策[2]。在经典的凯恩斯理论中,在有效需求不足时,如果没有财政扩张予以配合,货币政策因流动性陷阱的存在而无效。
以史为鉴,各国政府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时更加积极(Chine,2021)。据统计,2020-2021年全球财政赤字率合计分别达到了10%和8%。在主要经济体中,美国的财政支出规模最大,从2020年3月到2021年3月,四轮财政救助计划合计达5.9万亿美元,占2021年GDP的26.9%[3](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和2009年《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案》支出总额为GDP的10.3%),2020和2021年的赤字率分别为15%和11%(IMF,2021)。关于财政可持续性、债务货币化及其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再次成为热点话题。
如同持续的低通胀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创造了空间一样,零利率或负利率也提高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两者形成了一个闭环,为现代货币理论(MMT)及其政策主张——“财政赤字货币化”(或广义上的“债务货币化”)提供了现实依据。理论上,只要“r<g”(实际利率小于经济实际增长率)财政就是可持续的,问题在于长期估计误差较大,结构性拐点更不可知。过去60年里,美国国债实际利率的平均值为2.69%,中位数为2.18%。考虑到近40年的下行周期,未来三十年选取1%(33%分位数)作为基准比较合理(Cline,2021)——高于过去10年的平均值。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2021)对实际GDP增速的估计为1.8%。要想保持债务杠杆率的稳定,基本赤字率(primary deficit,即利息收支除外)需保持在0.8%左右。这显然不符合现实约束。
2008年至今,美国政府债务杠杆率已经从60%以下上升到120%以上,仅次于二战时期的125%(图1),CBO的预测2051年将超过200%,即使利率维持低位,利息负担也会显著提升。鉴于债务杠杆率的高企,再考虑到美国人口老龄化(古德哈特和普拉丹,2021)和财政支出结构的趋势性变化(如社会保障开支占比的提升等),美国财政的可持续性是值得怀疑的。如果通胀“破防”,通胀预期和利率中枢随之抬升,某种形式的违约或难避免。矫正财政收支失衡的方式无非是:增加税收、通货膨胀(税)、美元贬值(铸币税)或债务违约——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本质上是隐性违约。
图1:美国政府债务杠杆率
(Bordo and Levy,2021)
若将联邦政府财政赤字率和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或持有政府债券)规模的同时提升视为MMT的实践[4],那么在美联储一百多年的历史上共有四个案例(图2):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大流行。其中,前两次的财政赤字率显著高于美联储扩表规模,后两次规模相当,且可以看出美联储扩表的主要方式是购买政府债券。除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外,另外三次都导致了明显的通胀压力,整体CPI增长的高点分别为20%、13%和8%[5],并且持续时间均较长,从首次突破3%到首次降至3%以下,一战用了60个月,二战为34个月,新冠大流行目前已经持续11个月[6]——根据美联储关于通胀期限结构的预测,还需12个月左右才能降到3%以下[7]。在2022年3月21日的演讲中[8],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目标是3年内将通胀降到接近2%。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的通货膨胀之所以演变为70年代的“大滞胀”,虽然直接驱动因素是财政赤字的扩张,但美联储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只是没有以扩表的形式表现出来[9]。
图2:美国联邦政府赤字率和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扩张(美联储诞生以来)
数据来源:FED,CEIC,笔者绘制
说明:美联储持有的国债变化包含短期到长期的所有联邦政府证券。
历时百年,美国的社会经济结构、美联储货币政策框架,以及美联储与财政部的关系以及全球化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百年前是工业社会,现在是服务主导型社会;百年前是商品货币时代,现在是信用货币时代;百年前的美联储更像是财政部的“出纳”,现在的美联储则具有完全的货币政策自主权。百年前的世界经贸关系是在帝国秩序下进行的,现在是主权国家之间(或多边贸易协议内)的自由贸易。以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和浮动汇率制在全球的推广为分野,再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通胀目标制 利率规则)的确立,货币数量与通胀的相关性也发生了变化。虽不能将三个案例中的通胀压力都归因于财政赤字货币化,但货币作为持续高通胀的必要条件则是一条久经历史考验的经验法则。财政赤字货币化具有显著的通胀效应。
Bordo和Levy(2021)考察1800年以来美国和英国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发现战争时期政府开动印钞机征收“通胀税”是普遍现象。在20世纪初的两个和平时期,债务融资支持的财政赤字也产生了通货膨胀。对比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时期的政策,他们认为后疫情时代的通胀压力更大。现实情况也符合作者的预测。任何方式引发的通胀都是对债权人征收通胀税,对于其灾难性后果,凯恩斯在《货币改革论》中做了详细阐述。这一融资手段是有限[10]且不可持续的。列宁说:“要想颠覆现有社会的基础,没有比货币贬值更绝妙、更可靠的办法了。”
事前看,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低通胀(和通胀预期)、低利率和菲利普斯曲线的平坦化的事实确实提高了MMT的可操作性,但事后看,MMT的实践也有可能推翻其自身的逻辑自洽性。因为有充分的理论和经验证明,财政没有“免费的午餐”,长期低利率和不断上升的债务比率是一对矛盾体——债务杠杆率的提升终会导致利率的上升(Chine,2021)。学术文献的共识估计是,政府债务杠杆率(债务总额/GDP)每增加1%,10年期国债利率就会提高略高为3.5bp(Rachel和Summers,2019)。
基础货币如同央行发行的零息债券。若合并财政部与央行的报表,货币与政府债券都是公共债务。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本质是预算软约束,其对财政纪律、美联储的独立性和美元信用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可估量。如同物理世界不存在永动机一样,经济世界也没有永动机。一旦通货膨胀最终推动利率中枢的抬升,进而打破“税收-美元-美债”[11]闭环,全球都将为此埋单。债务货币化、美联储独立性和美元信用也是一个“不可能三角”:维护美元信用要求保持美联储独立性,却与债务货币化不相容。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时期一系列的紧急信贷支持计划模糊了货币与财政的边界。美联储应警惕财政主导[12](fiscal dominance)权力的回归,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Waller,2021)。
“我们从历史研究中得到的教训是:避免战争;审慎使用货币政策来维持财政赤字;避免财政主导;保持央行独立性;稳定通胀预期;并推行有利于增长的经济政策……忽视历史教训可能会给政策制定者带来风险。”[13]令人担忧的是,政策制定者们都在被历史裹挟着向错误的方向前进。理论上,在MMT的框架内,主权信用货币发行国不会出现主权债务违约,尤其是像美国这样的国际货币发行国。这并不符合历史经验。英镑的教训还历历在目。美国长期以来的财政与国际收支“双赤字”仍在侵蚀着美元的信用,这是美元体系固有的矛盾。实际负利率是美国国债透支美元信用的一种表现。随着美国经济份额的下降、中美经济相互依赖性的弱化和俄乌冲突催化的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美元信用靠什么来重建?
[1]公债即国债。
[2]在对欧元区和美国的复苏路径进行比较分析时或可得到这一结论。
[3] 2020年3-4月援助法案总额为3.1万亿美元(占GDP的14.8%)。2020年12月通过了一项9000亿美元的联邦支出法案;2021年3月又通过了一项1.9万亿美元的联邦支出法案;总额为5.9万亿美元。
[4]通常所说的“债务货币化”指的是将货币创造作为政府支出的永久性融资来源(Andolfatto,2013),也有观点认为,应根据美联储是否是有意帮助政府融资(Thornton,2010)。无论从哪个角度看,2008年以来的实践都符合“债务货币化”的定义。一方面,美联储已实施充足准备金制度(Waller,2022),截止到2019年7月缩表结束,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仍远高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后疫情时代的缩表也将是不完全的。另一方面,财政政策的主导性和货币政策的适应性更毋庸置疑(参考本书第二章)。
[5]数据截止到2022年2月。
[6]一战和二战时期,美国的通胀率在美国正式参战之前就超过了3%。
[7] 2022年2月的数据,来源费城联储官网:https://www.philadelphiafed.org/surveys-and-data/real-time-data-research/atsix
[8]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newsevents/speech/powell20220321a.htm
[9]主要表现为更高的M1增速和更低的利率(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一个百年”)。
[10]凯恩斯认为,“通胀税”融资额通常不超过GNP的20%,而通过低息的债券融资则可达到GNP的100%。但正如本文所说,后者也会形成通胀。
[11] MMT认为,在信用货币时代,税收驱动货币。
[12]财政主导假设认为,持续的财政赤字和不断增加的债务对央行施加压力,迫使其采取通胀性货币政策。
[13] Bordo and Levy,2021.
相关推荐
猜您喜欢
- 俄罗斯债券违约事件「俄罗斯主权债务违约」
- 美元指数筑底「美元指数走强」
- 通胀飙升经济反弹,欧洲央行将适度放缓购债步伐「英国负利率发行国债」
- 金科地产近况「金科资金紧张」
- 2020年各省专项债额度「地方专项债券额度」
- 财政部购买国债「债务置换」
- 汇丰晋信动态策略净值「汇丰晋信2022下半年债券投资策略 严控风险 寻找机会」
- 通货膨胀对比特币影响「影响比特币走势的因素有哪些」
- 债务重组的6个常见涉税问题解析「债务重组涉及哪些税款」
- 美债收益率持续走高释放哪些信号 「美债收益率对美元的影响」
- 万达集团疫情捐款「万达电影近期投资了哪些电影」
- 如何理解债务「读懂什么意思」
- 负债的解释是什么「负债是啥」
- 美联储购买债券影响「美联储购买债券」
- 债权转让的相关财税规定「债权转让需要缴纳哪些税」
- 美联储出售债券对利率的影响「美联储缩债是利好还是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