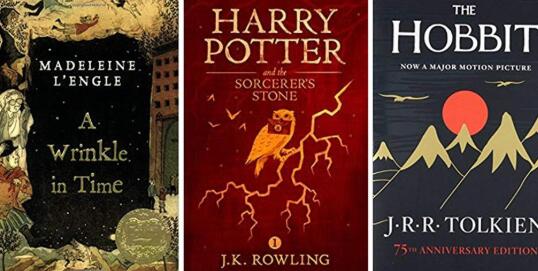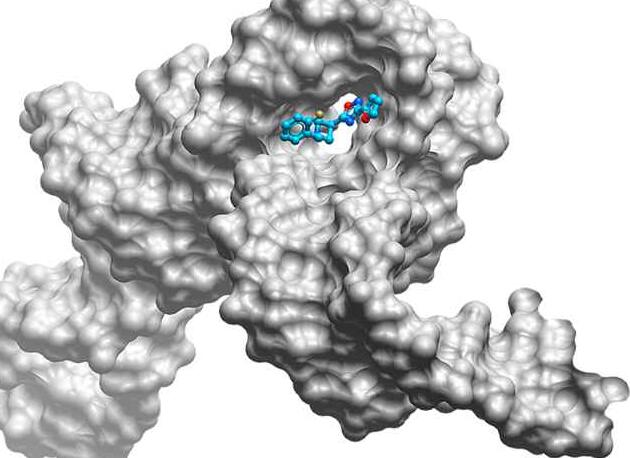按:何为华夏?何为中国?“中国”从文明的意涵走向国家的意涵,“中华”从一个文化共同体变为一个政治共同体,背后的历史脉络是怎样的?在《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一书中,日本神户大学教授王柯梳理了中国统一多族群国家的历史脉络,追溯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演变。
王柯提到,20世纪初,在大多数中国人还没想清楚如何处理近代国家建设与多民族国家传统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的时候,“中华民族”一词就已经横空出世,尤其是外敌的侵略将“中华民族”一度推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之后,这一概念逐渐深入人心,人们越来越习惯于将许多问题都放在“中华民族”的层次上来进行思考。然而,“中华民族”究竟是“民族”还是“国民”?抑或是代表国家?他指出,“不得不说这个名词其实至今缺乏一个科学的定义,”这个问题一直以来“困扰着力图从理论上解释20世纪以来中国建设近代国家历程的研究者们”。王柯分析认为,事实上,当年近代中国思想家们在接受“民族”这个词时,已经对此后中国的近代国家建设进程有过非常明确的考虑。我们今天的困惑,其实是来自后来的历史过程并没有遵从他们当初关于“民族”“国民”“国家”之间关系的设计。
而为了解开这个困惑,他认为我们既有必要回顾当年的近代中国思想家们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设计,也有必要思考中国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为什么没有遵从他们当初的设计。
经世纪文景授权,界面文化从王柯日前出版的《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一书中节选了部分章节,以期与读者一同思考“中华”概念的认识流变。
《“驱除鞑虏”:“中华”在近代的再认识》文 | 王柯(节选自《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先生在夏威夷的檀香山成立了政治团体“兴中会”。关于成立这一组织的理由,《兴中会章程》做了如下说明:“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盖我中华受外国欺凌,已非一日,皆由内外隔绝,上下之情罔通,国体抑损而不知,子民受制而无告,苦厄日深,为害何极。兹特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以扶国宗。”“华人”指的是中国国民,“国体”指的是中国国家,而受到外国列强侵略的“中华”,却包括了整个中国国家或全体中国国民。出现“子民”一词,证明这个章程中没有提及“主权在民”的问题。也就是说,从这个章程的内容中还看不到明确的“反清”意志,至少在这个时点上,清王朝的统治民族集团—满族也没有被明确排除在“中华”之外。
但是仅仅两个月后,孙中山先生就在香港修正增补了《兴中会章程》,明确地将推翻清王朝对中国的统治定为兴中会的目标。兴中会会员的入会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中的所谓鞑虏或胡虏,很明确指向来自北方的民族集团—满族,到了这个时点上,满族便被排除于“中华”之外了。
清朝末期民族革命思想的高涨,是将满族排除于“中华”之外的直接原因。而民族革命思想的高涨,又是和“汉族”民族意识的产生直接相关的。据说,是梁启超在他1901年所写的《亡国篇》中,第一次使用了“汉族”一词。“皇皇种族,乃使之永远沉沦,其非人心哉!夫驻防云者,则岂不以防我汉族哉!”但是从大量的文献中可以看出,事实上当时的人们更愿意使用的还是“汉人”“满洲”或“满人”。例如,1903年1月29日在东京留学生新年联欢会上,马君武和刘成禺做了“排满”演说,他们主张:“不排除满洲的专制、恢复汉人的主权,就救不了中国。”
从中国历史来看,每当出现强大的王朝之时或其后,王朝的名字也就成了生活在或曾生活在中国王朝直接统治之下的人们的自称或他称,“秦人”“汉人”“唐人”“宋人”“明人”等均属此类。其中因为汉唐时代中国王朝的影响力更大,所以“汉人”与“唐人”的称呼就更具有生命力。但是如果将“汉人”与“唐人”相比,可以发现,除了在时代上汉王朝更早于唐王朝之外,两者更重要的一点不同在于,早在唐朝之前的五胡十六国时代,中国就曾出现过“汉”“胡”对峙的历史,而“汉人”一词当时就发挥过区别“胡人”的作用。清朝末期的思想家之所以选择“汉”作为自己民族集团的名称,也许正是因为看上了这一点。
但是五胡十六国时代使用“汉人”以区别于“胡人”时,主要是从文化制度的角度。而近代思想家使用“汉人”时,则带上了强烈的种族意识。如前边提到的《亡国篇》中,除了个别“汉族”以外,还大量出现了“汉人”“汉民”“汉种”“汉种之人”等词。“汉族”一词的出现,本身就是这种种族意识的表现。事实上,许多文章都没有把“汉人”和“汉族”区分开来。然而,无论是“汉人”或是“汉族”,无一例外,都是相对于“满人”和“满族”而言的。近代汉民族意识的萌发,首先都是来自这种“反满”的意识。
关于未来中国的国家形式,当时中国社会中主要有两种认识,即革命派的认识和维新派的认识。革命派与维新派对立的焦点,在于究竟有无必要实行“排满”的民族革命、种族革命。梁启超是维新派的领袖和最主要的理论家。对于清朝的民族歧视政策,梁启超也非常反感,所以曾经一度主张过进行民族革命。但后来他认识到“排满”的种族革命和民族革命将会导致中国的分裂及外国列强的干涉,所以变为反对种族革命,主张进行政治上的革命,实际上即一场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的改革。
革命派则主张进行一场民族革命、种族革命。1903年末成立于湖南省的“华兴会”,在具有较浓厚的“排满”意识的同时,还具有排外的意识,能够将民族主义的意识建立在内外两个层次上;可是稍晚于“华兴会”在上海成立的“光复会”,就具有了更加强烈的“排满”意识,由陶成章起草的《龙华会章程》甚至写道:“满洲是我仇人,各国是我朋友。”1903年邹容的《革命军》最早描绘了建立“中华共和国”的蓝图。其中第一、二条开宗明义:“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不许异种人沾染我中国丝毫权利”;而第四、五、六条则分别写道:“先推倒满洲人所立之北京野蛮政府”,“驱逐住居中国中之满洲人,或杀以报仇”,“诛杀满洲人所立之皇帝,以做万世不复有专制之君主”。
事实上,很多革命家的民族主义思想不过是一种狭义的“反满”思想。“革命者,以去满人为第一目的,以去暴政为第二目的。”有人推断说,孙中山先生早就认识到了民族革命并不等于“反满”。因为1905年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的时候,一部分人认为该会的名称应定为“对满同盟会”,而孙中山先生则对此提出反对意见:“无此必要。我们革命的理由是因为满洲政府的腐败。如有同情我们的满人,应当允许其入党。”但是众所周知的是,就在同时期制定的同盟会入会誓词却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即以“中华”与“鞑虏”为对立面,提出驱逐满人为革命的第一目标。同盟会的入会誓词,应该是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制定出来的。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据说就是以同盟会誓词为基础归纳出来的。而在“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被列为第一位。1906年的《同盟会军政府宣言》也明确地表现了同样的民族主义思想:“维我中国开国以来,以中国人治中国,虽间有异族篡据,我祖我宗常能驱除光复,以贻后人。今汉人倡率义师,殄除胡虏。此为上继先人遗烈,大义所在”,“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敢有石敬瑭、吴三桂之流,天下共击之”。革命派的思想,在为了维持国体就应该排除异民族这一点上,其实质是与明末思想家王夫之的“夷夏大防”说相一致的。王夫之说:“天下大防有二,华夏夷狄也,君子小人也”。而孙中山先生说:“必朝野一心,上下一德,方可图治。而满人则曰:‘变法维新,汉人之利,满人之害。’又曰:‘宁赠之强邻,不愿失之于家贼。’是犹曰,支那土地,宁奉之他人,不甘返于汉族也。满人忌汉人之深如此,又何能期之同心协力,以共济此时艰哉。”在这里,孙中山先生彻底否定了汉族与满族联合的可能性。
为了煽动“排满”情绪,革命派反复强调“满人”“满洲人”并非中国人。他们纷纷执笔宣传:“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孰为中国人,汉人种是也。中国历史者,汉人之历史也”,“中国者,汉族之中国”,“汉族万岁,我中华大帝国万万岁”,“夫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非满洲之中国也”。
革命派否认“满人”“满洲人”在入关之后已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汉文化,并被汉化或面临着被汉化境地的事实。章太炎甚至对“中华”是一种文化的说法也提出异议,否认中国有接受了中华文化就是中国人的传统:“纵今华有文化之义,岂得曰凡有文化者,尽为中国人乎。”“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统而起。”他反对满人已经汉化的说法,认为同化一般指作为被统治者的民族集团向统治民族集团同化,而满向汉的同化,因为主导权不在汉,所以无异于一种“强奸”行为。
为了证明“满人”不是“中国人”,革命派对“华”“中华”也进行了重新阐释。例如,陶成章在其《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中如此写道:“中国民族者,一名汉族,其自曰中华人,又曰中国人。”就是说,只有“汉族”才是“中华”,才是“中国人”。再有,章太炎在其《中华民国解》中指出,华、夏、汉为同一意思。他说,汉的祖先自古以来就居住在雍州和梁州,因那里有华山,“就华山以定限,名其国土曰华,则缘起如是也。其后人迹所至,遍及九州。至于秦汉......华之名于是始广。华本国名,非种族之号,然今世已为通语。......正言种族,宜就夏称”,“夏之为名,实因夏水而得......地在雍梁之际,因水以为族名。......夏本族名,非邦国之号,是故得言诸夏。......汉家建国,自受封汉中始,于夏水则为同地,于华阳则为同州,用为通称,适与本名符会,是故华云,夏云,汉云,随举一名,互摄三义。建汉名以族,而邦国之意斯在。建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此中华民国之所以谥。”
在此以前,革命派叙述中的所谓中华,并不一定专指汉人。例如,在檀香山制定的《兴中会章程》中,除“中华”外,还使用了“中国”“华夏”“中夏”等词,这些均非民族上的意义。陶成章也说过:“我们中国将国家自称为华夏,夏为大,华为美,是大而美丽的国家的意思。中华,也称中国”。事实上,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之前,基本上没有过将“中华”作为民族的名称进行使用的例子。
所谓“中华”,指的究竟是什么呢?“中华”一词的诞生,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代。在南朝,皇宫的南门—正门被称为“中华门”。像清代紫禁城的东华门和西华门一样,很有可能是取“正面华美显赫之门”的意思。南朝宋的裴松之(372—451年)在注《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中,就号为卧龙的诸葛孔明一生,做了以下的论述:“若使游步中华,驰其龙光,岂夫多士所能沉翳哉。”也就是说,裴松之认为,诸葛孔明之所以没能充分发挥出他的能力,是因为他只活跃在蜀国即今天的四川,而没有活跃于中华大地上。北齐人魏收(506—572年)在其所著《魏书·高昌传》中描述高昌,即今天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吐鲁番地区:“其地东接中华,西通西域。”可见,“中华”首先是地理学上的意义,与“中国”相差无几。但是,作为“中国”和“华夏”的复合词的中华,在更多的场合是既指地理上的“中国”,同时又指最初诞生于“中原”、流行于“中国”的文明方式。例如,《新唐书·名例·疏议·释文》中写道:“中华者,中国也,亲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
历史上,“中华”基本上是作为这样一种人文地理意义上的词使用的。如果说它有时也被转用于象征民族集团的意义,那也应当是像1905年梁启超在他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所说的那样:“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混合而成。”即指拥有中华文化的各个民族集团而非汉一族。然而,根据革命派的解释,不仅是满人被排除在“中华”之外,“中华”甚至被他们改造成了“汉族”这样一个狭义的民族集团概念。革命派对“中华”的解释,最终是为了建设起一个“中华=中国人=汉族”的公式,让“中华”从一个文化共同体概念转变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概念。
为了唤起“汉人”的同仇敌忾之心,为了发动民族革命,革命派将原来主要是从地理和文化意义上来进行认识的“中华”,改造成为由单一民族构成的血缘型的“中华”,并且强调只有“汉人”才是“中华”—“中国人”,而满人并不属于“中华”,也就是说不是“中国人”,因而清朝对中国的统治也是缺乏合法性的。通过这种狭义的对“中华”的再解释,革命家们从民族上和文化上彻底否定了满与汉的同质性,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对立描绘成“中华”,即“汉人”,与“鞑虏”,即“满人”之间的对抗。而在这种狭义的“中华”话语中被表述出来的“中华民族”,其实就是“汉族”,相比起革命成功之后再次被提起的实质上指全体国民的“中华民族”而言,此时的“中华民族”不过是一个“小中华民族”而已。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革命,加速了中国走向近代国家之路的步伐。由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既是一场埋葬了封建王朝体制的民主革命,也是一场具有恢复汉族作为统治民族地位性质的民族革命。从封建王朝走向国民国家,从满人政权走向中华国家,从结果上来看,这两种趋势的发生和展开,的确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相互联系。孤立地看其中一面而无视这种内在的联系,自然会妨碍正确认识未来中华国家的本质。但是,革命的两个侧面,也许可以看作是第一目标与第二目标之分,甚至就是一种手段与目的关系。如果不承认在这场革命中民族革命先行一步的事实,也就无法理解此后中华国家的展开过程。因为在这个先行的民族革命的过程中,“中华”被革命家们努力从一个文化共同体改造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这一结果,此后一直不断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本文节选自《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一书,经世纪文景授权发布,较原文有删节,标题为编者自拟。
相关推荐
猜您喜欢
- 中国国债被纳入富时世界国债指数意味着什么「富时世界国债指数是什么意思」
- 揭秘美国国债的真正秘密是什么和什么「抛售美国国债的后果」
- 中国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银行资产证券化业务」
- 国际绿色债券「绿色债券政策」
- 中国债券今起纳入国际主要债券指数「实时债券指数」
- 融创收购万达资产第二轮融资 发行10亿高息美元债券「融创回购美元债」
- 外资买中国国债「外资购买中国国债」
- 恒大债券评级下降「恒大限跌令」
- 融创交房延期「融创发债」
- 中国银行投资次级债券「中国银行债券」
- 2021中国银行春招笔试答案「有没有什么打卡的软件」
- 恒生指数跟踪哪些股票「恒生指数是哪里的」
- 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条例「动产担保法律风险管理规范说法」
- 动产和权利担保的登记机关是哪里「动产和权利担保的登记机关」
- 港股中的优质股「港资持续流入股价下跌」
- 金观平 外资为何青睐人民币债券市场「外资流入导致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