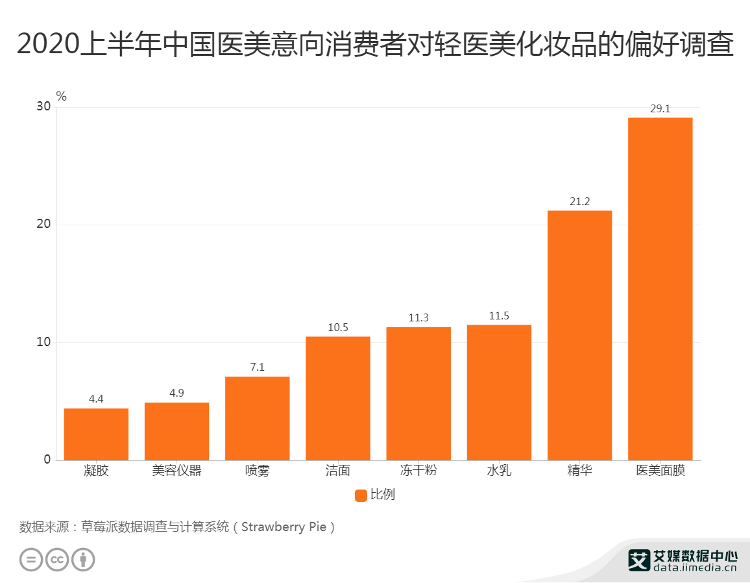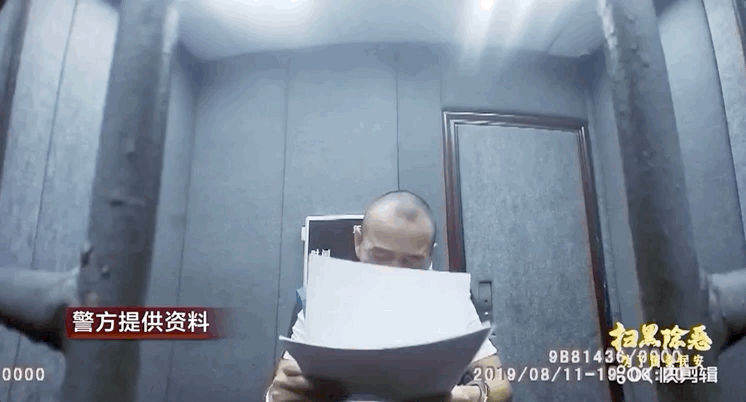近日,新疆棉花因NGO组织的一则抵制声明,发酵成中西方媒体的报道焦点。
欧美借所谓新疆维吾尔族人权问题攻击、诋毁中国的传统由来已久。这一话题为何“长盛不衰”?面对西方的不断指责,中国又该如何有力回击?就新疆问题及民族政策,观察者网采访了新疆问题专家、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启讷。
吴启讷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采访 观察者网 李泠
观察者网:您大概来过新疆多少次?
吴启讷: 大概有30多次吧。
观察者网:基本上把新疆各地都走过了?
吴启讷: 我做历史研究,不是人类学,所以我主要是去新疆各地的档案馆。不过我在当地有很多朋友,维吾尔族、哈萨克族、锡伯族、蒙古族、回族、汉族等民族的都有。
观察者网:您是新疆问题专家,但听说曾因在一部关于新疆的纪录片里的访谈而遭台湾网民“出征”,后来电视台将您的片段全部删除后再重新上架。
吴启讷: 事情是一年多前发生的,台湾的公共电视台引进了一部由澳大利亚某个机构拍摄的,名为“新疆再教育营”的纪录片,邀请我在影片播放完毕后在节目中做一点解读和评论,我就从学术的角度,对里面的内容和拍摄者的评判,做了一些分析、澄清。节目播放当下,我就受到有特定政治偏好的网民的大规模围攻,有些有特定政治立场的媒体,在接下来的几天中,给我扣了很多政治帽子。
一些网民并不关心事情的真相,他们主要是希望听到他们想听的话。 当时,电视台屈从于网民和政治压力,在专业和新闻自由上做了很大的妥协,为自己播出了“不当言论”道歉。这是很遗憾的事,我自己也遭受了不小的压力和损失。

观察者网:能说说那些网民不能接受您的哪些描述吗?
吴启讷: 我提到美国等国媒体上流行的有关“新疆大规模拘禁”的描述缺乏可靠的来源和证据。
这部澳大利亚纪录片所呈现的“再教育营”,只是寻找在网络上可以找到的新疆影像,透过剪辑、重组,交替出现真实的学校和真实监狱的场景,让观众产生那就是“再教育营”的真实样子的印象,但其实,这中间没有任何现场实景; 还有,纪录片中访问的“证人”,没有一个是亲历者,都是转述朋友和“朋友的朋友”所说的内容 。纪录片这样做,显然不符合基本的新闻专业要求和新闻伦理,从专业的角度看,在可信度上就大打折扣。
我又说,纪录片可以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但一定要有证据;也可以对证据作不同的解读,但不能杜撰证据。结果,一堆网民认为新疆的“集中营”“再教育营”,是美国人、澳大利亚人说的,绝不可能有假,我这样质疑这部纪录片,就是为“独裁”辩护。
我在访谈里讲到关于职业教育培训中心设置的背景和职业教育培训中心课程的细节,但网民显然根本不想理解其中的意义,也没有兴趣核实真相,直接把我这些描述认定义成“为中国暴行辩护”。大家知道,在台湾的政治环境里,这是非常严重的指控。
我在访谈中还谈到一点,遏制中国,是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长期战略,这个战略背后,包含一套庞大而复杂的遏制体系,包括军事、经济层面,也包括文化和宣传层面。在文化宣传这一部分,需要情报的支持,但更需要深度学术研究的支持。
冷战期间,美国的中国研究,也包括新疆研究,从研究传统、研究资源到精英的投入,在很多部分都超过当时的中国,这里面有很多学者是我非常敬佩的,他们也许立场各异,但对于证据和可靠研究方法的固执追求,都使他们的研究可以保有一定的质量,当时的美国等西方国家依据这些研究来制定中国政策,就拥有相对比较好的决策质量。
冷战结束后,尤其是最近的10年间,伴随中国经济的成长、全球化趋势的加速和网络世界的兴起,美国和某些西方国家的焦虑感大幅上升,他们加大了对情报工作和相关学术研究的投入,但是因为急于求成,获得的情报质量和相关学术研究的质量都有所下降。
在情报来源方面,我想海外华人社区应该都知道,从1980年代开始,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就兴起一种移民产业,可称之为“政治庇护产业链”,由律师协助没有当地居留身份的中国人提供一个申请永久居留的渠道,让他们声称自己遭受种种“政治迫害”,这样就可以很容易拿到绿卡。21世纪初之前主要是套用计划生育的名头,说自己在中国因超生被惩罚,近10年就说少数民族遭受迫害。
有些离开大陆的人士,受到一些国家情报机构的关注,提供自己知道的信息,但时间一久,他们的现货卖完了,就只能揣摩情报机构的需求,到媒体和网络上去找“证据”。这些人向媒体提供中国信息,大多也都是迎合媒体的偏好,无从查证信息的准确性。
美、加、澳、新(西兰)的华人社区都很清楚这一产业的情形,而所在国政府却一方面苦于无法查证政治庇护案的真伪,另一方面又乐见政治庇护案件所潜藏的政治资源。对此,台湾的民众大体不知情,也不关心,他们一听欧美政界和媒体说他们有学界和证人所提供的“确凿证据”,就认为不需要怀疑了 ,自然而然就会本能地觉得我在胡扯、在为“独裁”辩护。
观察者网:如果以后还有台湾媒体就这新疆问题采访您,您还会继续这么向民众解释吗?
吴启讷: 我做历史,我觉得,追求真相,并且坚持,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所以如果我碰到了新的采访,当然还是会做同样的解释。不过我想,不会有多少台湾媒体敢采访我了,现在台湾媒体也都承受很大的压力。原来还有某些愿意了解真相的媒体,但不是承受巨大的政治压力,就是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比如,台湾的通讯传播委员会在去年底就取消了中天新闻台的牌照。

炒作新疆问题
是西方打击中国的传统技能

观察者网:西方对新疆棉花的抵制,在经济层面会有哪些影响?内地舆论掀起支持新疆棉花的热潮,您认为能否有效帮助新疆拓展棉花销路?
吴启讷: 我觉得内地的反制情绪会有一些效果,但这效果不足以抵消BCI以及整个西方制裁的影响。
长绒棉是新疆的优质棉花,内地的纺织业市场应该可以把它消化掉;但新疆的棉花不全是长绒棉,尤其是北疆很多地方的棉花是利用机器采收,再加上用无人机喷洒落叶剂等农药,导致这些棉花的品相有所下降。而且它们的生产成本较高,如果内地纺织产业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使用这些棉花,产品的竞争力也会相应下降。以往内地的纺织业会通过进口美国的棉花来补足缺口。
所以,放到具体的纺织业生态里来看,我想这次新疆棉遭遇的损失不是一时之间就能弥补回来的。

观察者网:为什么西方这么喜欢炒作新疆话题,而且目前来看反复炒作反复“有效”?
吴启讷: 从中国的边疆和少数民族议题切入,是西方打击中国的一项传统。西方从19世纪接触中国以来,就想在中国推行他们在非洲及亚洲其他地区的殖民政策,但他们发现中国的国家组织、社会组织都比较严密,不像其他非洲亚洲那样容易见缝插针,只有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现象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缺口。
19世纪那时候,中国的中华民族建构过程还没开始——其实不仅那时候还没开始,我认为时至今日中华民族的国族意识也未建构完成,仍处在进行过程中。这使得西方认定这是一个可以供他们介入中国事务乃至裂解中国的切入点。
中国内部在面对多元文化、多元民族议题,处理边疆事务时,通常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所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让少数民族享受一些优惠政策的背后也有放松政治力道的设计。这一政治设计也给对中国有敌意的西方提供了介入的缝隙。
以前俄国、英国、法国、日本及现在的美国都“趁虚而入”过,且每次都可以达成一定的效果。如果我们从1830年开始顺序观察到今天,可以说至今190余年间在新疆发生的所有政治动乱都有外来势力的影子。
就美国而言,1940年代中期,蒋介石为了牵制苏联,将美国势力引进新疆。美国在新疆设立领事馆后,就致力于鼓动新疆脱离中国。后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一过程看起来中断了,但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美国又开始运用各种方式介入新疆。我们看到1990年代之后新疆的动乱再度增加,这些活动背后都有美国的因素,美国或通过在中亚活动影响新疆,或直接介入,相关证据越来越多。
一些台面上的美国人也并不讳言自己对所谓新疆维吾尔族争取宗教权利活动的支持和对分离运动的支持。这也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一直在做的事,他们在海外整合了若干维吾尔分离主义组织,向它们提供可观的经费资助,使得分离主义组织成了旅外维吾尔族人士的“正统”的、垄断道德正当性的政治组织,那些自认自己是中国人的维吾尔族人士,在海外反而成了过街老鼠。
而在新疆当地,也有一些条件和美国相配合。一方面,新疆的农村经济还处在相对落后的状态,而在改革开放之后,新疆的宗教活动又大幅恢复了,有两个渠道让新疆的维吾尔族人和世界的接触增加。
一是伊斯兰的渠道,中国政府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权利,让它们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跟伊斯兰世界建立宗教联系,其中包括前往沙特阿拉伯的麦加朝觐;二是伴随中亚地区的苏联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独立,新疆部分维吾尔族人和其中部分国家的突厥语族群体有了关联,因此这些维吾尔族人在伊斯兰之外又建立了突厥语民族这么一个身份认同。
穆斯林加上突厥语民族这两个身份,让整个中华民族建构过程受到了一定的阻碍,也为美国人提供了介入的机会。
另一方面,中国的市场化让维吾尔族的民众面临两种情境——一是他们如果要改变自己贫穷落后的状态,需要到内地工作;二是新疆本身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在中国取消粮票、放宽人口流动限制后,有更多的汉人被新疆吸引,到新疆就业。
后者的人口流动让新疆当地民营经济比重不断加大,而民营企业老板有时候不太喜欢雇佣维吾尔族人——这跟西方的认识恰好相反,西方认为新疆存在“强迫”维吾尔族人劳动的情况,这与新疆的真实状况大异其趣。事实上,那些私企老板优先考虑盈利问题,他们更愿意雇佣语言没有障碍、技能经过培训、工作文化相接近的汉人。
这一选择导致的情况就是,因国家政策保护,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民众进入公立机构的机会比汉人大,且受提拔的机遇也比汉人多,但在民营这块,情形就大不一样了,面对维吾尔、哈萨克斯坦族人士,就业的大门就比较窄。这一现象成为外人煽动维吾尔族人不满情绪的一个切入点,但,需要的时候,这些外人又宣称维吾尔人被“强迫劳动”。看来他们并不在意自己不断切换逻辑的漏洞。
观察者网:那您认为现在推行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能否有效解决上述提到的问题?
吴启讷: 毫无疑问,在语言、技能方面的训练会提升受教育者的工作竞争力,对他们是有正面帮助的。不过职业技能教育培训里也包含反对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这类教育,我认为这种教育对于已改开40余年的新疆来说,成效相对有限。
现在新疆的维吾尔族人更多通过互联网获取资讯,他们从突厥语世界、伊斯兰世界,从中亚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及南亚地区获得的资讯非常多。现在在民间甚至流行一种偏见,认为用汉字书写的资讯缺乏可信度。
所以我们会看到一种平行现象,那就是一些“两面人”的出现,比如CGTN反恐纪录片《暗流涌动》里提到的新疆自治区教育厅原副厅长阿力木江·买买提明等人。他们表面上看起来拥护国家政策、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但私下里又在做另外一些事情,比如非常热衷宗教活动、热衷跟境外的人联络,且把传播境外的信息当成一种时髦。
其实在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中,新疆并不存在非常严重的民族冲突,因为那时主要用阶级来划分人群,从不是用民族来划界,但到了1990年代之后,不管是在工作机构、教育机构还是商场等,我们渐渐看到民族好像成了一堵无形的墙,分割了各民族人的心灵。
总而言之,我认为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确实会推动维吾尔族人融入和适应现代社会,而在思想教育方面的成效,我觉得会打折扣。

中国应淡化“民族”的政治色彩
观察者网:那么就如何推动民族融合,您有什么建议吗?
吴启讷: 在民族政策方面,我们应该从大的方向去考虑。其实我自己平常不用“民族”这个词,因为我觉得“56个民族”这种描述给中国的族群现象加了政治色彩。
自1949年以来,国内在定义少数民族时,赋予了每一个民族特殊的政治权益,再在政治权益的基础上建构那些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其实大部分少数民族原本都没有写过自家的民族历史,这些工作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民族平等政策下帮助他们完成的。完成之后,把原本不那么清晰、不那么重要的族群文化界限本质化、清晰化了。界限的明确,使得少数族群逐渐形成或强化了民族意识,而这种民族意识跟西欧式的民族国家意识相一致,部分人逐渐把政治诉求上升到跟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相冲突的一个状态。
这状态在中国人民的解放过程当中或许是一个必要因素,因为那时要解决的是过去几千年来处于优势地位的汉人文化对少数族群的压制;但过渡阶段过去之后,我们要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中国应该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我想马戎先生的建议非常重要,就是应该强调族群身份的文化性,减弱其中的政治性。
说直接点,族群文化差异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少数族群的文化可以也应该获得国家的大力保护和支持,但不管汉人还是少数族群,他们的政治身份只能有一个,那就是中华民族一员,在此之外,不应该存在第二个平行的政治身份,这是减少国族分裂风险的必要思考方向。
观察者网:在实际操作中,要怎么把政治性和文化性剥离开来?
吴启讷: 我觉得第一步可以从文化氛围入手。我们现在的一些文化出了问题,比如讲一个人的身份,一定要讲他的姓名和民族,这点甚至会追溯到古人那里去。我看到有一本《曹操传》,在介绍曹操时,开宗明义就写“曹操,汉族”,这就有点过分了——不仅古代并不存在汉族这个概念,现实生活中个人身份的确立也并不需要提到他的民族。
我举个例子。东南亚国家非常重视宗教,他们在身份证上一定要标识自己信仰的宗教。当地很多华人有时候并不确定怎么标识,只好在身份证上填写儒教或孔教(Confucianism)。其实是否标明自己的宗教性,对中国人来说并不是重要的事情。
同理,在中国的传统里,人的族群差异并不受重视,大家更重视你在文化上是不是“文明化”了——这一表述可能带有文化中心主义、文化偏见,重点在于阐述组成中国人的标志是文化,而不是语言等差异;中国各地的语言、方言多的不得了,但只要你接受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你就是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至少在身份证上不需要标明民族信息。
当然,对于少数族群的一些优待也没必要取消。比如这些少数族群一般聚居在偏远地区,在经济方面处于弱势,需要国家的扶持,汉人对此也应怀有同情性的理解。至于大众比较关心的少数民族加分政策是否该延续?我觉得这就要视情况而定了。
如果他的母语不是汉语,且在偏远地区受教育,那他将面临一些汉人们没有面临过的困难,给他加分是应有之义;反过来,如果他在城镇地区受教育,且母语就是汉语,我认为如果继续让他享受加分优待,就是对完全同等条件下的汉人考生的不公平。 相比在发达地区受教育的少数民族,那些生活在新疆、西藏、内蒙古、青海、四川、云南、贵州等偏远地区的汉人,他们的教育条件也不好,他们在考试时是不是应该获得加分优待?
我知道在云南一些村子里居住着若干民族的成员,有些少数民族可以凭借政策获得优惠,而他的老邻居,祖上也在此居住了两三百年的老邻居,却没办法得到优待。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这么一个身份上,每个公民在法律地位上完全平等,国家再根据公民具体面临的处境差异给予政策上的优惠,而不是用所谓的民族来划线。
中国在反击西方舆论攻击时
要有文化自信
观察者网:回到当下,就目前整个国际舆论氛围来看,中国的反击看上去有点被动。关于后续如何更好地回击,您有没有想法?
吴启讷: 我认为中国的民族政策,不论是从传统角度还是革命角度来看,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关于少数族群的文化政策,中国应该理直气壮地对外展示这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首先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宽容,而宽容传统在西方那种用人群、血缘来划分界限的文化中是不存在的,中国这一种宽容的精神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未来世界也要朝这一方向前进。
其次,中国在革命的过程中吸收了苏联的民族平等政策。西方讲究所谓的自由——不一定是真的自由——而苏联讲究平等,包括阶级平等、族群平等、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苏联的这一政策后来被中国共产党借鉴到中国的民族政策里,并获得了非常真诚的推广实施。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后,少数族群才有机会走到普通人的眼睛能够看得到的舞台上,现在大家还追维吾尔族的明星,其中完全没有种族偏见。

所以,中国完全不需要为自己的民族政策感到心虚或内疚。放眼全世界,中国完全可以最自信。即使在自称文化多元主义的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它们在种族关系、族群权益方面的记录非常糟糕,但它们脸皮厚,技巧娴熟,可以轻松地把自己打扮成种族平等、多元文化的保护者。
当然,在展现形式上,中国应该去掉过去那种口号式的宣传方式,争取多元化呈现,比如塑造比较吸引人的艺术形象。中国有必要了解,如何在呈现时让别人能够听懂并接受,这就涉及话语权软实力的一面。
观察者网:说到西方在少数族群权益上的历史记录,记得单就针对穆斯林群体,它们就曾出台一些管治措施。比如,法国、瑞士推出过“面纱禁令”“头巾禁令”;9·11之后,美国国内社会掀起过反穆斯林浪潮,前总统特朗普还推出过“禁穆令”。您怎么看待它们这些双标表现?
吴启讷: 西方的双重标准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讲,一是历史层面,二是有形设施层面,三是宗教宽容层面。
从历史层面来看,基本上欧洲国家能够有明确记忆的历史就是反伊斯兰的历史,十字军东征就是它们跟伊斯兰世界的战争。因此它们整个社会充满了反伊斯兰的氛围和基础,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对伊斯兰教的敌视、侮辱是随处可见的。在法国发生的多起血腥冲突,都跟对伊斯兰的仇视以及伊斯兰的反弹有关。
从有形设施的角度来看,现在欧美的穆斯林人口在大幅增加,但我们看当地的宗教设施清真寺及伊斯兰教育场所,数量、比例远远少于中国大陆的相关配置,可以说是少到可怜。如果我们用中国大陆的标准去要求它们,完全可以指责它们是宗教迫害。
再比如饮食,我们在中国大陆随处可以看到清真餐厅,不信仰伊斯兰教的中国同胞跟信仰伊斯兰教的同胞出去吃饭时,一般会去清真餐厅以表示对后者宗教信仰的尊重。这是中国的传统,被视作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在西方,就不一样了。在美国,我很多次只能带穆斯林朋友去犹太人开设的餐厅,因为犹太餐厅跟清真餐厅相对接近,他们找不到清真餐厅,非常困窘。
其实在台湾也一样,台湾网民对中国大陆民族政策的指责非常多,但全台湾只有4座清真寺,这跟台湾27万穆斯林比起来,比例小得非常可怜;如果按照中国大陆的标准,台湾应该增建400多座清真寺。我在新疆、宁夏的朋友来台湾时,他们有的人会吃20多天的吐司面包,因为没有清真餐厅,不敢到别处吃东西。所以我不知道台湾网民在指责大陆的民族政策时,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们为何还会如此理直气壮?

再就是精神层面来看,中国社会普遍尊重伊斯兰文明,而我们在西方世界里看到的基本都是鄙夷贬斥,把它视作邪恶势力,这一情况不仅在传统文化气氛里存在,现在在学术领域也能看到他们对伊斯兰的鄙视。
当然,现在西方社会里也有所谓的“白左”主张对伊斯兰、穆斯林保持宽容态度,但他们其实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把握,因为他们内心还是包含了对伊斯兰、穆斯林的轻视,他们觉得伊斯兰文明里提倡的那些价值不是他们所推崇的普世价值。他们在讨论伊斯兰价值的时候,讲的还是如何拯救穆斯林妇女。这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认为自己的价值比较高级,“同情”穆斯林妇女,但完全不知道应该尊重别人的文化。
我们可以看看伊斯兰国家,哪一个不忌惮美国?即使是跟美国政治关系很好的沙特阿拉伯,那里的普通民众也都能看出美国对他们的轻视甚至敌意。
来源|观察者网

相关推荐
猜您喜欢
- 雪克来提·扎克尔:新疆连续4年多未发生暴恐案件 实现了民众对平安稳定的期盼
- 上合组织秘书长及有关国家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参观访问新疆
- 美国炮制所谓新疆问题 学者称实为遏制中国崛起
- 上合组织秘书长和多国驻华使节及外交官参访新疆
- 这就是BCI在新疆找到的“强迫劳工”?
- 学者评新疆反恐纪录片:“暗流涌动”揭示新疆反恐任务艰巨复杂
- 外交部:上合组织秘书长及20余国驻华使节正在新疆参观访问
- 上合组织秘书长等参访新疆说“眼见为实” 华春莹回应说谣言止于智者
- 新疆“赏花游”受追捧 加速旅游业“回暖”
- 又一部新疆反恐纪录片播出,披露这些细节!
- 中国棉花协会:支持邀请国外行业协会等赴新疆调研
- 中国棉花协会:支持邀请国外行业协会等赴新疆调研
- 台湾烘焙达人在新疆:收获爱情和“面包”
- 能否证明美方在新疆制造动乱?外交部:欢迎外媒记者做一个连续跟踪调查报道
- 能否证明美方在新疆制造动乱?外交部:欢迎外媒记者做一个连续跟踪调查报道
- 国际锐评:“谣言流水线”盯上新疆棉花,美西方不为人权为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