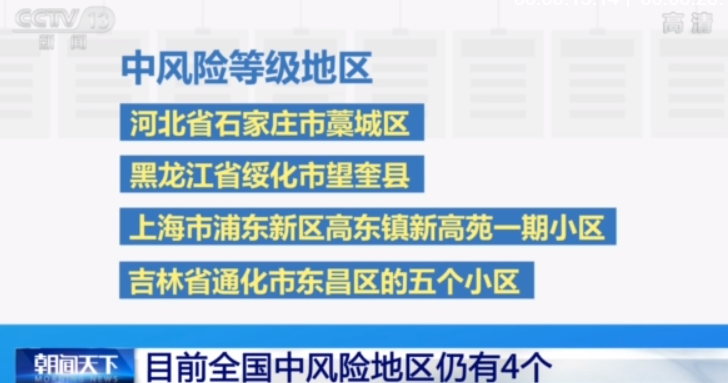半月谈丨治不好网络霸凌是文明之殇
“挂人”、P丑图、不间断“问候”双亲、扒黑料……无人知晓,此时此刻有多少人正在遭受网络霸凌暗流的冲击。有数据显示,我国有四成的未成年网民遭受过网络霸凌。依附而来的,是羞辱文化这一亚文化在网络世界的滋生泛滥。整治网络霸凌这种“社会群殴”式的病态现象,不仅需要受害者勇于反击,更需要技术的支撑和法治的完善,以及全社会的零容忍。
网络霸凌是一种全方位“精准打击”
目前,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约为1.75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3.1%,其中,有42.3%的未成年网民遭受过网络霸凌。2020年11月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这天设为首个“反对校园暴力和欺凌包括网络欺凌国际日”。
天津市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付佳介绍,校园网络霸凌常见的方式是通过发信息、照片、视频等贬低被霸凌者,让受害者蒙羞后,再借由社交网络进行更广泛的传播。
与传统霸凌不同的是,网络霸凌凭借机械化、号召性极强的特点,无休止全方位对当事人实施“精准打击”,能快速击溃未成年人心理防线,严重的甚至可以将当事人逼上绝路。实施网络霸凌的人,往往有一到数个“圈子”,通过一起观摩影视作品寻找霸凌灵感,更有甚者,以设计霸凌情节、直播霸凌过程为乐。
在绝大多数的网络暴力事件中,受害者往往只能选择沉默。无论是对个体而言巨大的、难以招架的声浪,还是藏在手机屏幕后,那些不知来自何方的拳头,出于对被“人肉”的恐惧、不愿被反复伤害等考虑,卸载社交软件、等待风波过去成为很多人不得已的选择。
羞辱文化何以大行其道
在看似波澜不惊的学校里,羞辱文化正依附于网络悄然滋长。羞辱文化是网络霸凌带来的一种亚文化。一些黑暗隐晦的力量,经过互联网被无限放大。施暴者就像是在虚拟世界中随意扔石头,没有人知道是哪块石头最终砸死了受害者。
在我国,反网络霸凌的法律法规目前还不够明晰。上海一名高三学生小林(化名)在遭受长达1年的网络霸凌后,选择了报警,得到的答复却是:情节较轻且并未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没有达到立案的标准,无法受理。律师也无奈相劝:可以起诉,但收集证据难度较大,且在无法明确欺凌主体的前提下不建议起诉。
寻求法律的介入,在很多人看来不但是小题大做,也很难得到实际意义上的解决,因为网暴源头很难锁定,“三无”小号没了也可以再换。久而久之,网暴者可以轻轻松松肆无忌惮地横扫一个又一个“战场”,受害者的真实人生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
网络空间的开放性带来话语权力的提升,但这并不意味着能够以“普通网友”的身份越过道德与规范去攻击戕害陌生人。
可以看到,从当前我国政策法规中传达的信息是,网络并非法外之地,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然而,网络上最近流行的“你的评论我喜欢,你的私信记得关”“把保护打在评论区”等评论,除了网友们对越来越严格的网络生态的调侃外,更多折射出的是对于网络暴力的无奈。
对“社会群殴”应零容忍
霸凌不会因沉默而终止,学会反抗是自我保护的终极武器。前段时间,一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学生,在微博上吐槽了一名女星。随后,该学生的姓名、院系、学校被女星粉丝一一曝光,粉丝还在学校的官微下方要求学校对该学生进行严肃处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则在官微上进行还击,对此事作出了回应。这起事件以女星在微博上道歉结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保护学生的做法值得称道。特别是在个人被群体情绪裹挟的时刻,理性的发声能够纠偏失控的行为,让施暴者反思,让受害者规避部分伤害。
打击网络暴力,除了勇敢发声外,更需要多方面共治共管。政府和网络平台应合力为受害者拿起法律武器创造更加便利的条件,畅通平台举报、申诉机制。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情况下,应立即对网暴者处以警告、封号等限制。为避免换个“马甲”卷土重来的情况,可在后台对屡禁仍犯者进行实名制记录,必要时可限制其平台账号的注册。
网络霸凌行为传播范围广,所引发的从众、跟风、模仿、放大等特点明显具有“社会群殴”效应。这不仅是对当事人的伤害,也毒化了社会道德风气,是任何一个文明的法治社会所不能容忍的。因此,除了个人心理调节外,国家还应该建立积极的应对机制。
一是对违法的网络霸凌行为进行及时的司法干预。这是最直接、最有效、最具震慑力的措施。二是网络平台应该承担起应负的社会责任。尤其是在社会面对此类危机事件的时候,公共媒体和网络平台理当有更多的担当和作为。三是需要全社会进一步加强公民道德教育和网络法制教育。近期,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已经向社会公布并公开征求意见,期待法律铠甲能够在治理网络霸凌方面发挥里程碑的作用。(记者 梁姊 吴晓颖刊于《半月谈内部版》2021年第2期) 【编辑:田博群】
相关推荐
猜您喜欢
- 乡风文明推动乡村振兴
- 文明城市 因你而美——致全市人民的感谢信
- 文明出行,别样春运更温情
- 漫评 | “末梢网络”激活社区治理新活力
- 团结村的新时代文明乡风如何树起来
- 拓展网络时代的关系理论
- 网络黑灰产为网络犯罪持续“输血供粮” 中国最高检强调“打财断血”
- 最高检:2019年以来起诉网络犯罪案件5万余件14万余人
- 最高检:办理网络犯罪案件应当把追赃挽损贯穿始终
- 西藏出台生态文明建设综合性法规
- 突出地方特色 西藏推进立法保护生态文明建设
- 2020年全国受理网络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1.63亿件
- 美团互助宣布关停 专家呼吁出台网络互助监管规则
- 河南兰考:开创水生态文明建设新格局 河湖相连润“红城”
- 生态文明建设踏上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