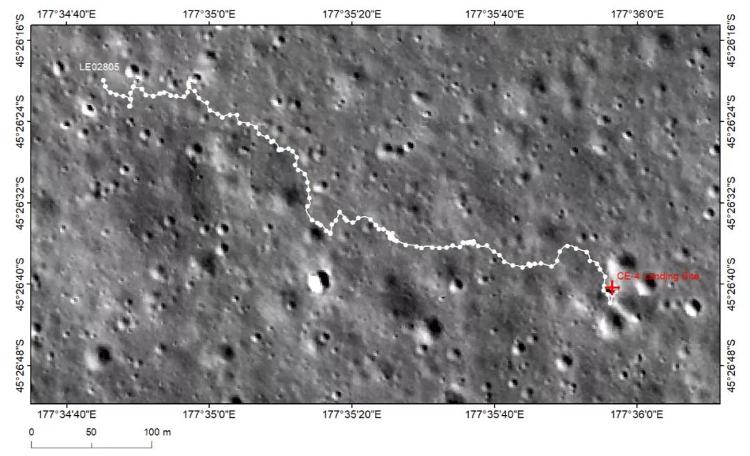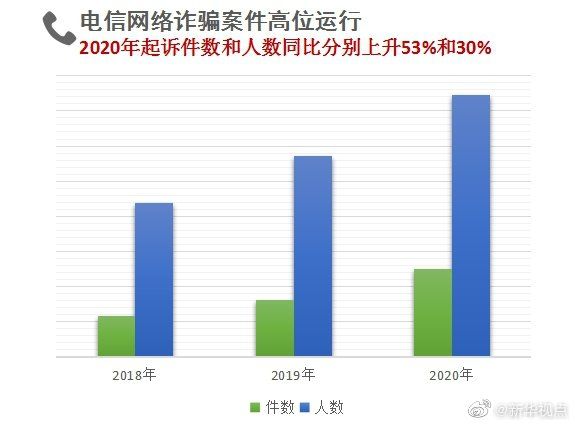低迷一个月的电影市场,终于在清明节小长假迎来了观影热潮。国家电影专资办数据显示,2021年清明档累计票房8.2亿元,创造了国内同档期票房纪录。位列票房前三的影片是《我的姐姐》《哥斯拉大战金刚》《西游记之再世妖王》,前两部斩获了档期内八成票房。其中,《我的姐姐》排片占比从上映首日的16.6%飙升至35.5%,是清明档的最大赢家。
截至4月6日18时,影片《我的姐姐》票房突破4.58亿元,打破《反贪风暴4》创造的国内清明档票房纪录和观影人次纪录。对于一部中低成本家庭类型片而言,这一成绩可谓亮眼,并带动持续低迷的大盘上浮。照此趋势,在新片较少的4月,《我的姐姐》极有可能走出一个漂亮的长尾,突破十亿大关。
影片讲述的是父母意外离世的二孩家庭,已成年的姐姐安然面临着追求个人生活还是抚养年幼弟弟的难题,在亲情的羁绊和个人梦想追求之间,她挣扎求索,找寻真正的自由与自我。在讲述安然命运决择的同时,创作者宕开一笔,从产科护士的角色观察,辐射当代女性在爱情、家庭与个人梦想之间斡旋平衡的一生,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
《我的姐姐》的成功,是意料之外更是情理之中。这与眼下女性意识高涨的氛围密切相关,在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环境下,从综艺到影视剧,文娱产品正在不断迎合女性的消费需求,重塑女性形象。在流行文化中,从“大女主”戏到《乘风破浪的姐姐》,再到《吐槽大会》,以“她”为名的综艺、脱口秀、影视剧井喷,女性的声音不断被表达,在掀起一阵阵舆论争议的同时,将大多数女性的真实诉求带到了日光之下。当这些故事被拍成影视剧、被讲述的时候,存在本身就是意义,被看见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中国式姐姐”
在多子女家庭中,“中国式姐姐”往往与勤劳、顺从、忍让、沉默、照顾和牺牲等词语画上等号。在亲情的裹挟下,姐姐的牺牲被认为是一种理所当然。
《我的姐姐》导演殷若昕和编剧游晓颖都是独生女,她们的创作缘起于2015年全面开放二孩政策。游晓颖观察到,身边的朋友陆续产生了生二孩的想法,其中包括一些成年朋友的父母,他们在抉择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亲情的撕扯和碰撞。“当姐姐从来都不是我自愿的。”不少观众留言讲述自己的经历。
《我的姐姐》实际上聚焦了两代“姐姐”,通过姐姐形象的变化反映社会的变迁与女性意识的觉醒,并将批评的矛头指向重男轻女的惯性思维。朱媛媛饰演的姑姑成长于多子女家庭,肩负“长姐如母”的责任,在物质资源匮乏的时候,她将读书的机会让给弟弟,一手操持大家庭的全部琐碎,放弃了个人梦想,照顾重病卧床的丈夫,对她而言,认命是唯一的选择:“我是姐姐,从生下来那天就是。”作为姐姐,她无法挣脱罗网,将自己的一生囚禁在家庭的枷锁之中,蹉跎于远低于才华的人生,直到影片最后,她理解了侄女的选择,“其实套娃也不是非要装进同一个套子里头。”

张子枫饰演的主角安然是独生子女政策下出生的孩子。父亲在她年幼时就想再要一个孩子,于是要求女儿假扮残疾以获得多生一个的指标,被发现欺瞒后,他将怒气撒在女儿身上,一番毒打对安然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她上大学之后,父母坚持要了一个孩子,这个几乎没有见过几次面的弟弟获得了父母的全部宠爱,安然变得边缘化,几乎与家庭失去联系。父母意外离世之后,她无法原谅他们最初的选择,这种被轻视与对爱的渴望,成为安然拒绝抚养弟弟,无法与家庭和解的最大原因。
安然的形象也与传统影视剧中的姐姐形象不同。她强大独立,目标明确,在父母离世之后,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人生与梦想。在大家庭中,她是愧对父母、叛逆、不孝、自私的晚辈,是宁可将弟弟送养也要追求个人梦想的新女性。
有趣的是,影片的结局成为最大的争议之源,对口碑造成一定影响。故事的最后,姐姐与弟弟在相处之中建立了情感联系,通过爱的相互给予治愈彼此,姐姐最后并没有在送养协议上签字,而是带着弟弟离开了送养家庭。批评的声音主要认为,姐姐最后的决择“不够自由”,与她追求个人梦想的初心违背。在一些观众看来,影片的和解也没有真正实现女性呼声,不少观众希望看到这个被父母辜负的女孩能够勇敢挣脱家庭的罗网,到别处展开新的天地。“姐姐凭什么为弟弟牺牲自己的人生?前有《娘道》,后有《姐道》。”
关于结局,导演和编剧都曾提到这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游晓颖认为,告诉女性应该怎么做是不公平的,因为没有面对她的那些矛盾和艰难。“我们从剧本到电影,都不是希望教女性应该怎么生活。一个人或者一个曾经被束缚的生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无论你做什么选择,无论你相不相信,你想选择什么,我们都支持。”
重塑女性形象
近年的影视剧中,能够看到创作者开始对家庭中的女性角色进行反思。无论是《欢乐颂》中的樊胜美,还是《都挺好》中的苏明玉、《安家》中的房似锦,这些爆款影视剧中的女性形象都有着相似的原生背景:生于重男轻女的家庭,作为姐姐被要求无条件支持弟弟的成长和学业,处处体贴和照顾弟兄,以各种物质和精神的形式回报家庭。
这样的女性形象让荧屏前的女观众为之愤怒呐喊:她们强大而独立,却无法挣脱亲情羁绊。家庭伦理影视剧中的女性形象,终于得以从贤妻良母、婆婆妈妈或是歇斯底里中跳脱出来,也是创作者对根深蒂固的“长姐如母”形象的改写。从这些影视剧的热播也能够看出,对姐姐形象的改写与重塑,能够引发更多观众的情感共振。“作为一个同样因为弟弟的出生改变了人生轨迹的姐姐,很多场景、台词、情节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代入感太强。”在看完影片之后,有观众表示。

社会学家李银河撰文指出,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男权的乡土社会,时至今日,社会上还存在着大量重男轻女的情况:从营养、教育、医疗资源到喜爱程度,全都向儿子倾斜,就连媳妇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都会影响到她在家中的地位。这种性别偏好在中国人社会心理中是深入骨髓的。在她看来,《我的姐姐》揭示了在现代化、都市化的过程中,女孩和男孩的人格平等、机会均等问题已经开始大规模进入社会生活,对传统的性别秩序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对传统的社会心理也构成了强大的挑战。目前,传统的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正在发生深刻的改变,一个现代化的男女人格平等的新秩序正在形成。
2017年上映的《相爱相亲》同样是游晓颖编剧,这部聚焦三代女性情感与命运的口碑影片获得了1824万元票房,在当时是一个不错的票房成绩。从与时代互动的关系来看,《我的姐姐》出现恰逢其时。《夺冠》编剧张冀评论认为,这次几乎清一色的女性主创,以勇敢的态度替独立女性发声:“在锋利的外表下,渴望爱与和解,也是对中国人所笃信的家庭主题的一次突破表达,从逻辑上而言,这股子力气也只能发轫于女性。”他同时指出一个现实,不管是男性创作者还是男性观众,都得学着转变和换位,因为今时今日,“听她说”比“对她说”重要得多。
近些年,女性创作者在电影领域表现出色,在国际影展、电影节上锋芒毕露,《嘉年华》《相爱相亲》《送我上青云》《过春天》《春潮》……一批女性主创合作的影片得到了奖项肯定。2021年春节档和清明档,《你好,李焕英》和《我的姐姐》成最大赢家,证明了女性导演、女性编剧在创作优质作品的同时,也能够产生较大的票房号召力。女性观众对部分影片中符号化的女性形象感到厌倦,更愿意为女性导演创造的女性形象买单,对于整个市场和创作环境而言,能够进一步开拓女性创作者的探索空间,帮助创作者得到更大规模资本的垂青,同时为电影市场带来更多的中国女性的好故事。
相关推荐
猜您喜欢
- “盛世如你所愿”——清明之际的追思和告慰
- 复盘丨清明出游人次破亿,留给了“五一”哪些经验
- 4月6日四大证券报精华摘要:清明假期出游需求集中爆发 小众目的地受追捧助推乡村振兴
- 清明假期铁路公安抓获网上在逃人员202人
- 戍边烈士牺牲后第一个清明,令人泪目
- 全国铁路清明小长假期间共发送旅客4991万人次
- 华龙区各社区开展清明节主题活动
- 清明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1.02亿人次 实现国内旅游收入271.68亿元
- 清明假期消费活跃 旅游、餐饮、出行等消费明显回暖
- 盘点清明小长假 | 跨界合作 “体育+民宿”带动旅游新发展
- 清明假期超1亿人次出游 机票酒店预订量双双大增
- 清明假期出游需求集中爆发 小众目的地受追捧助推乡村振兴
- 清明假期“生活归来” 折射消费活力强复苏
- 1.02亿人次! 清明“补偿式出游”需求强劲
- 【网络中国节·清明】“红领巾”跨越山海的祭奠
- 清明假期国内旅游出游1.02亿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271.68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