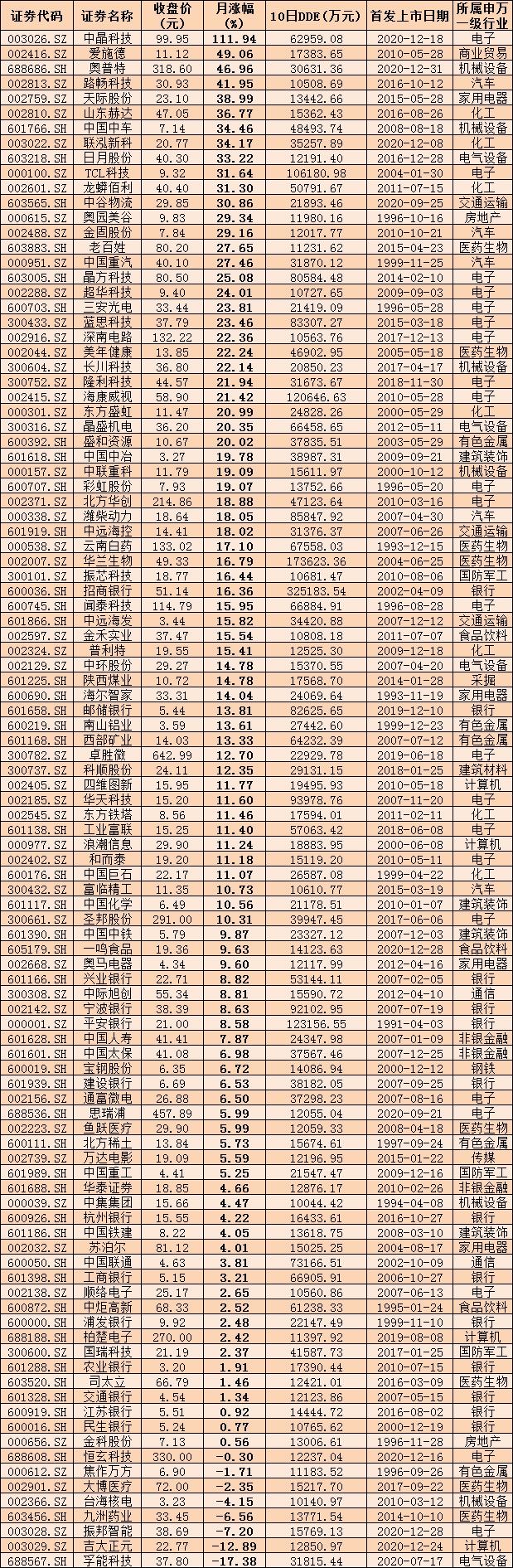租界时期的上海,跑马又如何席卷了在华外国人和华人精英,最终下沉到青帮和市民阶层?张宁在《异国事物的转译》一书中探索的正是其来龙去脉。这部前后写了近16年的著作并不仅仅是要说明跑马、跑狗、回力球这三个运动项目的演变史,作为台北“中研院”副研究员,张宁还希望借此回答一个更广泛存在的问题: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些与西方“看似一样,实则不同”的事物究竟是怎么来的?

第一财经:在这本500多页的书里,你一直以中立的笔调来叙述“转译”的过程,对“转译”前原汁原味的英式跑马和后来成为一种博彩方式的跑马都没使用认同或批评的词汇。而日常生活中,我们谈论很多舶来品时,时常会形容它“扭曲”了,“变味”了,等等。在研究了跑马在近100年的“转译”过程后,你真的没有价值判断吗?
张宁:研究了这么多年之后,我发现这个改变是必然的,一个概念或一项活动,为了适应新环境,它一定会做出修正,谈不上好或不好,也不一定是“扭曲”或“变味”,重要的是它是怎么变的,决定它变的方向的动力是什么。我同时也觉得,这个“变”不仅存在于异国事物进入异文化之后,也存在于所谓“原汁原味”的原版,如果把时间轴拉大,可以看出在那一头它也在配合自身的需求变化,而且两边的变化是可以相互影响的。
过去,我们研究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或者法律制度等,都假设有一个不动的文本,静静地让我们移植或翻译,做完这个研究后,我觉得这些都可能需要重新考虑。
第一财经:不少研究中国现代化的学者都把目光集中在上海。比如你的同事连玲玲,她对百货公司的研究,地点也是在上海。请谈谈你们对上海的关注。
张宁:连玲玲老师是我在“中研院”近史所的同事,也是撰写专书时相互鼓励的益友。我们把目光集中在上海有两个原因,一是上海的确在中国近代史方面占有重要地位,许多事件在这里发生,许多人才荟萃于此,它是新事物进入中国的窗口,也是商业性文化的中心,在地位上堪与北京比拟。第二个原因,在于我们问的问题,譬如连老师的消费文化、我的文化转译,在上海最为明显。你如果仔细看上海的历史,会发现在这么有限的空间、这么短的时间里,居然会出现三个跑马场,或者在连老师的主题里,会出现四家百货公司,大家还都在同一条路上,这是非常惊人的,也是在世界其他城市里难以看见的。这种对异国事物高密度的承受,是让我们关注上海最主要的原因。
第一财经:通过你的研究,我们看到了跑马在租界时期上海的广泛影响力。这项盛极一时的活动为这座城市的“近代化”留下了什么?
张宁:我们现在多半谈“现代性”而非“现代化”。所谓“现代性”,问的是当时展现出什么和过去不一样的现代的特性?如果用纯物质的角度,那就是清末人所说的“声光化电”或茅盾在《子夜》中所说“光热力”。跑马在速度与力量方面的确展现了某种程度的现代性,后来的跑狗与回力球,因为大量使用电力,更展现出“光”与“热”的部分。
第一财经:你在书中写道,每逢赛马,很多妓女和淑女都会出来观看比赛,进而成为被观看的对象。出门观看赛马的是仅限于一些出身买办、西式家庭的女性,还是闺阁女性的普遍情况?
张宁:这一点我也觉得很有趣,除了高级妓女展示性的观赛,还有许多良家妇女或者坐在善钟马房的阳台上或者坐在马车里看,也就是有所遮蔽地观赛。更有一些因为在新兴纱厂里工作,而有一定经济能力的“湖丝阿姐”“摇纱阿姐”出来看赛马。还有一些爱出风头的女性,驾着马车呼啸而过。乍看之下,好像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传统说法不同,但只要想想清末上海租界是个全新的空间,而赛马是好像钱塘观潮一样的活动,是一年仅两次的热闹,有这么多不同阶层女性的参与就不会那么奇怪了。
当今的马术是向上攀爬的文化资本
第一财经:现在中国大陆也有很多马场,尤其在北京和上海这样中产阶层相对庞大的大城市里,把孩子送去学骑马也成了一种时髦。在你看来,如今的马术在阶层塑造上起到了什么作用?
张宁:我想骑马、赛马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家里开牧场或本身就住在草原上,这样的孩子出于生存所需,很自然就会骑马、赛马,同时终生对马匹有一定的情感。另一种是城市人,出于体育的概念送孩子去学骑马,让孩子不怕马,甚至能享受驰骋之乐,这一种我想在任何地方都是一种时髦。台湾也有这样的情形,但为数不多,因为骑马有一定的危险性,即便是成人、老手摔下来的也所在多有,家长必须敢冒险才行。我想能让自己的孩子拥有其他孩子没有的才能或经验,是一种夸耀,也是为孩子长大后往更高阶层发展的准备,在这里,它不是阶级塑造的工具,它是向上攀升的文化资本。
第一财经:我看到你的同事孙慧敏发表在《新亚学报》上的书评,文中说你很爱好体育。你喜欢哪些体育项目,其中是否包括马术?
张宁:我喜欢走路、慢跑、做瑜伽、打网球及打太极拳,慢跑是从大学以来的习惯,一般可以跑4000公尺,太极拳则是最近这几年新学的活动,这些都很有意思,能帮助自己放松。我一般一周慢跑三次、上一次太极拳课。至于马术,因为涉及马匹、场地与教练,不是一般人可以从事的休闲,电视上有时转播欧洲马术比赛,我也喜欢看,但仅仅只是观众。
第一财经:在研究西方事物在中国的转译时,你为什么会选择以“跑马”为切入点?
张宁:跑马是通商口岸生活里很重要的一项活动,不论是外侨还是华人都会参与,占地广大的跑马厅又是帝国主义的象征,有许多争辩与冲突,加上它的转译过程还没有真正完成就因政治因素而中断,大家对它始终都存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是研究文化转译非常好的切入点。
第一财经:这本《异国事物的转译》在你的历史研究经历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张宁:这本书是我研究履历中非常重要的一章,因为它是我的第一本书,过去我一直写的是单篇论文,主题虽然明确,但不容易铺洒开来。这本书对我的另一个重要性,是它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可以继续发展。近代中国传入了很多新的结社方法与形态,用英文讲大概包括club、association、society,老上海的华洋菁英毫不客气地用这些新组织来建构他们的人际网络,其中的俱乐部更改变了城市人群的休闲方式。我打算未来继续以上海为案例,写一本和俱乐部有关的书,进一步展开我对文化转译的论述。

《异国事物的转译:近代上海的 跑马、跑狗和回力球赛》
张宁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启微 2020年8月版
相关推荐
猜您喜欢
- 年后重要股东净增持62家公司 两因素促产业资本“买买买”
- 国融证券董事长侯守法:对未来资本市场改革有三大期待
- 发挥资本市场作用 为创新企业提供多层次融资服务
- 社保基金迎1.68万亿元国有资本“进账” 划转国有资本运作管理办法落地可期
-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陈雳:让资本市场更好地“输血”实体企业 实现高质量发展
- 资本市场要成为“二师兄”主心骨
- “十四五”服务绿色产业发展 资本市场三方面助力转型升级
- 去年北向资金净流入超2000亿元 资本市场持续开放增强对外资吸引力
- 资本为何带不动民营医院?
- 一手退市新规一手注册制改革 打造资本市场高质量“出入口”
- 国产新冠疫苗正式上市 资本逐鹿千亿元市场
- 刑法修正案筑起保障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法治体系
- 资本市场再迎长期增量资金,3万亿年金投资范围大扩容
- 见证资本市场三十载辉煌“退而不休”心系改革发展——专访中国证监会北京证监局原副局长姚万义
- 推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再上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