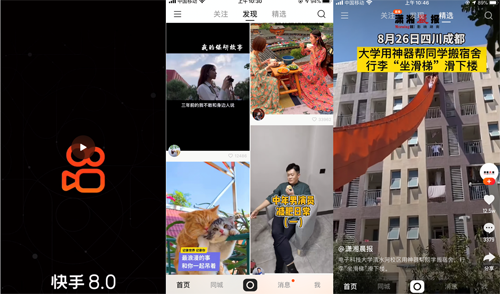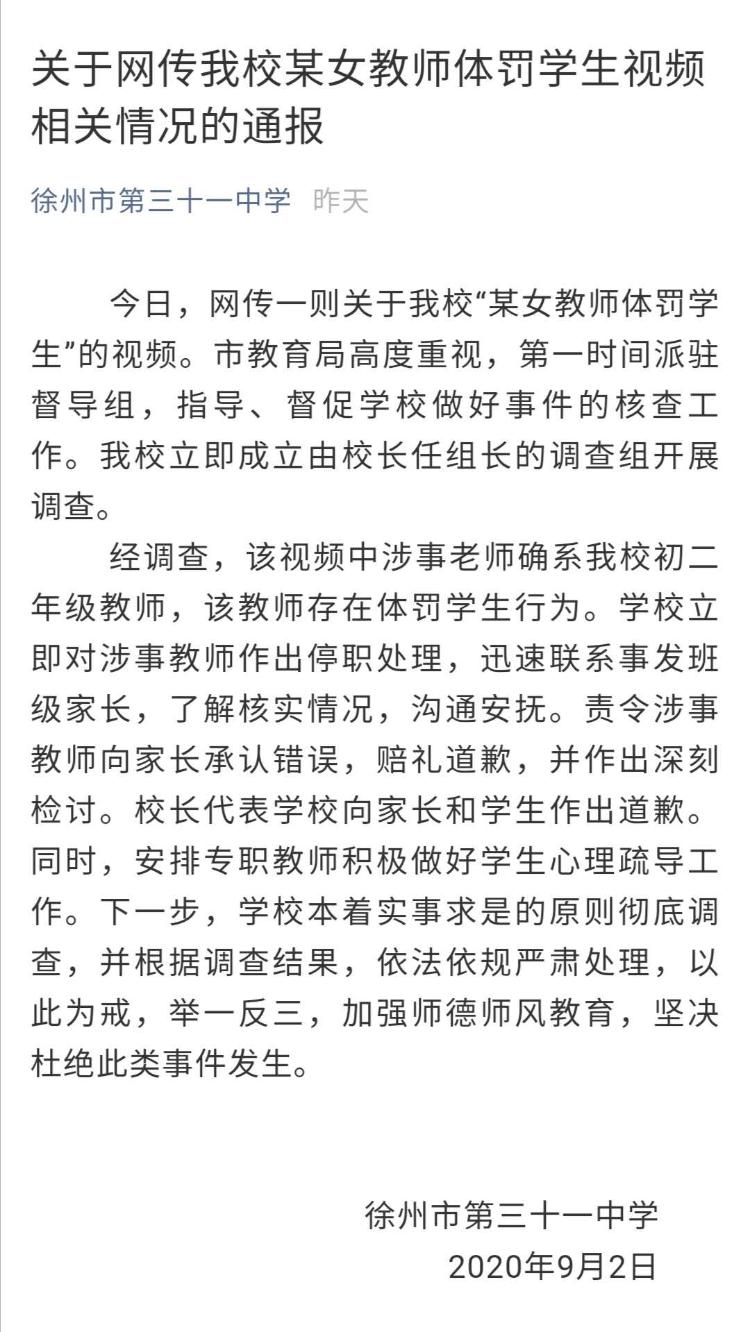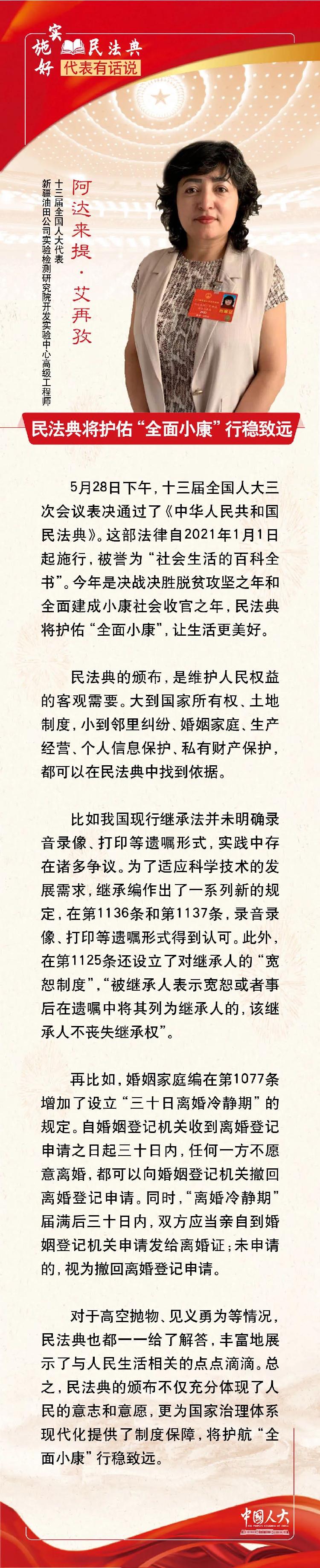每年一到高考季,与科举相关的话题关注度就连带着上升,尽管两者性质完全不同。
的确,抄袭、顶替、户籍“移民”,高考中的这些“弊案”,早在科举时代就见怪不怪;“状元”、谢师宴、喜报,每当成绩公布,各地热闹程度也与科考放榜相去不远。可以说,尽管科举制度100多年前就已终结,但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正是因此,日本著名史学家宫崎市定在《科举史》中指出,“论及中国民族性的本质时,也必须将科举带来的后天性一并考虑进去”,“谈及中国,就不能无视科举”。“宫崎市定写的不仅是一种考试制度,而是把科举制度放在官员选拔的角度来考察,对重新看待科举制很有启发。”《科举史》译者、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研究员马云超说。
二战期间的“遗稿”
《科举史》的出版过程比较曲折,最早写于1939年,5年后才有出版社有意出版。1945年春天,宫崎市定加以增补时,日本战败已成定局,但军国主义政府还想作垂死挣扎,他身边很多同僚和朋友都被征入伍。44岁的宫崎市定预感不久后自己也难逃厄运,就加快了修订与写作的步伐。果不其然,他刚刚完成全书修订,就收到召集令状,“当时都做好将这本书作为生前遗稿的心理准备”。
《科举史》原稿交付秋田屋出版社后,就发生了大阪大轰炸。出版社化为废墟,只有一号金库留下了燃烧残余。原因是大轰炸前夜,社长似乎有预知般在金库下面放了一杯水,才使得少部分地方没被完全烧毁。金库冷却后,工作人员打开大门,发现《科举史》的手稿恰好就在那杯水附近。
1946年,《科举史》终于出版,但又“生不逢时”。当时日本战败,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民众食不果腹,谁还有心思去了解异域的一项古老制度?书出版后销量并不好,不久,秋田屋出版社也倒闭了。
1963年,宫崎将《科举史》中关于科举具体流程的部分章节加以整理润色后,换了一家出版社,以《科举》为名出版。为了区别于《科举史》,《科举》一书加了副标题“中国的考试地狱”。直至1987年,完整的《科举史》原作才有机会在日本再版,此时宫崎市定已是86岁高龄。
近年来,中国越来越注重“他者的眼光”,域外汉学研究很受关注。与史景迁等人一样,宫崎市定的历史写作通俗易懂,引起了一股译介热潮,中译本已有二三十部之多。马云超解释“宫崎热”兴起的原因时说,除了能把学术著作写得“火星人都能看懂”,他的视野还非常宽广,尤其注意把中国史纳入世界史范围,让读者清晰地看到当时中国与世界的互动。
尤为关注落第考生
每当有高考作弊或者顶替之类的丑闻被曝光后,很多人就会提到科举时代对舞弊者的严厉惩罚。
《科举史》中,宫崎市定也花了相当多篇幅讲述科考作弊手段、著名的科场舞弊案以及对舞弊者的惩罚。
但是与破坏公正性的科场舞弊相比,宫崎市定更关注落第考生的安置问题。在他看来,落第考生一旦处置不当,对王朝统治会产生更大破坏力。这是因为,随着中古贵族制度的瓦解,科举成为士人求职的第一步。尤其从宋代开始,随着科举制度成熟,考生越来越多,但录取率始终非常低,每次科考结束就意味着大量考生落榜,有时落第者甚至多达上万人,“出身贫困却又抱着万分之一侥幸从事举业的人,如今改变职业也来不及了,有气概的人流落到国境附近等待机会”。这些人一旦得不到妥善安置,很可能就会引发社会动荡,进而影响王朝统治稳定。宫崎市定敏锐地指出,类似的历史进程,从唐朝末年到宋元明清,在华夏大地上一再重复。
科举制度虽然早就走向历史终点,但是读完《科举史》会发现,它对国人心理上的影响依然不可小觑。近几年,教育部虽然三令五申不许宣传“高考状元”,但每年高考成绩一公布,各省市“状元”“榜眼”“探花”的名单依然在第一时间快速流传开来。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学校、地方政府或企业对“状元”的奖励更是能达到上百万元,这时的考生家庭大概也能感受到几分“金榜题名”的荣耀。
另外,高考中的一些加分政策,也脱胎于科举时代。比如清代有“难荫生”,是指二品以下官员除了战死,因公事在外海、大江大湖等溺亡,或因军务以外的公事病故,给予其子孙以特殊恩典。“就抚恤家属而言,基本思想上确实是一脉相承的。但在具体的做法上仍有区别,难荫生是不通过科举考试,直接授予官职。而政策性加分是建立在参加高考的基础之上。从这一点而言,现代社会显然更加注重公平性。”马云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