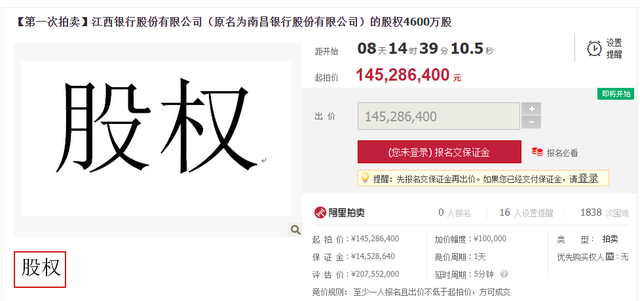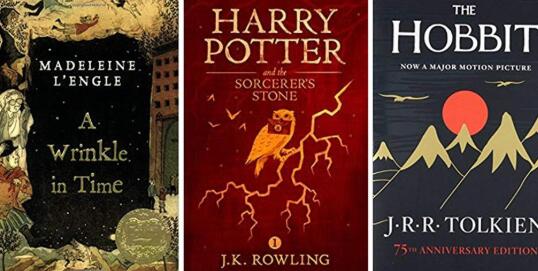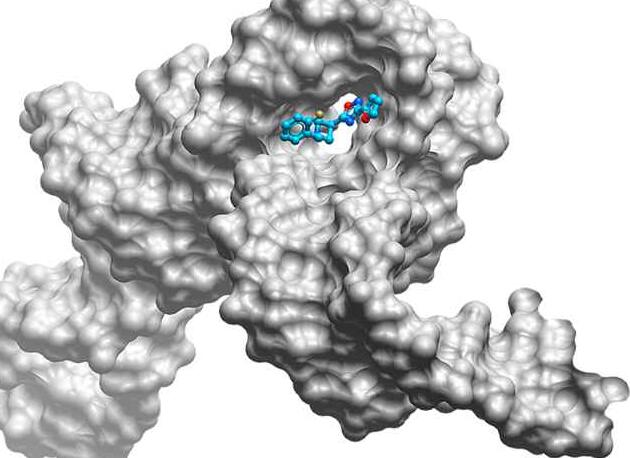新冠肺炎疫情对就业市场的冲击前所未有。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测算,我国已有超过1亿人的就业因疫情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有约400万新增的失业者,2600万因疫情原因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还有7500万休假不上班的人。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表示,虽然调查失业率上升的幅度不大,但判断就业形势不能只关注失业率,而是要将多个就业指标综合起来进行分析。目前官方公布的数据已经充分反映出疫情对就业的影响,这也是中央政治局会议将“保居民就业”置于“六保”之首的重要依据。
曾湘泉认为,就业问题本质上是经济问题,就业是否能出现反弹取决于宏观经济恢复的情况。下一步就业走势与国内防疫的方针以及国外疫情的发展密切相关。目前当务之急是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稳定现有的就业存量,如加大失业救济力度,尽快给予低收入者现金补贴等,以防止更多就业质量不高的人下沉为失业群体。

疫情波及超1亿人就业
第一财经:国家统计局公布3月调查失业率之后,不乏质疑之声,认为经济下滑6.8%,但调查失业率环比却不升反降,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调查失业率失灵了吗?
曾湘泉:自2018年公布以来,我国调查失业率变动总体上与宏观经济的变化趋势保持了一致,现在的问题是出在变动幅度上。我国GDP从去年末的6%下降到一季度末的-6.8%,下降区间已近13%,这是改革开放以后从来没有的情况,但是调查失业率却只比去年同期上升了0.7个百分点,并没有充分反映出GDP下滑对就业的冲击。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之后,有人质疑调查失业率的真实性,并自行推算出更高的失业率,这种对于失业率的判断是缺乏专业依据的。我们也要看到调查失业率所面临的两难境况,世界上有180多个国家采用了这种劳动力调查的方法,若我国不采用国际指标就会失去标准。
同时,失业率指标不是万能的,这套国际指标在调查发展中国家失业率时普遍出现失业率偏低的情况。为了找到更多的失业者,我国已经将失业搜寻期从国际通行的4周延长到了12周,如果完全按照4周的标准,我国的调查失业率会比现在更低。
在我看来,调查失业率本身的变动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对就业市场的判断不能依赖失业率单一指标,事实上也没有一个单一的数据能全部反映就业市场全貌,因此就需要将就业、失业、退出劳动力市场(not in labor force)等多项指标来进行综合的判断。
当前的疫情不仅导致了失业,还导致更多人的就业受到了影响,比如他们的工资、福利、工时等都有减少,这部分人虽然没有失业,但就业质量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如果疫情持续得不到缓解,这部分群体中就必然会有人下沉为失业者,我国的调查失业率就可能进一步上升。

第一财经: 4月2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另一组数据,城镇就业人口下降6%,还有18.3%处于休假未上班中,你能否帮我们测算一下,这两组数据分别影响到了多少人口?
曾湘泉:这是两组特别有价值的数据。尽管抽样调查用相对数推绝对数存在统计偏差,但大体还是可以看出疫情对就业产生的冲击。这也提醒我们,疫情对就业的影响不能只限定为那些失业的人,它对于就业的人也产生了影响。
以2019年末我国城镇就业人数总量为4.4亿计算,城镇就业人口下降6%即2640万人。这部分人就是我们所说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即没有工作意愿,或者有工作意愿但没有工作搜寻行为的人。我判断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工,他们因为疫情的原因返乡了,不能算作失业,但疫情确实影响了他们在城镇的就业。
“18.3%处于休假未上班”人口的推算方法是4.4亿城镇就业人口减去上述的2640万,然后再乘以18.3%,得出的数字是7568万人。这些人都是单位就业的人,处于休假未上班中,他们可能仍然领工资,并未失业,但他们的工时、工资、社保等都可能受到影响。
因此,在分析疫情对就业影响的时候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失业人口,按照调查失业率同比上升约一个点计算,新增了400万人左右;二是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口,即城镇就业人口下降6%;三是受到影响的就业人口,即18.3%处于休假未上班,后两者相加后初步计算涉及到的人口约有1.02亿。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群体,也说明了GDP下降了13个百分点后对就业确实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同时还要强调一点,国家统计局的劳动力调查是以常住人口为口径的,包括在城镇的2.8亿农民工,现在所谈的疫情对就业市场的冲击已经包含了对农民工的影响。

失业定义有一套严格的国际标准
第一财经:据了解,“休假不上班”的人群中已经出现了无薪休假的情况,他们实际上没有收入了,为什么没有算做失业者?
曾湘泉:我国调查失业率是按照国际标准建立的,劳动力调查也是按照国际通行的方法开展的。社会对这个数据的质疑,一方面是因为对我国劳动力调查制度的不了解,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失业定义有一套严格的国际标准,并非民众所认为的短期内没有收入就应被认定为失业。
国际通行对失业者的定义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标准:一是没有工作;二是如果提供工作,愿意并且有能力工作;三是在调查周的前4周内积极寻找过工作。只有同时符合这三项条件才能被认定为失业,如果一个人没有工作也不愿意积极去找工作,就不能被划入失业者的范围。
国际上对就业者的定义是指在调查周内,至少有一个小时的付酬工作。同时还提到一个人有工作但因为休假、疾病、天气或罢工等原因而暂时离开也被认为是就业者。
从失业和就业的定义中可以看出,疫情中休假的还是属于就业者,即使是无薪休假的人也不符合失业的定义,是算作有工作的人,一旦经济恢复,企业就可以叫回来上班。
这种情况在中国尤其常见,经济一变好,很多企业就面临招工难,所以企业一般不采取裁员的方式来进行调整,而通过工资来调整。中国实行的是浮动工资制,企业可以为员工缴纳社保,或是发放最低工资来取代裁员。浮动工资为避免就业刚性迫使企业裁员提供了一个有效缓冲。
失业率和收入有相关性,一个国家失业率高,肯定会影响居民收入,但两者不是简单对应的关系。就业或失业测量的是劳动力面向市场的状态,也即劳动力资源利用的状态,而不是人们的生活水平。甚至就是无收入和负收入都可能处于就业状态,比如做生意的人可能是赔本的,收入为负,但是他们也是就业的。所以就业的要件是为了取得收入和报酬,并不是一定能取得收入和报酬。
现在受到疫情影响,大家没有收入就觉得自己失业了,这是失业理解的范围太宽了,而统计上的失业是有严格界定的。当然,这也反映出了调查失业率的局限性,一直以来我都在呼吁就业统计时引入就业质量指标,来全面反映劳动者的就业状况。
下一步希望国家统计局能进一步完善就业信息发布,比如公布劳动参与率的情况,落实十八大和十九大一再强调的推动实施更高质量的目标和要求,研究发布就业质量统计指标,包括工时、工资、社保、劳动合同、工作稳定性等,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当务之急是稳住就业存量
第一财经:政治局会议已经提出了“六保”,保居民就业成为“六保”之首,地方已经陆续开始启动投资项目,以拉动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你认为当前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扩大就业?
曾湘泉:当前首要的问题不是扩大就业,而是要稳住存量。对于就业问题要高度重视,不要以为调查失业率只有6%就掉以轻心,受到疫情影响的这1亿人,虽然还不属于失业者,但他们的就业质量已经下降了,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来稳住这些就业存量,他们将很有可能下沉为失业者,我国的调查失业率将会迅速上升。
现在救助体系、逆周期调节政策所发挥的作用都不足,因此当务之急是加大对这部分低就业质量群体的救助力度,这么做不仅是让他们免于贫困,而且可以提升总需求。目前各地发放的消费券主要解决商家就业的问题,对于低收入者来说作用不大,更好的做法应该直接发给他们现金补贴,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作用要大于高收入者,这对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增长都有帮助。
目前低收入救助体系首先要解决“发给谁”的问题。国家已经在网上进行失业登记,下一步还应该建立一个低收入者申报体系来直接给低收入者补助,也可以委托腾讯、阿里等大公司,借助微信等技术手段尽快把这套系统建立起来。
就目前企业的经营状况来说,仅靠企业的力量来稳住当前的就业岗位是较难的。一些娱乐、旅游、线下教育培训、会展等行业几乎停摆,虽然也有免房租、失业保险返还等作为稳岗补贴,但力度太小、时间太短,不足以弥补这些困难企业的损失。在企业经营困难的一段时期内,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划定困难企业的标准,政府按照最低工资标准为企业的员工发放工资。
第一财经:你预计我们的就业形势什么时候会出现反弹?是否存在报复性反弹的可能?
曾湘泉:就业态势最终取决于疫情本身的发展,国外疫情和国内科学防疫是两大影响因素。国内防疫的方针很关键,短期内对劳动力进行管制问题不大,但管制长期化就会造成失业问题。如果要素不能流动,那么政府出台的扩张政策包括给企业发钱,都会难以维持。
在当前就业总量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建议政府在新上投资项目时引入就业评估机制,带动就业多的项目可优先上马,真正把就业优先落实到项目投资上,充分体现“保就业”的政策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