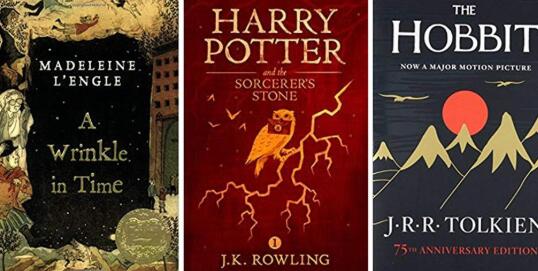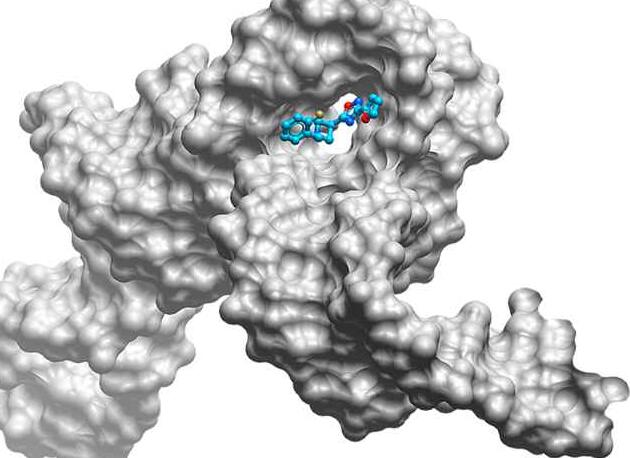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仍以惊人速度攀升,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按下暂停键,社交中断,行业停摆,金融市场惊魂未定,全球经济再现危机时刻。
与1月底对疫情的经济影响作出乐观预测形成强烈反差,3月下旬以来,全球研究机构纷纷调低2020年经济增速预测,很多学者又开始预言这次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堪比1929年大萧条。看来,如何在灾难开始的时候不盲目乐观,而在灾难高峰时不过度悲观,人们还是需要不断积累经验。
我们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本质上是短期外部冲击,所带来的供给冲击与疫情持续时间同步,所造成的需求萎缩也将于疫情受控后三个月内缓解并逐步复苏,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止于2020年。此外,考虑到各国逆周期调控能力,全球经济合作机制,5G和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引领的新供给扩张等多方面因素,本次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程度和时间远远小于1929年大萧条,但短期影响或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和1987年股灾,所造成的经济衰退不是“大萧条”,只是“短萧条”,企业只要千方百计渡过2020年难关,2021年就会迎来新供给扩张周期。
短期经济衰退程度堪比“萧条”
在1月乃至2月初期,很多国内外研究机构都曾参考2003年非典对经济的影响做出预测,认为这次疫情冲击对中国经济增速的影响不过0.1到0.2个百分点。针对这种错误的评估方法,我们曾在1月31日发表文章《评估疫情影响、考虑应对之策,不能刻舟求剑》,强调必须从“新疫情”、“新社会反应模式”、“新的经济结构”来评估疫情影响,呼吁稳增长的应对之策“刻不容缓”。
如今看来,不论是盲目乐观者还是过度悲观者,都是没有找到适当的评估标准,因而或对短期心存幻想,或对长期过度悲观,更有一些甚至影响了决策的及时性。
从“新疫情”的角度看,目前海外疫情仍处于快速扩散期,病毒的传染性超出了各国预期。从“新反应模式”角度看,正如我们1月份研究报告中专门强调的,“新冠病毒影响人们的健康,而真正影响经济的则是为了防控疫情而不得不采取的社会反应模式”,这些不得不采取的防控措施,包括类似中国的社区和出行管控,也包括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禁止举办大型群体活动、禁足令、社交距离、关闭商铺、学校停课、航班减少甚至停飞,等等。上述新的社会反应模式不仅造成劳动力、供应链中断等供给冲击,而且造成交通运输、餐饮、住宿、购物中心、商务活动等服务业的需求萎缩,以及制造业中可选消费品的需求萎缩。
所谓新的经济结构,主要是指中国经济与2003年非典时期已然不同:非典时期消费对GDP的贡献是37%,如今已经接近60%;非典时期中国服务业占比42%,而如今已经上升到54%。此次,消费和服务业不仅是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领域,而且也是疫情结束后复苏最慢的。受疫情影响,中国服务业一季度出现比较严重的负增长;而欧美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占GDP份额近80%,预计在二季度也会出现严重负增长。
正是基于上述“新疫情”和“新反应模式”,本次新冠疫情影响范围之广、引发的社会反应之强、对实体经济的总体影响之大,已远远超过1987年的股灾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
无论是走在纽约,还是伦敦的大街上,现在人们都像是走进了电影灾难片。全球各地类似这样的场景,的确难免让人想起“萧条”二字。
从经济数据看,短期冲击也堪比萧条:1930年大萧条,美国GDP年度增速最低为-23.1%,而现在机构对二季度美国经济增速的预期在-25%左右。事实上,新冠肺炎疫情对很多地区、很多行业的经济影响,在三个月以内的短期冲击都大于“大萧条”时期。
海外机构全面调低全球各地区GDP增速预测

短期冲击不可持续,长期萧条可能性不大
首先,从疫情持续时间上来看,一般三个月到半年,极端情况不会超过一年。中国的疫情防控虽然短期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但无疑是成功的。欧美等国家的社会制度、文化和行为模式虽然与中国有所不同,但是最终也不得不采取类似的疫情防控模式。
中国的经验表明,只要减少群体性活动、减少出行和近距离接触,疫情就会短期受控。以当代人类的认知能力、决策水平和医疗水平,即便考虑部分地区有复发和反复的可能,从社交防控、医药研制、疫苗培育等几个方面预测,疫情受控和社会秩序恢复也不会超过一年。
第二,与“大萧条”时期不同,疫情对需求和供给的影响不会持续。1929年大萧条时期,欧美等国家仍然以前两次工业革命的纺织、铁路、钢铁、汽车等制造业为主,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各产业关联性强、抗风险能力差。一旦出现总体的生产过剩,就会造成大量失业、消费低迷,再加上股市暴跌、投资萎缩,使经济出现了长时期的衰退。
如今全球的产业结构比1929年复杂百倍,不仅有二战以后的石油化工业、通信产业,1990年以后的电子计算机、互联网、通信、现代制药等新兴产业而也不断壮大,知识产业、信息产业、文化娱乐、金融、健康等服务业成为经济的主体,各行各业的供需变化虽然彼此相联系,但此消彼长、遵循各自的规律和节奏,若非疫情这样的冲击,已经很难出现各行各业的供给和需求同时向下共振的情况。
本次虽然从现象上出现了罕见的各行各业供给和需求同时断崖式下跌,但背后的原因却与1929大萧条截然不同。由疫情防控造成的短期供给冲击和需求萎缩,既不是不可逆转的总供给严重过剩,也不是不可逆转的总需求不足。相反,一旦疫情受控,供给短期即可恢复,需求也会在三个月到半年时间内逐步复苏。
第三,各国政府的逆周期调控能力与国际合作不同。经历过二战以后几十年的逆周期管理经验积累,尤其是美联储经格林斯潘、伯南克两届主席日益精准成熟的调控艺术积累之后,2020年,面对本次新冠疫情的经济冲击和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各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反映更加迅速、更加协调。这与大萧条时期各国政府缺乏应对经验和应对手段截然不同:彼时,一方面金本位制限制了各国央行发挥稳定作用的空间,另一方面,逆周期货币宽松政策化解流动性风险的经验尚未成熟,也没有使用积极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的一致行动,直到1933年罗斯福新政才逐渐摸索出一些恢复经济的方略。
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全球股市暴跌,各国纷纷及时采取了降息举措和大规模的财政救助计划。比如,美联储3月3日紧急降息50BP;3月15日,再次下调100BP至零利率;3月23日推出无限量QE政策;3月27日,特朗普总统签署2万亿美元经济救助方案支持中小企业和中低收入居民,经济救助规模占2019年GDP比重约为11%。
英国3月10日跟随降息50BP;3月17日,发布3300亿英镑的政府贷款计划,并直接向企业提供200亿英镑的税收减免和资金补助;3月18日,再次降息15BP,至0.1%;3月20日,政府将为无法工作的人员支付80%的薪酬,在最初的三个月里,每月最高2500英镑,经济救助规模占2019年GDP比重约为16%。
澳大利亚也于3月12日宣布一项176亿澳元的财政计划;3月23日,澳洲政府承诺额外提供664亿澳元的支持,累计财政救助规模占GDP比重接近10%。
德国的经济救助力度最大。3月23日,默克尔政府拿出7500亿欧元的纾困方案一揽子计划;3月25日,德国议会授予政府紧急状态权利,允许无限制发债,同意暂停债务上限,同时拟推出一项用于救助小企业和自由职业者的民生政策,计划总预算为500亿欧元,累计财政救助规模占GDP比重高达22%。
各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经济救助措施

数据来源:各国财政部网站,万博新经济研究院
此外,得益于二战以后形成的成熟国际合作机制,面对本次疫情冲击,各国虽然在跨国人员流动方面采取了减少航班、限制非本国居民入境等措施,但国际金融和经济合作非1929年大萧条时期可比。1929年大萧条期间,各国采取了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其中美国的进口平均关税提高到47%。本次疫情暴发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但是几十年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国际经济组织、国际对话机制仍然在发挥作用。面对股市暴跌带来的流动性危机,美国、欧盟等积极进行货币互换合作。在3月26日召开的G20峰会上,各国承诺采取一切措施抗击疫情、保护生命、重振经济。
第四,新技术革命与新供给扩张周期。虽然近代经济史上各国走出经济衰退的方法、路径各不相同,但每一次真正拉动经济走出衰退,都离不开技术创新引领的“新供给扩张”。比如让美国经济彻底走出了1987年股灾后的经济危机的,其实是1990年代的生物制药、新材料、互联网等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新供给不断创造新需求;让美国经济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的,也是3G、4G、智能手机为基础的新技术、新模式所引领的新供给扩张。
“新供给经济周期”理论认为,总需求变化影响经济周期,但站在总需求变化背后的是“供给结构”:当经济体中新供给产业占主导地位,则一个单位的有效供给会创造出越来越多的有效需求,总需求逐渐大于总供给,则经济增长速度自然会上升;反之,当老化供给主导了供给结构,一个单位的供给会创造越来越少的有效需求,结果当总供给逐渐超过总需求,经济增速下行。1929年大萧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前两次工业革命之后的“供给结构老化”所造成的产能过剩。在没有新供给扩张的背景下,即使罗斯福新政出台了一系列复兴和救助计划,从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衰退,也没有办法开启新的经济上升周期。
本次疫情暴发正值新一轮工业革命的起点,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即将迎来“新供给扩张期”。面对这次疫情冲击,凡是前期信息化、自动化技术应用较多的企业,受冲击越小,复产复工速度也比较快。因此,疫情冲击不但不会阻碍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进步,反而会极大地刺激这些新技术的应用,从而使“新供给扩张周期”加快到来。
应对“短萧条”的政策建议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不是“大萧条”,而是“短萧条”,虽然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动荡,进而有可能打击消费、投资,延长经济衰退时间,但毕竟疫情冲击并未伤害社会运行机制,也未恶化经济结构。对企业而言,虽然造成收入巨减、利润恶化、甚至资金流动性困难和供应链中断,但是并未伤害到大部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正如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接受CNBC采访时说的,“比起1930年代的大萧条,当前的危机更像是一场暴风雪或自然灾害。”
那么如何应对“短萧条”呢?
第一,救助、恢复政策出手要快。
虽然本次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比欧美要早两个月,但相对而言,中国在控制疫情方面行动较快,而在出台经济刺激政策方面则表现得更为矜持。这一方面或出于更长期的结构性考虑,另一方面也与决策体制、经济决策效率和决策谨慎习惯有一定关系。一季度各项经济数据即将公布,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个体经营者受冲击而关闭企业、店铺的情况将在二季度逐步显现,因“居家隔离”形式潜藏的实际失业情况也将在恢复正常社会秩序后逐步暴露出来。因此,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无论是救助企业,还是刺激投资、消费,都出手宜快不宜迟。一旦错过最佳时机,中小微企业、个体经营户已经大量关门倒闭,再出台救助政策,就会事倍而功半。
第二,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发挥大国稳定作用。
无论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还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都曾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稳定作用。本次疫情冲击和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发生在近几年以美国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但是反对隔岸过火、以邻为壑,坚持积极推动国际合作的政策,则有利于全球经济,也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3月30日,从上海出发、满载疫情防控物资的商用飞机降落纽约机场,后续还将有几十驾次飞机从中国起飞向美国运送疫情防护物资,类似的中美合作对于全球战胜疫情、稳定全球供应链、提升全球信心、推动经济复苏更是至关重要。
第三,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改革政策要解放思想。
货币政策应继续降准、尽快降息,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相对于欧美而言,虽然中国货币宽松的空间和降息空间都很大,但是由于货币决策部门背着“货币是否流向实体经济”、“是否大水漫灌”等各种实践、理论和舆论“包袱”,在这次全球降息中独自缺席,货币流动性释放力度也相对较少。事实上,在经济面临“短萧条”时,货币政策毫无疑问应该执行逆周期调控的本位工作,果断大幅降准、降息,而不应该自缚手脚于“货币流向微观机制改革”、“房地产调控”等多年不曾实现的“理想”。
积极财政政策要用创新办法打开收支空间。除了调高财政赤字率到3%、发行特别国债之外,若按2019年国有企业盈利的50%现金分红,可增加非税收后入1.3万亿。
改革政策应着力于放松供给约束,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中国的很多行业都存在不合理的资格、专营权、价格、数量等方面的管制政策,其中大部分都是没有及时取消而沉淀下来的“短期供给约束长期化”。此次,为了防控疫情所形成的很多“供给约束”都是权宜之策,疫情受控以后应该尽快取消,全面减少行政计划手段对市场的干预,消除计划经济遗留的“沙砾”,进一步放松对生产要素、各行业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约束,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滕泰系万博兄弟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哲系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万博新经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