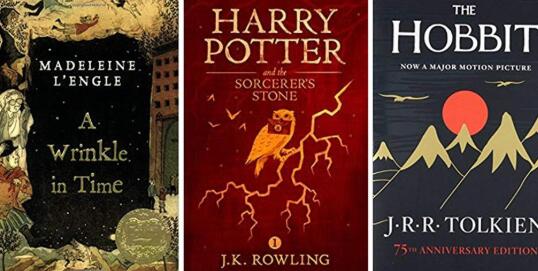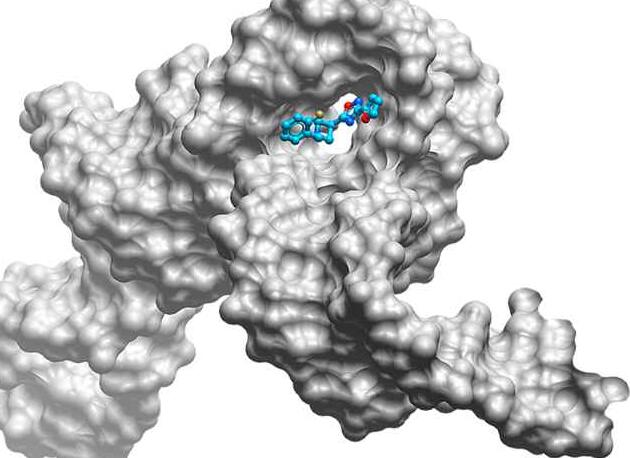边缘往往是了解整体结构的最佳切入点。这一点,不仅对于社会观察是如此,对历史研究来说也是成立的。东北地区(“满洲”)虽然是满清皇室的发祥地,但无论是在清帝国的版图上,还是在清史研究中,可说都处于边缘的位置,而这一地区的环境史,则更是边缘中的边缘;然而,美国学者谢健正是从这里出发,揭示了以往被忽视的帝国政治经济学密码。
长久以来,人们对这一地区环境史的理解,基本上就是一部人类的环境开发史。换言之,它被呈现为原始、丰饶、沉睡的“黑土地”如何一步步被涌入的移民进行农业和林业开发。谢健这部《帝国之裘》所揭示的图景则是其“史前史”,他通过以往无人问津的相关满文、蒙古文文献,发现当地在清末迅速农业化之前,长久保留着的渔猎活动本身就有着深远的意义和更广泛的历史背景。人参、东珠、裘皮这些高附加值的物产,早已嵌入早期全球化的商业浪潮。用他的话说,“到1800年,从蒙古到加利福尼亚的毛皮动物猎手在同一个世界里劳作、面临同样的问题、满足同样的市场需求”。
当然,努尔哈赤崛起时得益于人参贸易带来的丰厚利润,这早已为人所知,但我们可能还是低估了其规模:据狄宇宙估计,仅人参贸易一项,可能就让从日本和新大陆进口的白银总量的1/4流入满洲地区和刚建立的清朝。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朝其实是重蹈了辽朝的覆辙:对边疆女真地区物产的需索,在客观上改变了当地本来原始、分散的社会组织形态,促成了新势力的迅速崛起。这也是谢健忽略的一点:与其说明末清初的山珍贸易更类似北美、俄国那种资本主义模式下的对自然的掠夺性开发,不如说它更接近于中国的传统模式,这又回到类似“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市场需求所催生出来的不是对当地的殖民开发,反而孕育出了动荡和不可控制的敌对势力?
答案或许在于,中国与欧美并不适合作简单的类比,本书虽然做了一些框架比较,但却没有真正深入地比较内在结构与机制。正如《棉的全球史》一书指出的,近代欧洲创设的是一种“向心体系”,其基础是“中心”从它的生产和商业体系中剥削资源和利润;但在传统的亚洲各国,却是一个通过中间商网络进行贸易的“离心体系”,生产和需求的中心并不能掌控各个贸易节点。在此我们可以看到,满清最初的壮大,其实和莫斯科公国的崛起一样,都是掌控关键节点的中间者最终“下克上”颠覆了中心,这是一个逆向的离心体系。
清廷之所以竭力要将人参、东珠纳入内廷管理之下,说到底是因为这关乎政治权力的等级制度,而不仅仅是经济利益。本书强调了人参、东珠、裘皮、鹿茸和蘑菇的贸易在很大程度上符合经济地理学所说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外围地区模式,甚至说努尔哈赤是以“商业资本家”而非简单的猎人身份发家的,这确实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但过度强调这一点也容易忽视另一面:对清廷而言,进贡本身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政治效顺的象征,而这些物品本身也不只是商品,它还有着特定的文化象征意味。
这就是为什么1800年前后野生人参出现减产后,清廷拒绝尝试人工种植人参这一“园艺革命”,反而烧毁种植秧参的农田。与其说这是因为他们愚蠢地认定“没有人参似乎也比秧参好”,不如说是因为他们从完全不同的文化和政治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而不像后人那样将之视为一个经济问题。按经济学的逻辑,如果朝廷完全被利润和财政收益所左右,那就应该建立自己的参场,或将现有参场合法化并征税,但这却是朝廷直至1881年无计可施之后才开始采取的措施。这或许提醒我们,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并不存在一个单独分化的“经济”领域,把一件事单纯看作是“经济”问题,这远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自然而然”,它本身就是社会认知发生变革的结果。
虽然整个东北(尤其在柳条边之外)在清代都被看作是一个很少被人触动的“自然边疆”,但正如本书所指出的:“肃清满洲、蒙古地区的结果并非恢复大自然的原始状态;它反映的是政府的本质。清帝国并不是在保护边疆地区的自然环境,而是创造了它。”也就是说,东北的“自然秩序”本身不是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清帝通过一系列政治管控措施刻意造成的。这一点当然人所共知:因为这里被视为特意为清朝皇室保留的禁脔,长久以来甚至严禁向关外移民,直至清末迫于日俄压境的严酷形势,才转向“移民实边”的政策。
关键的一点是:清朝话语中“净土”,与我们所说的“自然”或“荒野”不是一回事。“净土”颠倒了原先那种“文明/野蛮”的价值二元,将“野蛮”推崇为不受污染的道德力量。如果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对此就不会感到诧异,因为早在道家思想中就认为,上古初民混沌自然的“大朴”状态才是根本,而礼乐名教都是衰世产物。阎步克在《魏晋南北朝的质文论》一文中指出,在北魏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武”是与“质”联系在一起的,帝王在倡导“文治”的同时也须维持刚劲之“武功”,正因此,“捐华即实”“还淳反素”口号所体现的重事功、重法制的实用主义精神,构成了关陇政治文化的基本特色。
考虑到明代的衰亡普遍被归结为某种“文明中毒”,清帝对“满洲之道”和“净土”的捍卫才能让我们理解,那与其说是某种“内亚性”或族群政治使然,不如说是出于统治的前车之鉴。“净土”在此与其说是一个不受人类触动的自然秩序,不如说是一种道德、政治的话语,象征着一个未被玷污的道德秩序,因此淳朴的满人或土著游牧渔猎者也是这“净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这涉及到对清帝国性质的认定:它如何界定、划分和维持一个如此庞大国家的多元性?它是像欧洲近代殖民帝国那样鼓励“教化使命”,还是支持当地土著对土地的所有权?这里复杂的一面在于:清帝本身就出自满族这一少数群体,直至清末慈禧当政之前,朝廷一贯的政策都是严格维持满汉之别,“满洲之道”被视为朴素、纯真和天然的,是帝国生命力的根本所在。正如谢健指出的,清廷本身就反映了两种满人形象:一种突出“自然”和“返璞归真”的本真性,另一种则强调与外界的联系及其适应性、活力和可变性;前者大抵是留在东北老家的那些人(此前所谓的“生女真”),而后者则是更“文明”的(“熟女真”)、最终更容易汉化的那些“八旗子弟”。然而事实上,无论怎么努力试图维持一种独特的、永恒的、不变的特性,如果不能动态地适应外部的变化,那么最终迫于形势也不可能不发生变化。
与其说这种对东北物产的管理体现出某种国家行为,是朝廷或官方的举措,不如说这更多体现的是皇帝的个人意志和特殊利益。人参的专营专卖,都是内廷的机构在管理,其利润是落入皇帝的私囊而非国库,并且向来是清代皇室内廷特供生活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清帝之所以三令五申要将东北保留为“净土”,同样是出于自身统治的考虑,既不是为了维持什么“族群多元性”,当然更不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维持那片“净土”本身。
虽然《帝国之裘》一书在出版后广受赞誉,但在我看来,正是在这些方面,它也存在着以往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所常有的问题。确实,本书很好地体现出挖掘、解读原始满蒙文献的重要性,从更广阔的全球化视角切入中国历史,可以说很好地结合了美国边疆学派、全球史和生态史的话语,带来一种全新的解读;但另一方面,这一解读又往往是在粗率的框架性类比之下进行的,刻意突出了清代政治的内亚性,淡化乃至割裂了与中国思想传统的连续性,有时不免读出一些似是而非乃至莫名其妙的看法。
从中国传统思想的角度来看,清廷的做法既不费解,甚至也不算特殊。固然,历代清帝都严格封禁东北边疆,保护这一“净土”,维护“满洲之道”,但这与其说是出于“多元性”的考虑,不如说是在中国历史上一种根深蒂固的治理思路:不同群体最好“各安其分”,安土重迁,警惕和担心混杂、流动所带来的社会稳定问题,而这归根结底是统治秩序。
正是因此,清朝以前的历代,也都强调不要去扰动边疆族群,以免造成难以治理的纠纷、争讼、械斗等难题。明代对深山腹地苗疆的“生苗”,一向主张“只应以镇静抚驭为主”,法条律例也有“汉民入苗寨之禁”,甚至“汉奸”一词现在通常认为的“汉人之奸宄”一意,最初就是明末用以指称流入西南土司辖境后挑拨生事的汉人。如果没有足够的警力维持秩序,这种相互隔离的状态可能也是避免纷争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很多历史学者确信,美国革命的直接导火索之一,是英国在《1763年公告》中禁止殖民者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建立殖民地,以图制止白人和印第安人之间因扩张而产生不可避免的暴力,但对渴望土地的殖民者来说,这种限制其土地权利的立法无疑是邪恶的。
当然,东北对满清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对它的“净化”不仅是为了避免颠覆社会秩序,还因为这被视为清朝的“根本”。谢健将之与圣山、围场作比较当然是对的:设置一套复杂的监管、巡逻体系,乍看似乎是为了保护被狩猎的动物,但其实还意味着确保这一地区不被扰动。然而,在此值得补充的一点是,这当然不是出于“生态保护”的理念,而意味着这些是保留给皇帝的特权。事实上,对东陵、西陵这两座清代帝陵周围的封禁措施与之如出一辙:直至清亡以前,附近民人对帝陵禁区内任何一草一木的盗采都是重罪。
在这方面,与其将清朝与现代早期的多元帝国相比较,不如将其封禁政策与秦汉时帝王的禁苑、欧洲中世纪贵族对其庄园的封建权利相对比——换言之,整个东北边疆,在皇帝眼里都属于私人产业。在中国,山泽原属国有(现实中则等于是帝王所有),这一制度的崩溃,是因东晋时世家大族开始暗地破坏私占山泽的禁令,最终朝廷不得不承认百姓能合法地取得山林的所有权,正式开禁。在欧洲,帝王贵族对这一特权的捍卫顽强持久得多,而底层民众则越来越强烈地试图打破这种垄断,晚至19世纪中,阿尔萨斯农民之所以对拿破仑一世念念不忘,就是因为他在位时没有《森林法》来禁止农民进入林地。
两相参照,这更有助于我们认识清帝国和清朝皇帝的性质:对东北边疆的所有管制,表面上看是国家行为,但最终都旨在维持皇帝自身的权力;而后来东北向流民开禁,则表明这种特权地位的垄断,最终不得不屈从于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