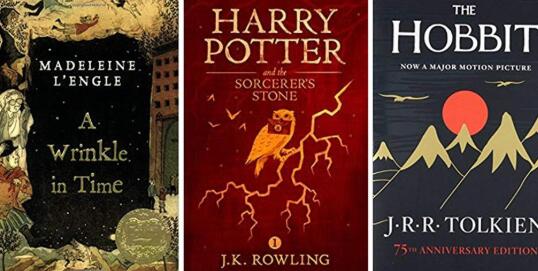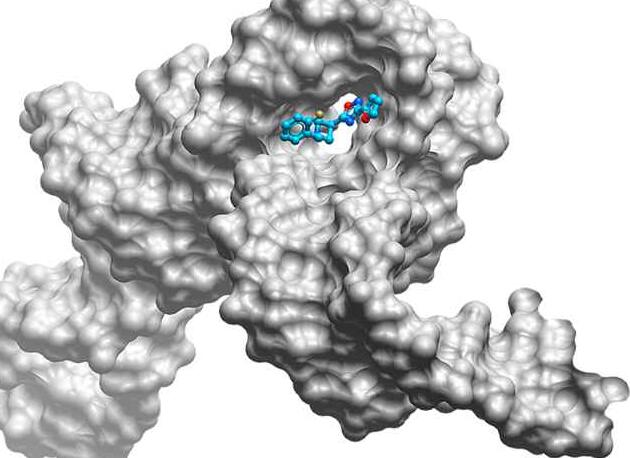20世纪是个残酷的世纪,爆发了两场空前激烈的世界大战(如果加上冷战则是三场),哪怕是原本强盛一时的大国,也经不起再三出错。其中,最弱的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分崩离析,退出了大国的行列;德国在二战中卷土重来,但终于和日本一同战败,虽然经济力量迅速恢复,但政治影响力却一去不复返;最顽强的俄罗斯在一战末期溃败后,居然卷土重来,成为二战的胜利者,但也还是在冷战中被挫败。至于英法,虽然名义上三次都是赢家,但也元气大伤。这样算下来,大国中唯有美国是大赢家,以及一个三次都站队正确的国家——中国。
如果说一战时北洋政府的站队尚不无运气的成分,那么八年抗战则是不折不扣的艰苦卓绝。以中国当时国力之弱,竟能在内忧外患面前挺立如此之久,不仅出乎敌方预料,甚至中国人自己起初也没有想到。自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国民政府一直向民众灌输一种看法,即抗战在三年内无论如何必定会有一个了结,然而三年期满,终点依然遥遥无期。虽然很长一段时间中,中国的策略是“苦撑待变”,但“苦撑”也得有资源可以撑住,而“待变”也不能只是消极等待天上掉馅饼,这都意味着,只有以高明的战略善加利用国际形势,才有可能迎来最终的胜利。
因此,“八年抗战”并不像很多人下意识以为的那样,仅仅是一对一地和日本鬼子搏斗了八年,背后有着极其复杂的大国博弈。邓野的《蒋介石的战略布局(1939-1941)》便是将当时的中国放到国际关系的构成演变下来观察,以此证明:从德国入侵波兰(1939年9月)到日军偷袭珍珠港(1941年12月)这两年多时间里,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阵营的逐渐形成,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抗战的最终结果;而作为当时领导人的蒋介石,其大局判断和战略视野,在其中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其中首要的一点,是中国虽遭受重大挫败,但国民政府始终拒绝日本的和谈条件。当时很多人基于国力的强弱,都判断中国难以进行长期的抗战,甚至一些始终忠于蒋介石的高官,在1938年后都曾加入所谓“和平倡议”;然而尽管日本在战争期间对华发出多达29次和谈要求,却无一成功。这固然与蒋介石顽强、坚忍的意志有关,但部分地恐怕也是因为日方愚蠢的谈判策略所致:他们坚持要求和谈的先决条件是蒋介石本人下台。
从一开始,蒋介石就相当清楚:中国作为弱国,争取更多有力的盟友,将中日战争国际化,“置国命于世界总决算”,是解决困境的唯一出路。然而正如邓野指出的,战争爆发后相当长时期内,“理论上分属两条阵线的几个世界大国,实际上大都存在程度不等的、互为交叉的模糊关系,某种情况下,某国可能是反侵略者,某种情况下,某国又可与侵略者相互妥协,甚至合作”。对中国而言,这是极为现实的:中日战争爆发之际,中国武器和军援的主要来源是德国,而德国的立场却越来越倾向于日本,“理论上”应和中国站在一边的英法苏则无视中国利益,中美关系也若即若离。
虽然也有一些判断失误,但蒋介石当时的整体谋略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欧洲战场开打后,日本虽然一度表态“不介入”,但最终却按捺不住,想抓住英法被德国削弱这一难得的“机遇”,在东方攫取利益,而正是这一点最终将它拖入了与美国的决战之中。珍珠港事件之后,原先的交叉模糊状态不复存在,两大对立阵营最终成型,中美英苏四大国联合反法西斯的阵线由此确立——众所周知,这是中国近代屡次挨打之后,首次被国际承认其大国地位,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席位也是由此而来。
不可否认,这期间蒋介石的战略眼光比日本政治人物要高出一筹,因为在这样不断动态变化的复杂国际局势下,谁都没法总是那么算无遗策,有时对手的出错甚至无形中更为重要。然而,日本之所以走向这样一条军事冒险的道路,却并不只是蒋介石以为的“倭人气短量窄,事尚彻底”这类民族性的笼统判断这么简单,甚或归结为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好虚名”所致,因为日本战时决议是内阁多方合力博弈的结果,远不像蒋本人在中国的权力决策中可以起到那么关键的作用。从历史上看,很多重大决策未必是前后一贯的深谋远虑,高层内部往往有严重的意见分歧和各种势力争夺,最终的决策甚至是事前无法预料的。蒋介石虽号称“知日”,但在战略决策中,倒不如说是凭己意揣摩,乍看高明,其实不过是误打误撞“猜对”了而已。
如果追溯过往,就能看清楚,日本在当时的军事冒险,乃是一战后东亚旧有国际均势崩溃的结果。在此之前,美国所倡导的“门户开放”政策之所以能有效协调各方利益多年,其基本前提是列强相互制衡,当时的日本也只是列强中的一个小伙伴。但一战之后,俄国自顾不暇,英法也元气大伤,在东亚遂形成日本和美国独大的局面,而美国当时却又陷入不肯担负海外重责的孤立主义情绪之中,这就给日本造成了独霸的机会。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更进一步明确排除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并在它的诉求遭阻碍时,不惜高调退出伦敦裁军条约和国际联盟。
这种种局势发展,就不只是日本的“民族性”或某个首相的个性所能决定的了。从战时情形来看,日本外交努力的方向是确保自己能不受阻碍地行事。也就是说,在日本高层的潜意识中,“结盟”和退出国联这样的举动一样,都是确保单边主义的手段,以便最终单独解决中国问题。1940年的轴心国结盟,与其说是为了寻求德国和意大利的实质性配合,倒不如说是为了“吓阻英美干预,排除其对日本行动的牵制”。这种独特而强烈的单边主义逻辑既与日本文化的孤立性有关,更受东亚国际局势的失衡推动,而日本近代史上的独特经历也深深地影响了其战略思维:日俄战争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一直被日本高层视为奇耻大辱,因而他们几乎一致谋求不受干预地单独行动,也就不难理解了。
日本与德意签署轴心国条约,中国这边洞若观火,立刻看出此举是自我孤立、重大战略失策,胡适说自己对三国盟约“天天期望”,王世杰称“引为大慰”,蒋介石干脆说“求之不得”,日本为何偏偏不明白?并不是他们多么愚蠢,而是权衡的重点本来就不同:日本高层觉得与“英美鬼畜”利益不兼容,已是敌人,断绝也谈不上损失,倒是可以拉上德意助阵,使英美投鼠忌器。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何日本会一头栽进战争泥潭中:因为这种单边主义思维的盲点,便是只看到尽力排除阻力,却无法理解国际政治中同样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成正比”,正是其鲁莽暴走的一意孤行,为自己增加了敌人,最终遭到毁灭性打击。
或许也正因一味从所谓“民族性”和领导人性格意志这类神秘倾向的因素去揣测,而未深切意识到当时国际权力格局的复杂交错与日本的单边主义逻辑,蒋介石才不止一次出现严重误判,例如直到卢沟桥事变之前,他一直认为日苏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大于中日战争,甚至直至1939年都坚信日苏大战无可避免;也从未想到日本竟敢偷袭珍珠港,主动攻击美国。反过来,正如齐锡生所言,“日本人完全没有预料到蒋介石的个人因素”,可以说,日本的政治结构使他们低估了领导人的个人因素,而中国的政治传统,却让蒋介石高估了近卫首相左右政局的影响力。
从其对局势的判断看,蒋介石虽呈现出一个政治家的素养,并不单纯从军事角度来看待问题,然而他做出大判断时,却常常偏好主观的单一因素,且完全从中国自身着眼。这固然无可厚非,却会影响他的判断。比如他把日军南进的目的看作是为了解决中国问题,美国转变对日态度是因中国外交努力,但正如宋子文1940年10月呈交的报告中所言,美国之所以默认美日战争无可避免,并非由于同情中国,而是由于世界其他地区情势的转变。同样,蒋介石判断德国将侵苏,理由也仅仅是为了发挥德国陆军的优势,苏德战争的逼近是因“今日已非理智与常识所可测度”。这不仅将盘根错节的结构性因素和决策机制简化,甚至都诉诸神秘因素。当然这种“唯意志论”本身不失为认识蒋介石这个人物的关键之一,但研究著作过分注重他个人的判断,却可能使我们看不到历史更复杂的面向。
这也是本书潜在的问题:虽然清晰梳理了蒋介石当时的战略思维,但依赖的史料却大抵有限,甚至主要依靠《蒋介石日记》这样不无主观自辩成分的史料,而对日美的材料和著作基本上无所参见。对一部研究战时国际局势的严肃史著来说,这自然容易招致批评,不过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作者特殊的视角与写法——他无意遵循历史研究的一般范式,而是着力于对政治事件进行“复盘”。这是从王夫之《读通鉴论》等以来一直都能看到的中国史论方式:以类似“政治点评”的视角,代入历史场景中,重在点评历史人物施政高下,指点江山,最后重心则落在人物品评上,成功也便归结为政治家的“远见”。这乍看是历史研究,其实谈的是权谋。这样的写法,誉之者或以为干净利落,一针见血,毁之者则或觉其有亏学术规范,甚至不知所云,其优劣均在于此。

《蒋介石的战略布局(1939-1941)》
邓野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