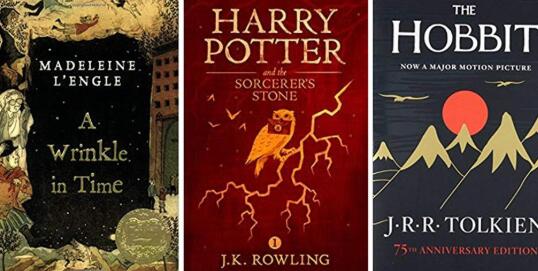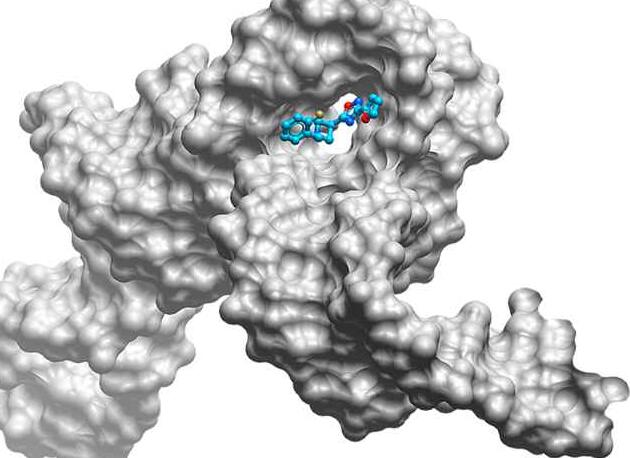《少年的你》票房大热,最能激起话题的,恐怕就是校园霸凌问题了。但把视线仅仅集中于霸凌,恐怕是错过了,也稀释了它更深刻的地方。在我看来,它的重点其实更在于残酷竞争的成人社会对少年世界的全面入侵。公然的集体性的霸凌(区别于某种幼年正常的动物性的残忍)背后不总是成人社会建制化的、区隔性的暴力?不总是成人假“爱”之名所行之自私,在不断给少年们形成中的世界观以背书和扭曲?
不妨对照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的自传体小说《男孩》和《青春》,来看看这种成人社会对于少年的真正的“霸凌”。

成长小说
“等你有了自己的孩子……到那时候你就明白了。”
在《男孩》接近结尾的地方,库切让母亲说出了这句话。这句话大概每一位母亲都至少会对自己的孩子说上一遍。在比较极端的情况下,比如说我的记忆里,这样的话我妈对我说过成千上万遍。当然,这是因为说了没用,只好再说。没用的理由,正如库切所写的:“他会明白什么?是她那老一套生活?那是自古以来人生的必经之路?也许每一代人对下一代说的都是这一套,既是警告,也是威胁。可他不想听。等你有了自己的孩子。真是胡说八道,真是自相矛盾!一个孩子怎么会有孩子?”
正是这个表白,让《男孩》和一般的成长小说区分开来。
说起成长小说,就会想起那些在我“成长”的年代最喜欢的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威廉·迈斯特》《彼得·卡门青德》《大卫·科波菲尔》《约翰·克利斯多夫》《天使,望家乡》。这些成长小说大约有两个共同点。一是大多带有自传性质,二是基本都是作家很年轻时候的作品。《少年维特的烦恼》完成于1774年,歌德时年25岁;《威廉·迈斯特》稍晚,但也是在1777年就开始构思、动笔了;《彼得·卡门青德》曾是我最喜欢的成长小说,27岁的赫尔曼·黑塞凭借它一举成名;《天使,望家乡》同样是托马斯·沃尔夫的处女作,出版时他才29岁;完成《大卫·科波菲尔》的狄更斯和完成《约翰·克利斯多夫》第一卷的罗曼·罗兰,年纪稍大,都是38岁,但对小说家来说,也还相当年轻。
可能正是因为“年轻”,几乎所有这些成长小说,都对“成长”这个主题抱有一种终极的乐观态度,即使赫尔曼·黑塞、托马斯·沃尔夫那充满时光逝去年华不再的哀婉文字,骨子里依然是掩饰不住的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一种强健的生命力贯穿着他们最忧伤的爱情故事;极端如维特的戛然而止,谁又看不出其中狂飙突进时代的强大意志?——死了一个维特,自有无数维特来把旧世界颠覆。然而所有这些,在库切的《男孩》,那个被包装成成长小说的文本里,都告阙如。
反成长小说
《男孩》是库切1997年的作品,那年他已经57岁,它的续篇《青春》,更是2002年62岁时的作品。库切没有在自己的青春“现在时”或者“正在过去时”写自己的成长经历,他把它们埋藏到了功成名就的“耳顺”之年。就这一点来说,它就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成长小说,甚至都未必可以很顺当地把它归类为“小说”。它似乎更接近于老年萨特的《词语》那样说不清道不明的文本类型。在这样的文本里,某种追根溯源的自我反思、自我解构的企图,要远远超过成长小说中自我表达的叙述热情。事实上那更像是一种“反成长”小说,虽然同样借助于自传材料,但与成长小说中的乐观和憧憬截然相反的是,它们要表达的不是“成长”如何能够以启蒙式的热情达成一个人的“自我实现”,而是一种“前成长”的阴影如何将它阴郁而强大的影响力贯穿人的一生。
库切笔下的“他”,既不是成长小说里从懵懂中历经磨难渐渐领悟人生真谛的约翰·克利斯多夫们,也不是《铁皮鼓》里那个自行“拒绝成长”的奥斯卡。奥斯卡虽借助“天意”,因事故而停止成长,但他对此是满意的,并且加以运用。童年某种意义上被作为一个伊甸园,用来映照丑陋的现实——成年人的世界。然而奥斯卡式的“拒绝成长”具有太多的“自主性”,果然,他也可以在某一天自行决定:现在该长大了。库切通过反对“母亲”那句极具“普遍性”的话,即“等你有了自己的孩子……到那时候你就明白了”,来反对一种关于成长的意识形态。他既反对成长小说过于乐观过于“自主”的成长,想必也不会赞同君特·格拉斯同样过于乐观过于“自主”——只不过反了个方向——的“拒绝成长”。
在库切那里,成长是“被拒绝”的。母亲用“爱”,父亲用冷漠,亲戚用疏远和轻视,老师用职能和地位,农庄用它的陌生和他人的所有权,所有这一切代表着成人世界的东西,都以“亲人”、“长辈”或者是他们的“关怀”的名义,在实际上拒绝“他”的进入。当然,在成年人和他们的世界看来,“他”还没有这个资格,要通过成长小说里的“成长经历”,来获取通行证。这个成长经历就是一个模式,具体的“成长道路”可以千差万别,模式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获得成年人的首肯。
成年人永远不会费心去理解“男孩”的逻辑:“等你有了自己的孩子。真是胡说八道,真是自相矛盾!一个孩子怎么会有孩子?”但这是一个如此有力的逻辑。孩子的准确定义,就是那个不可能有自己孩子的人!所以他就是不应该像一个有孩子的人那样去行动和思考。孩子就应该有自己的世界,他们也在试图积极地构造他们的世界。如果成年人不那么偷懒,不那么傲气十足,而是多费心去理解那个世界,并想办法更好地在两个世界之间进行一些细致的衔接——毕竟孩子总还是要“长大”的——这样不仅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实际上很可能也有利于成年人对自己的世界的改造。
自私的爱
但是库切发现,要成年人这么去做,几乎不可能。他们只会用强制(再讲究策略,依旧是暴力性的),来“教育”,因为他们自己已经被教育过了,已经是产品了。他们通常只知道应该,而不去深究为什么,然后把这应该再强制灌输给下一代。没有“成长”,只有加工出来的“成品”。哪怕母亲那令人窒息的“爱”,那被当作神恩颂扬的“母爱”,依旧是一种更多出于“自私”的强制。
“他知道母亲是爱他的,但问题就在这儿——她置于他那种爱,实在不对头,却总是逼上来。她一切的爱都包含着十足的戒意,好像随时准备扑过来,保护他,把他从危难中拯救出来。”当“母爱”一再被浅薄地加以歌颂的时候,它的泛滥在社会学意义上可能对孩子造成的伤害,特别是以它的名义而行的某种吞噬性的占有欲,却总是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正如没有“爱”是一种创伤,过多的“爱”同样带来创伤,而且更可怕,因为前者也许只涉及一个人的孤独,后者却可能导致至少两个人的相互伤害。当“男孩”清楚地意识到“他要尽全力抵御她,永远也不会松懈自己的防守,永远也别给她机会”的时候,这种对双方的伤害已经成形了,并且日长夜大。“这到头来没准会导致那样一个时刻:他不得不粗暴地喝止她,残忍地拒绝她的关爱,她愕然而止,退后一步松开手。他满脑子里闪现着这一瞬间,想象着她那副惊诧的模样,体验着她受伤害的痛感,到这份上他又会产生一种负疚感……”
想知道“爱”可能是一种多么自私的东西吗?想知道种种自私的阴暗欲望是如何偏偏披着“无私”的伪装,而被塞进“爱”这尊空心偶像的内胆里以自欺和欺人的吗?请读库切。
对于库切来说,从“男孩”一出生所经受的“母爱”开始,人一辈子种种“爱”与“博爱”的经验,无不是可以深究与批判的。“感觉到她受到的伤害,这种感同身受犹如他是她的一部分,而她也是他的一部分,他知道自己落入了一个无法逃脱的深井。是谁的错呢?他责怪她,他对她没好声气,但他也为自己的不知感恩而觉得羞愧。爱:这就是所谓的爱了……”
正是这种“男孩”因“母爱”而遭受的“创伤”,为以后所有人与人之间相互的“爱的伤害”定下了基调——“他的心如历经沧桑,阴暗而坚硬,一颗顽石般的心。这是他的一个卑劣的秘密”——也许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卑劣的秘密”。
被拒绝的成长
孩子自己不会“拒绝成长”,他们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在不断发现对象,并学着与其打交道。但他们很快发现在对象和他们之间横亘着一个成人世界,这个世界神秘莫测地关着门,只开几扇窗给他们看。这个世界当然也在帮助他们,但更多的,却是强制的“创伤”。
那个成人的世界暂时还是不可理解的,像块石头,哪怕是五彩斑斓的雨花石;根据它而为孩子构建的半开放的模拟世界同样是硬邦邦的;这两个世界在孩子的生活中重叠在一起,孩子们“自己的世界”只是一个想象,实际上童年永远是成年人的童年;因此孩子在自己的发现行动中,随时会而且必定会磕在这些硬物上,而造成永久性的损伤。
正是这种弗洛伊德关注过(但关注重点不同)的童年期“创伤经历”,使孩子们不可能按照理想的“自主”方式成长。这种“自主成长”为成年世界所拒绝、篡改,以至于他们最终“成长”起来的时候,实际上带着所有“暗伤”。他们没能像成长小说的启蒙神话那样,在一条艰辛然而最终是光辉的道路上,从一个“半人”自我实现为一个“人”;相反,他们被一路追打着,逃进了一个叫做成人世界的阴暗“场所”,在那里喘着粗气,惊恐地面对那些实际上依然无法接受的东西——他们只是反复被“教育”说他们已经接受了,于是以为自己真的接受了。
这就是《少年的你》里一再从孩子们嘴里蹦出来的那个充满乌托邦意味的词:“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