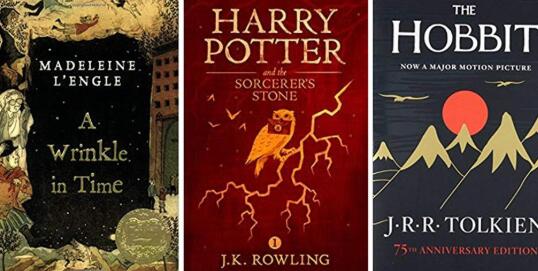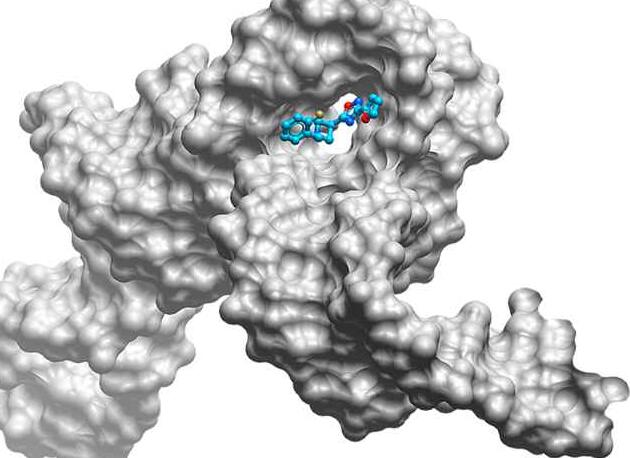就中国在新时代的国际环境中,如何继续开放,发挥新的做用,本文阐释三点看法。
一、包容性和开放度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核,我们擅长于把外来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
中国历来是非常开放的,善于吸取外来的文化和思想,具有高度包容性的社会。佛教在东汉从印度传到中国,经过了一番挫折,但是最终在中国的文化土壤里深深扎根。西汉张骞通西域后开辟了丝绸之路,加强了汉代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通过丝绸之路,佛教正式传入中国。但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在一定程度上被汉化了,出现了非常微妙的儒家思想和佛教的融合。在唐代,和西域甚至更远的地区的交往就很频繁。犹太人在中国拥有相当悠久的居住史,关于他们的文献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也就是唐朝年间犹太人在欧洲不被同化,为什么到了中国就被同化,这是因为中国人的包容,才使得那些在北宋年间从西北进入河南的犹太人逐步放弃了心理障碍,和中国人通婚,最后被彻底同化。
明清两代一般被认为是闭关锁国的朝代,中国近代落后于世界列强,这是一个起点。但是,对外联系和接受外界新事物的意识并非全然没有。清代康熙皇帝通过虚心学习,支持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历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中华民族从来不会把外来的思想文化在华夏大地上简单复制,而是消化吸收,变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毛泽东主席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教条主义地照搬俄罗斯的十月革命的经验。正如金一南所说:“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中国,中国改变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擅长于对外来的文化兼收并蓄,加以改造,变成自己的东西。对于开放政策、外来思想和建议也是一样的。
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政策不是全盘西化,不是照搬西方经济政策,而是根据自身的经济基础和发展态势,有选择地运用到中国的实践中去。我们中国引进自己所需要的,并且加以改造,使之适应中国的社会和人文环境。

二、在开放方面,对于全球化和外来的思想和政策建议,我们能说好, 也能说“不”,这同等重要。
在全球化的问题上,我们能说“不”(No),和说“好”(Yes),是一样重要的。我们对自由贸易说“好”,对外国直接投资说“好”。我们对毫无节制的资本流动说“不”,对进口全方位的自由化说“不”。这是我们过去开放政策的基本精神,也应当是现在和未来开放政策的基本理念。对全球化的恰当应对,是我们政策抉择的关键所在。
我们之所以要对全球化作出选择性的应对,要“挑三拣四”(picky and choosy),是因为大多数西方经济体的决策者都根本没有考虑到也没有预料到其后果,所以受到全球化的广泛的冲击。就大多数情况而言,全球化就这样发生了,并没有经过周密的计划、构建,预料到其严重的影响。我们不能有同样的疏忽——要明白全球化能够起到什么作用,不能起到什么作用;全球化为谁服务,而又将谁抛弃在后。
回顾历史,全球化的第一次浪潮是贸易的爆炸性增长,发生在19世纪,这是由于蒸汽机的发明所带动的。第二次浪潮发生在1946年发明集装箱化的运输之后,再加上二次大战结束,欧洲等国家重建的需要,贸易和投资迅速增长。 第三次浪潮和中国的崛起同步而进。
贸易促进增长,这是毫无疑问的。发展中国家由此创造了就业、生产能力,是因为贸易扩大了它原本微不足道的市场。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由于价格的下降,品种的增多,人们的生活水平得以提高。近二十年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使美国国内消费品价格降低了27%。最得以获利的,是贫穷的群体,他们能够买得起更多的玩具、服装、家具和移动电话。
但是,有些国家未能得到充分获得贸易自由化的利益,出现了艰难困苦的情况,工厂纷纷消失,工人失去工作。其根本原因,是在开放的同时,一个国家的国内政策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变革,以适应自由贸易的局面。
拉美国家对全球化的各个领域一概说“好”,不加区分,全盘接受。他们放开了金融市场,实行贸易自由化,他们对于出口部门和进口部门都敞开大门。东亚各国对出口积极开放,但是,对于进口是逐步实行放开的。在拉美,短期投资的资本(即热钱)蜂拥而入,使得汇率上升,一时间出口部门就失去了竞争力。生产力高的就业岗位被外国公司夺去了,而当地的产业则陷于中低效率和中低价值的就业,以后一直无法走出这个低效率陷阱。我们国家则不同,允许中间产品免税进入,但是,条件是只要最终产品必须出口海外。我们保护了就业和中等阶层的工作岗位。
中国的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多年来我们国家竞争性的日益提高,不仅仅是劳动力成本的关系。外资和外资企业仍然能够在中国获得盈利的市场。长期以来,外国公司通过生成各种产品而获利,包括电子产品。最大的、出口业绩优异的企业,多是跨国公司。这些企业得益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而我们则得益于外国的投资和诀窍。我们本国的企业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地提高了竞争力,从国内一直拓展到国外,如入无人之境。我们有众多的产品具有巨大的国际竞争力,例如产品如华为的手机和电信设备。贸易具有双赢的特性。我们没有出现中间产品就业岗位空心化的现象,没有重蹈拉美国家的覆辙,没有遭到墨西哥和巴西那样的命运。我们实施的开放政策,得到了正确的国内政策的辅助。
金融全球化是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发生的,发展中国家在90年代加入。人们普遍认为金融全球化非常棒,因为资本可以流动到生产率最高的地方,投资者的资产可以多样化,降低风险。但是这些年来,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现象,越来越多的资产价格、信贷,和一系列全球金融指数都更加趋于同周期化, 这些因素都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当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增强时,信贷全世界都增加;资本从核心国家流到边缘国家。不需要信贷扩张的国家,也看到资本大幅度流入,导致信贷扩张。资产价格上涨,可以说是遍地开花。人们一直以为,只要一个经济体实施完全的自由浮动汇率,他们可以基本上控制货币政策,阻挡过多的外来资本。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所谓宏观独立性,在如今不受限制的全球资本流动的大环境,只能是说越来越困难。
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教训,是不能放弃国内政策的主权。政策需要有选择性,需要合乎每个国家的国情。问题出在很多经济体的政府和政策。造成经济脱节和断裂的,不是全球化本身,而是它们的失误。幸运的是,中国没有进入那些国家的行列,而很多大国,包括西方国家,都没有摆脱这种局面。这就是全球化遭遇到逆反冲击的原因。所以说,开放经济体的同时要有相应的国内政策和调整。
今天,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指望我们对全球的需求起到稳固的作用,指望中国消费者和中国的游客能多购买他们的货物和服务。
我们该如何往前走? 下一个目标是什么?我们应该在什么方面开放? 应该对什么说不,对什么说是?
我们的消费者正在日益变得富有,日益讲究。所以开放贸易,进口适合消费者口味的产品无疑是有益的。消费者可以享受到品种繁多的产品,各种各样的货物,不同的质量档次和品位。同时,我们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坚韧性更好,竞争性更强,所以,开放金融部门,允许更多的外国金融服务参与,将会有利于我们的金融部门。我们知道竞争造就优质。全世界的企业都感受到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促使他们的技术进一步升级和创新。我们同样也需要合理的竞争,以及其带来的正面的溢出效应。我们需要加强金融体系的深度和广度,为家庭和企业提供更为广泛的金融服务,更多的多样化投资的机会,我们也需要国外企业的管理诀窍和最先进的公司治理。知识的溢出效应是巨大的。
但是,尽管资本账户开放和让汇率随行就市浮动是重点,保持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还是重要的。就连IMF的观点都有所改变:西方经济学中最为根深蒂固的观点,即全面开放金融部门和资本流动不受约束,都已经不再被认为是正确的开放途径了。此外,伴随着更为自由化的资本流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审慎政策的结合,是非常重要的。但也许我们最为需要的,是政策的透明度、可预见性、清晰的传递和沟通。这些都是防止投机操作和过度经济波动的关键条件。
三、在新时代的全球化过程中我们应当抓住全球网络体系的演变,做其领导者。
中国应当将自己确定为新时代的全球化的卫士。中国应该发挥什么作用?
今天的全球化经济和昨天的相比,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如今的世界已经是一个巨型的网络。技术是网络,基础设施是网络,供应链是网络,金融资本是网络,甚至连人也是全球网络的一部分。
网络使得每个国家的比较优势获得了更大的价值。只有在技术进步使得贸易网络拓展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才能成为重要的资产。中东石油输出国的石油在150年前毫无用处,但是今天它可是世界产出不可缺少的投入品。这要归因于全球网络。也是因为世界上需要电动汽车,才使得非洲国家的铑和锂变得如此值钱。
在全球已成为巨型网络的环境下,传统的强国和霸权意识已经过时。过去的霸权主义是大国设规定,其它国家跟随服从。在一个网络社会里,这已经不现实也不中用(not appropriate not feasible not suitable)。中国本身的发展就是基于网络的建设,是造就一个全国性的基础设施和市场的网络,使得我们成功地爆发式地推动了发展,这要感谢我国政府铺垫的基础。那么现在中国可以蓄势待发,将成为全球的网络领导。中国并不谋求独霸这个系统,而是要努力确保这个网络的平稳运行,保障其安全和可持续性。要防止其他国家试图破坏这个网络。
作为世界上最中心的连接点应该是我们的追求(号召)和发展目标。“一带一路”推动世界上各个地区都实现互联互通,同时成为物质基础设施和数字基础设施的中心。在网络条件下,规模和经济体量不再是最关键的因素,而是在一个网络的位置和连接(connectivity)。卢森堡是一个小国家,但是,它是金融资本网络的联结最佳的组成部分。卢森堡的资金流入和流出超过任何其他欧洲大国,该国保持着网络系统的中心地位。100多年前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卢森堡如今是欧洲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
通过建设现代化的基础设施,标准化的技术背景(landscape),从而缩短中国和其他经济体和民众的距离,将会使中国成为全球化网络中的最佳联结点。我们处于一个新的时代,和以往不同,再也不可能有那么一个霸主(dominant power) ,可以发号施令,制定各种规章制度,条条框框,而其他国家只能是唯命是从。在网络体系中,有很多参与者,他们都很重要,而互相之间的联络非常重要。
因此,在网络这个新时代,如果采取过度保护主义,维持孤立主义的心态,切断和其他各国的关系,甘愿自我封闭,将自己排除在网络体系之外,只会降低自己的影响力。因为在今天的世界上, 每一个环节都是重要的,每一座桥梁都是重要的,每一个结节对整个网络的运行都是重要的。我们应当是这个网络体系的领导者、保护者。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最伟大的命运不是仅仅成为一个最大的经济体,而是要认识到涉及一种架构的责任和收效, 这种架构能够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让大家都得到发展,在自身联结的过程中增强联结。真正实现一荣俱荣,一富俱富。
最后,当我们推出新一轮开放政策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考虑我们对其他经济体产生的影响,以及反过来对我们自身的影响。我们是一个大国,就像任何一条大船扬帆前进,都会引起强大的尾流,旁边的船只会受到颠簸。当我们对国际金融领域的风险敞口(exposure)扩大时,其他各国对我们经济的风险敞口也会相应扩大。我们的任何政策动向、资产价格或汇率的任何波动,都会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当我们和世界上其他地区实行股市和债券市场互通的联系时,当我们的股价列入在全球的指数中之后,当我们更多的投资者把我们的资产作为他们全球投资组合(portfolio)一部分时,我们所有的行动都会对他们产生放大的效应。这种影响将会迅速地扩展到世界的其他地方。
美联储在设计其政策时,很少会考虑到对其他国家,即使其任何决定都会对其他各国造成影响。我们的政策固然应该继续把国内的问题放在中心位置来考虑,但是,也要考虑到我们政策的溢出效应,特别是对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影响,否则将会对自身造成波动的风险。溢出效应(spillover)和回流效应(spillback)在欧洲和美国实施大规模量化宽松的时候,表现得非常明显。
更大幅度的开放也需要和其他经济体进行更大的协调和合作。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金融全球化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今年是我们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75周年。
我们应该是开放的捍卫者,我们也应该是实施对其他国家负责任的开放政策的典范。但是,最重要的是,在开放的新时代,我们应该建立在网络体系的中心地位。
(作者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本文根据作者在第五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的发言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