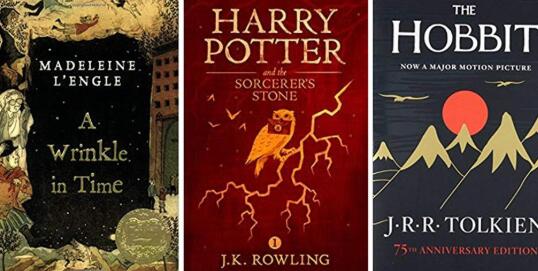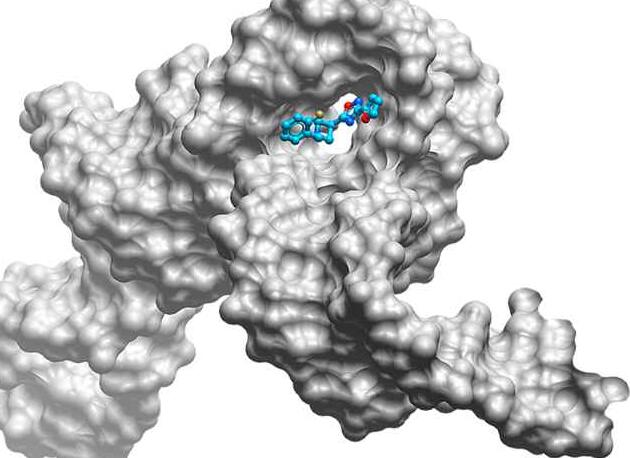或许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中国人现在所说的“普通话”,其实只有短短百年历史。在此之前,虽然也有“官话”,但那通常仅限于精英阶层,因为绝大多数人民都生活在本地狭小的地域内,并没有跨省区日常交际的需求。何况中国社会一贯更注重文字,方言语音的不统一根本无碍于政令的下达,所谓“皇权不下县”这样的说法虽然在实际治理中未必尽然,但也体现出传统政治更偏向间接统治,这意味着国家不需要直接与民众打交道,而是通过士绅这一中间层;在这种情况下,没必要有一个“国家的声音”让所有民众都听到、听懂。
只有在近代的危亡局面之下,出于动员“昏睡百年”的中国民众的需要,这才成为紧迫的需要。因此,自晚清以降,忽然涌现出无数人投身于创制标准音、文字改革这样的运动,像陈独秀,甚至直到晚年隐居上海,仍然完成了《中国拼音文字草案》——这一度让有些人困惑不解地以为他是在革命失败之后意志消沉,才去钻研这样的课题,但其实,倒不如说是他仍然壮心未已。对比看一下欧洲历史就不难发现,语言和文字的标准化,远不只是一个语言学的问题,它事实上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令人惊讶的是,直到王东杰这本《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问世,才有人真正系统地梳理中国近代史上这重要的一页。这或许是因为语言和文字太令人习以为常,而那些相关的争论看起来似乎又纯粹是语言学上的学术性问题,很容易让人忘记了它所蕴含的重大政治意义。简单地说,如果没有国语运动和文字改革,近现代中国从媒体传播、民众动员到公共交往,都将是另外一番面貌。
和近代的许多事物一样,这也是受西方刺激的结果。正如王东杰书中所言,当时的人们在对比中西之间差异时,侦测出中国语言文字的三项弱点:“汉字重形,不如拼音文字简便易学;文言佶屈,不若白话文章行之广远;方言林立,以致同为国民而耳目不接,一国之内俨如数国。趋新人士认为,这些问题不仅阻碍了民智开启,亦不利于人心固结。改革语言文字,就可以提升民众素质,塑造民族精神,打破地域和社会壁垒,强化国族认同,最终实现国家富强。”但确切地说,这三者不是同时出现的,而是有时间递进的:起初在晚清,有识之士认为关键在于提高识字率(如张德彝所说的“吾尝遍历欧西,知民之智愚,视乎识字之多寡而因以察其国势之盛衰”),为此就想改革文字,以便尽快扫盲;到1901年,才有人正式提出创设国语,以实现“国民之团结”;而又要到新文化运动时,白话文才成为蔚为壮观的运动,这不仅是新一代文化精英对传统的敌视、引入新文化,也是清末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的延续。
虽然当时人们常将这三者并重,但如果仔细辨认,就可看出它们其实有着不同的侧重,甚至可能构成内在矛盾:为了提高识字率,钱玄同、鲁迅等激进者都曾主张废除汉字,理由是拉丁化的拼音文字扫盲更快;然而随之而来的一个必然争议是,拼音是拼什么“音”?如果按各地发音来拼写,那统一的汉语文字就不复存在,这反而不利于“国民之团结”,如果按标准音来拼写汉语,那么且不说这样的国语当时尚未通行,也势必压抑方言所蕴含的地方文化丰富性,难以达到“多样性统一”基础上的“团结”;至于白话文运动,虽然确实有利于扫盲、普及文化,但现实证明,要做到这一点也不是非得废除汉字不可,甚至使用繁体字的港澳台还更繁荣发达。王东杰也意识到,中国字拉丁化运动和国语运动尽管许多主张近似,但双方竞争一度非常激烈,结果却“不无反讽意味:竞争也包括了斗争,反对之中包含了利用”。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的现状:汉字简化但不废除(以拼音辅助)、使用普通话(与方言文化消长),而文言文则基本退出公共领域,被白话文为主体的现代汉语所取代。这个结果也意味着,书面语最无力抵御改革浪潮,语音次之,而汉字则是最顽强的堡垒。
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最堪注意的一点是:在救亡的危局之下,紧迫感压倒了一切,人们急于采取行动,立论往往充满了不加验证的判断——而这些信誓旦旦的断言,在事后看来有些可疑,另一些甚至是完全错误的。文字改革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认为汉字难学,而使用拉丁字母的西方人扫盲容易,因而国家富强;然而,唐德刚、钱存训均曾发现,一个社会的识字率与文字难易无关,同样使用拉丁字母的国家,近代西班牙的文盲率比德法等国高得多,甚至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也与其识字率不成正比:西欧各国中最富强的英国,识字率长期不及经济上后进的德国。别的不说,东亚各国中,最彻底拉丁化的是越南,但这百余年发展下来,越南却是原汉字文化圈各国中最落后的;若说越南是历经战乱与分裂,那么同样改用拉丁字母的土耳其,也迄今仍未像当年预期的那样完全现代化。简便易学也未必就是普及的前提,世界语相当简单,据说托尔斯泰曾用两小时就基本掌握了这门语言,几周内就学会它的事例更比比皆是,但现在学世界语的人数却越来越少。
由此不难看出,当时的人们在立论时,论证的选择性、目的性很强,可说急于结论而不耐烦论证,因而充满了武断乃至专断的色彩,其断语常基于一系列不加质疑,也不必质疑的前提,而这往往就是中国社会长期以来信奉的理念,特别是“教育万能”。就此而言,文字改革、国语运动其实是一种激进的设想(简化文字本身就反传统),试图由文化入手,从根本上重整社会秩序。在这么做的时候,这些近代中国的重要人物压倒一切的考虑是国族存亡,对其余代价则在所不惜,既不在意传统的存续(土耳其改用拉丁字母后,年轻人就再难阅读古籍),甚至也不耐烦考虑传统的某些优点——例如汉字的超语言性质对国家的统一所起到的潜在作用。
另一个不时可见的基本前提是:他们不约而同地接受了当时西方的文字线性进化观,认为汉字在世界上往轻里说是“过于独特”,往重里说则是“野蛮的残余”,是落后的象形文字,而字母文字才是所有文字发展的必然终点。汪荣祖在《康章合论》中曾说,康有为“惟见全地球的共同归宿(destiny),而无视(或认为不必顾虑)各文化的个别命运(fate)”,这其实是近代很多人的共有想法。对这些人来说,“中国人”认同的基本文化要素是汉语而非汉字,因此消灭汉字正是为了解放乃至保全汉语的必由之路;但对像傅斯年这样的学者来说,放弃汉字是比“中国”灭亡还要可怕的一件事,因为汉字是中国文化的基本载体。类似的争论其实在近代日本也有过,像前岛密等人都将日语使用汉字和假名书写视为不幸,乃至“日语的受难史”,日本学家赖肖尔甚至抱怨日语有着全世界最复杂的书写系统,认为只需在战后“稍稍忍受一点痛苦”,用15个拉丁字母就可以拼写日语,简便得多了。对此,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曾说,这完全低估了所需付出的代价,它将摧毁文化传承,在转换过程中释放出的暴力将泛滥成灾。
国家标准语的普及,是各国现代化过程中都要上的一课,只不过中国的情形尤为复杂。法国在1789年大革命爆发之际,全国2000万人中能正确拼写法语的据估计远低于300万人;甚至在革命之后,仍有30%的民众不懂法语。为了在全国普及“唯一的自由语言”法语,1795年创设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由此启动在全国范围内对法语的初等教育。这一过程势必伴随着对各地方言的排斥和挤压,根据美国历史学家欧根·韦伯开创性的名著《从农民到法国人:法国农村地区的现代化,1870-1914年》(奇怪的是本书未加参考),对现代法语的普及起到最重大作用的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四种力量:交通通信、教育、兵役和政治。如果这样做一对比就可发现,对中国而言,政治的作用最重要,交通通信和教育其次,但兵役的作用却微乎其微,本书中甚至不着一词。
本书也很少谈及普通话的推广通过什么途径,但粗略可见的,一是学校教育,二是电波媒体。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直至一两代人之前,很多地方的老师仍然都习惯用方言授课,因而很长时间里,人们听到的标准音其实不是来自老师,而是广播、电影和电视这样的电波媒体。史学家周策纵在《忆己怀人》中曾回忆,1931~1933年在老家衡阳读中学时,来了一位“一口卷舌音”的金老师,“校长说他讲的是最标准的国语,我们都应该学”,但学生们都听不懂,竟然最终把他轰走了。相比起来,现代化的电波媒体则有特殊的权威,并借由大众传播将普通民众卷入国家政治和文化生活之中,他们自此不再像以前那样能保持“天高皇帝远”的疏离姿态了。

尽管这些媒体上的“国家的声音”对下层社会的渗透仍然是有限的、间断的,但正如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所说的,大众传播的技术所带来的“那种接触的高频率和高强度是很了不起的普遍历史的新事物”。这使得普通民众以先祖未曾有过的方式,感觉到自己是国家政治生活的组成部分,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行动着、感知着的主体,所谓“当家做主”。
1923年,中国第一个广播电台出现不久,国民党就率先注意到它的潜在力量,1927年统一全国后,更颁布多项对电台的政策法规,其中《通饬各广播电台使用国语播报令》要求所有电台一律禁止方言广播,必须用国语普通话,“利用广播以提倡识字,尤属当务之急,至其实行国语,统一方言,尤其余事”。这直接导致一大批不懂国语的明星(如只会讲粤语的张织云),到有声电影普及的1930年代被迫息影。与此同时,作为全国标准音的普通话也逐渐推广,以此为媒介,国家开始与民众直接接触。这在没有广播和报纸的年代里,是无法想象的:大众传媒对民众的动员、操纵、灌输能力,远远超过了以往的行政文书。
虽然书中也提到“国语传播主要是借助于现代性建置的渠道进行的(学校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其性质和效率都和官话的自然传播方式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但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学了标准语,不一定使用,其普及使用还需要一个必要条件:与异质人口的交流,而这与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城市环境分不开。本书未言明的设想之一,是将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理解为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这在某种程度上固然也是现实,但却不必然是简单的替代关系。在一个现代社会中,倒不如说更像是一种碎片化的场景:不同的语言被应用在不同的场合,方言未必彻底消亡,但却逐渐撤退到了家庭内部的私人领域,而普通话则占据了越来越多的公共领域。当然,这就是另一种现代政治了。

《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
王东杰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