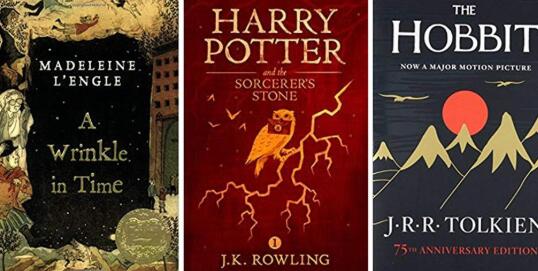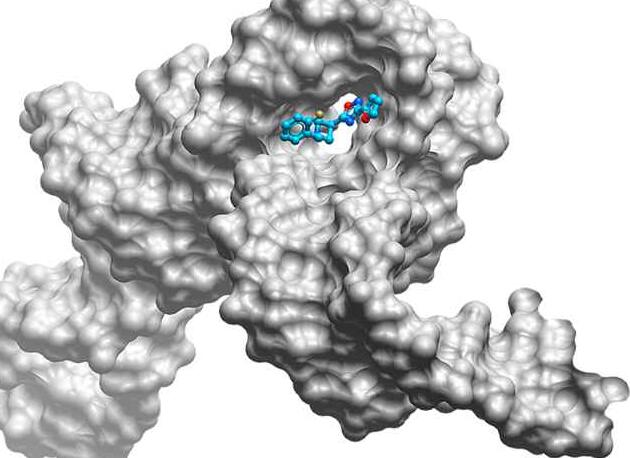路易斯·海曼/文 栗红岩/译 于留振/校
本文原载Symposium Magazine,2013年7月8日。作者路易斯·海曼(Louis Hyman)是美国康奈尔大学产业与劳动关系学院(ILR School of Cornell University)历史学教授,哈佛大学美国史博士,本科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主要研究和教学领域为劳工史、企业史、消费史和资本主义史。他出版的著作主要有:Debtor Nation: The History of America in Red Ink(2012),Borrow: The American Way of Debt(2012),American Capitalism: A Reader(与Edward E. Baptist合编,2014, 2017),Temp: The Real Story of What Happened to Your Salary, Benefits, and Job Security(2019)等。
译者简介:栗红岩,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8级本科生;于留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与副教授。
今年春天早些时候,我接到《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打来的电话。因为我写过几本关于美国个人债务史的书,所以记者偶尔打听情况也不足为奇,但通常他们想听到的都是有关理财的五大成功秘诀,而非“真实的”历史。
这位不同寻常的记者珍妮弗·舒斯勒(Jennifer Schuessler)问了我一个非常出乎意料的问题:书写资本主义史的用意何在?我愣住了,顿了顿,随即问她是从哪儿听到这个术语的。她避而不答——“哎呀,到处都在谈论”——而我则开始告诉她,在我看来,这个新兴的分支领域来自何处,我的回答中充斥着“能动性”“偶然性”和其他历史学术语。她告诉我说她听得懂。
当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她为什么要关注这个问题。毕竟,《纽约时报》通常不会报道学院派学科的分支领域,尤其是历史学。所以,你可以想象,第二个周日,当我醒来,看到《纽约时报》头版头条的时候有多么惊讶:“在历史系,资本主义研究方兴未艾。”几天来,这篇文章成为《纽约时报》网站上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次数最多的报道,数百人突然针对‘何谓资本主义’这一问题发表评论。
在许多方面,论坛上的讨论比那篇文章本身更具启发意义。虽然网络喷子有他们的发言权,但是,论坛上的分歧意见更令我感到震惊。许多读者指出了他们认为所有学者都遗漏或排除了的东西,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努力弄清楚,我们究竟是得到了巨额资金资助的支持企业的辩护者(我们当然不是),还是共产主义的“第五纵队队员”(这是一种更加有趣的指控,但我们同样也不是)。
对我来说,相比那些人身攻击而言,更加值得关注的是,这简直就是一场关于资本主义的新颖讨论。对大多数参与这场讨论的读者来说,资本主义完全就是由卡尔·马克思或亚当·斯密所解释的那样(偶尔还可以算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或约瑟夫·熊彼特所做的解释)。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是一种可以通过一种理论或另一种理论得到普遍解释的制度,无论你是否理解这种理论。要么你读懂了作者,要么你就是个门外汉。按照这种观点,资本主义史只不过是自然法则的逻辑展现,就像苹果从树上落下一样。正如一位读者所言,“‘资本主义史’就像‘引力史’一样具有启示性。”
卡尔·马克思
如果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就像艾萨克·牛顿的“苹果”那样是可以预测的,那该多好啊!历史学不是为了证明一个普世理论,而是用来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作为一种学术性实践,历史学就是用来解释事件实际上是如何发生的,以及随之产生的所有不符合规律的情况。这里的关键问题,不在于像女学究那样刻板地给资本主义下定义,而是思考,为什么资本主义看似如此简单,却难以对其进行简单的界定。在过去的十年里,历史学家重新燃起了一种兴趣,他们不仅要挑战关于资本主义的既有定义,还力图从历史学的视角对这些非常混乱的定义进行解释(这让世界各地的唯名论者大为震惊)。
随着美国从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中复苏,人们不难理解这种突如其来的紧迫感。繁荣和萧条以惊人的频率冲击着我们。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主义史”这一术语在21世纪头十年中期的某个时候,就开始在历史学界流行起来,当时正值科技崩溃和经济大衰退之间。虽然这次大衰退重新激起了公众对资本主义的兴趣,但这种新的研究在2008年之前就开始了,并且标志着一种智识和代际方面的重要转变。
在过去的两代人中,那些想要功成名就的历史学家,几乎没有一个致力于研究经济问题。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左派学者的研究,强调的是为推动社会变革而斗争的各种运动(诸如劳工、妇女和非裔美国人等群体的运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后现代转向,将传统的经济史研究题目挤出了历史学领域,随之一同被挤出的,还有死气沉沉的计量史学(即经济史研究的定量取向)这个分支学科。如果一个学者写作的是商业史,或者甚至更糟,写作的是商人史的话,那么他/她似乎就暴露出了右翼倾向。如果你写作的是真实的商业,许多左派学者就会觉得,这只是为了歌颂商界领袖,就像大多数历史学家所写作的受压迫者的可歌可泣的历史那样。有些坚定的学者(所有政治派别都有)仍然存在,但总体而言,他们被边缘化了。
相比之下,对于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成长起来的这一代研究生来说,这个世界看起来就大不相同。几十年前,社会运动就要么已经取得成功,要么已经遭遇失败。在看似永无止境的经济停滞中,激进的改革似乎就是一种幻想。冷战时期那种非此即彼的区别好像没有那么重要了。那些激发了许多社会史研究的问题变得似乎很幼稚。“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古老的问题,变成了“既然我们身在美国,为什么还要谈论社会主义”。我们对离经叛道的托洛茨基分子了解过多,但对支配世界的银行家却一无所知。
人们的这种认知鸿沟,源于这样一种信念:这其中根本没什么值得了解的。阿尔弗雷德·钱德勒的《看得见的手》是大多数美国历史学研究生仍然继续阅读的唯一一本企业史著作。而这本书重申了新左派对资本主义的所有看法:即资本主义是无法避免的、机械的、高效的和乏味的。资本家根据一种不可阻挡的逻辑经营运作,而我们这些其他人则是追求自由意志的“临时代理人”。如果被追问的话,很少有学者会把这种假设用这样的话表述出来,但它美化了人们提出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文化研究学者从安东尼奥·葛兰西那里借用了“霸权”一词,后来,这个词已经被稀释为对广告活动的愚蠢分析。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学家认为,当他们阅读马克思或斯密的作品时,就“明白了”何谓资本主义,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多说的了。
The Visible Hand :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我们这一代学人,深受所有那些新左派社会运动历史学家的影响,他们将种族、性别、阶级作为重要的分析视角。如果你是通过阅读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书而接受的训练,那么商业档案在你眼里就会大不相同。当你像米歇尔·福柯那样看待银行时,它们看起来也是不一样的。这种史学范式始于这样的假设:即处于边缘地位的人很重要,文化至关重要,关于性别和种族权力的问题与关于阶级的问题是不能分开讨论的。借用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的著作的标题来说,资本主义的书写也必须“从边缘到中心”。无论如何,人们必须这样书写历史,即使我们所书写的人民并不是我们的英雄人物(我们这一代人从未真正拥有过真正的英雄)。
当诸如银行和公司之类的资本主义机构被视为带有真实人物的真实场所时,这些故事就开始发生变化了。盈利的必要性依然存在,但盈利方式的选择(如果真要选择的话)开始变得不那么不可避免了。除此之外,我们不可能忽视这些选择方式是如何被塑造的,它们不仅受企业间竞争的影响,还受文化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尽管利润很重要,但它只是指导管理者做出选择的众多因素之一。管理者做出的决策,在决定我们的日常生活方面,尤其是那些处于底层的人的日常生活,可能比任何人所做的决策都更为重要。
简而言之,像我这样将来会研究资本主义史的学者,则是在反其道而行。我在哥大读本科时,约书亚·弗里曼(Joshua Freeman)开设的劳工史课,是在一个大礼堂里上课,但仍然座无虚席。相比之下,同样是在读本科时,我上的斯米特(J.W. Smit)开设的资本主义史课,班里却只有四名学生。他是个很棒的学者,但此类课程非常不受欢迎。当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指导老师伊丽莎白·布莱克玛(Elizabeth Blackmar)告诉我说,我应该停止研究劳工,而要开始研究资本时(我的论文研究的是关于1919年“无啤酒,就不工作”[No Beer, No Work]运动中的工团主义和禁酒令之间的激进冲突),我看着她,仿佛她是个外星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才认识到:她是对的,要理解劳工的历史,我真的需要理解资本的历史。
我现在认识的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史学家都有过类似的觉醒过程。研究商业领袖、供给学派和金融危机的历史学家金·菲利普斯·费恩(Kim Phillips -Fein)尖锐地指出:“如果是在另一代人那里,我们可能都会成为劳工史学家。”读研究生时,我们感觉自己与那些将商业和金融排除在外的正常研究项目格格不入。我们经常在档案馆里偶遇,其时我们互相询问彼此的研究工作。我第一次见到朱莉娅·奥特(Julia Ott),是我们在华盛顿特区的国家档案馆等待暴风雨结束的时候,而现在她早已成为我的长期合作伙伴。在认识她之前,我从未见过一位自称“金融史学家”的人,而金融史听起来像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聊的东西。但后来,当我开始写作更多的关于债券市场的研究时,我也开始把自己视作金融史学家了(或许我们俩谁都不是那么无趣吧)。尽管如此,当我在21世纪初告诉别人说,我正在从事个人债务史方面的研究时,我得到的最多的回应是人们充满厌倦的呆滞眼神。(相信我,在金融危机之前,没有人愿意谈论抵押贷款担保证券问题。)
友谊可以带来友谊,甚至可以跨越世代,就像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感到孤立的布莱克玛和理查德·约翰等人,现在他们发现自己已然成为连接当今资本主义史学和旧的政治经济史学的桥梁,这些旧的政治经济史学非常重视资本主义制度组织的力量。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这些问题的历史学者,看到了学界对“资本主义史”研究兴趣的激增。最初由研究生组织的资本主义史小型研讨会,逐渐发展壮大,到2012年,全国性的美国历史学术会议将其主题确定为“资本主义与民主研究的前沿”。
正如《纽约时报》论坛上的回应所提醒我的那样,仅仅表明资本主义已经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了变化,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转变。资本主义并非历史的终结(正如弗朗西斯·福山在冷战结束时所做出的著名论断那样),资本主义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资本主义发生的变化需要诠释。即使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也已经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基本进程,譬如工作和投资,是如何被政策、文化和发明改变的。不平等、失业和债务等话题,充斥着我们的报纸和博客。
弗朗西斯·福山
所有这一切的关键,在于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之间的奇怪分歧,他们似乎很自然地分享我们对经济史的兴趣。到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家凭借其稳健的模型、高额的薪水和公众形象在学术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美国人,至少在精英论坛上,实际上很信任他们的意见。我们这些人文学者则放弃了公共领域,退回到晦涩的期刊里,但我们确信,批判性理论仍然要比数学时髦得多,即便白宫没有召见过我们。
在经济大衰退之后,反对市场正统观念的声音,突然发现了新的机会。美国经历了多年的经济停滞之后,我们再也不能盲目地接受自由市场从长远来看是有效的这一假设。那些在社会边缘群体中盛行的一些观点,现在得到了更多人的广泛讨论。正如历史学家所观察到的那样,大部分经济学家未能提供一个让人们感到信服的解释。在大多数情况下,故事要比回归分析更有说服力。历史学家显然应该比经济学家更胜一筹;毕竟,美国人讨厌数学的程度,与他们喜欢《历史频道》的程度旗鼓相当。
然而,历史学家未能将这一教训传授给更为广泛的公众。读者喜欢故事,但我们提供的关于资本主义的叙事却几乎无人理会。有些历史学家仍然试图用巧妙的术语来打动人们。其他历史学家则固守马克思主义的夸夸其谈,或者认为讨论经济的运行方式就是支持其运行,就好像每当我们讨论任何有争议的事情时,我们就会自动成为其辩护者一样。大多数情况下,这与其说是政治问题,不如说是想象力问题。我们还没有完全认识到,其中的利害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生活在一个极有可能创造出新的方法来解释经济问题的时代。
资本主义史研究当然要使用统计资料(当然它也本该如此),但它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它讲述的是那些真实人物的故事。政策制定者做出更改法规的决定。商业领袖要在无畏的冒险中承担风险。工人们居然力图抵制巨型公司。譬如,经济学理论会告诉我们,萧条时期是罢工和组织罢工最糟糕的时机。然而,1936年的弗林特静坐罢工事件(Flint Sit-Down Strike)却发生在大萧条中期。一群汽车工人,参加了一场反对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公司、即通用汽车公司的罢工,并取得了胜利。正是这种现实,而不是任何理论,使资本主义史不同于经济史。意义最为重大的事件,恰恰是那些并不能完全被人们预测到的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最引人入胜的历史,就是那些关于挑战市场平衡和常识的企业家的历史。
我们几乎所有关于发展的经济理论,都源于我们过去500年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只有理解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才能有望促进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引导发达经济体走上可持续增长的道路。最为重要的是,历史学家必须提醒所有人,万事万物都在变化,资本主义也不例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观点比任何宣传共产主义千禧年的小册子都要激进。虽然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则可能看起来是固定不变的(超额利润应该用于投资,生产工作需要组织起来,私有财产需要得到保护),但其可能的形式却是无穷无尽的。
甚至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仅仅在我们国家,资本主义的多种形态就显示出,即便是像“投资”这样简单的概念,也可以是千变万化的。譬如,19世纪早期,风险最大的投资是工厂投资,而一般的投资都进入到了商业冒险领域。旅行投资的收益是有保障的。许多朋友(通常都是私人的)可以聚在一起分摊一艘船和一批货物,旅行结束后,船只可以卖掉,利润可以分成。一个工厂该怎么分呢?它的“旅程”什么时候结束呢?这种漫长的投资期看起来风险太大。如果你想投资于生产,最安全的赌注不是工厂,而是奴隶。因为奴隶不仅可以工作,还可以生育新的劳动力。随着边疆的扩张,奴隶还可以被用来出售赚钱。如果有人想借钱,奴隶可以很容易地用于抵押,甚至成为证券。我们所认为的代表资本主义投资的工厂,在某种程度上是19世纪二三十年代投资者的次要选择,这使得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变得错综复杂。
新左派历史学家和我们一样了解这段历史。其区别与其说是事实层面上的,不如说是解释层面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主义史”或许与其说是新左派史学的中断,不如说是新左派史学的延续——就像每一代新人都想推翻上一代人一样。能动性对我们来说仍然很重要,但我们把它局限在了影响商业和工业的少数有权势者范围内。我们研究的更多的是关于如今仍然具有影响力的公司,而不是那些没有影响力的社会运动。我们看到的能动性,是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而非一个假设命题。
我们会希望现代资本主义以其他方式演进吗?当然希望。但历史学家的任务是直面冰冷的现实,而非塑造英雄传奇。在我们的现实中,普通人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能推动真正的改变。弗林特静坐罢工事件是有可能发生的,但与其将它视为日常能动性的另一个例子,不如将其理解为某种特殊的事件,这样它的教训才能被人们理解和运用。幸运的是,档案总是能提供更多关于过去特殊性的指导,尽管它们也促使我们质疑我们对资本主义运作方式的假设。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即使不是每个人都做出选择,每天也都有人做出选择,这些选择不仅决定着资本主义的过去,也决定着它的未来。资本主义史不是一时的潮流,而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的对象,这样我们才能在未来有更好的选择的时候做出更好的选择。
责任编辑:于淑娟
校对:张亮亮
相关推荐
猜您喜欢
- 许家印购买恒大债券「2022年3月恒大到期债券」
- 安利一个小众又高薪的职业都有哪些「哪些比较挣钱的小众职业」
- 融创为什么也陷入困难「融创危险了」
- 会计基础题库及答案解析「高考押题押得到真题吗」
- 理财真的可以挣到钱吗「理财真的能赚很多钱吗」
- 美联储大量购买债券「美联储缩减购债对股市影响」
- 又可以赚钱「顺便赚钱」
- 今年的基金冠军「基金最赚钱的人」
- 债券投资怎么赚钱「做债的经验分享」
- 下跌之后 重点关注这些转债股票「可转债下跌」
- 券商股暴涨背后 藏着什么玄机和秘密「最近券商股票大涨啥原因啊」
- 白话可转债-入门与进阶实战指南 epub「论攻略指南的错误用法小说」
- 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解析「资产负债表可进行分析」
- 公积金利率一般是多少「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利息是怎么算的」
- 租赁住房支付房租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吗「租私人住房公积金可以提取嘛」
- 公积金提取次数限制 「住房公积金提取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