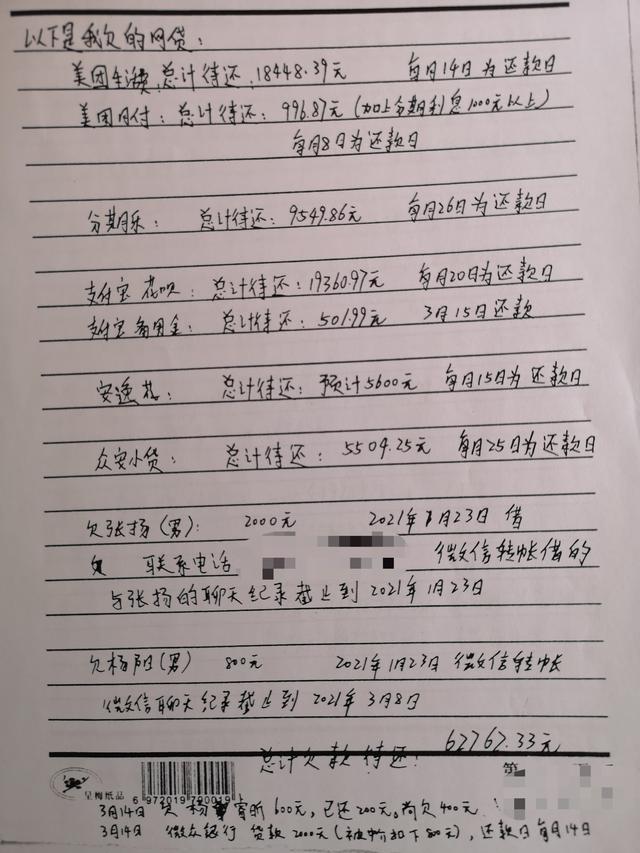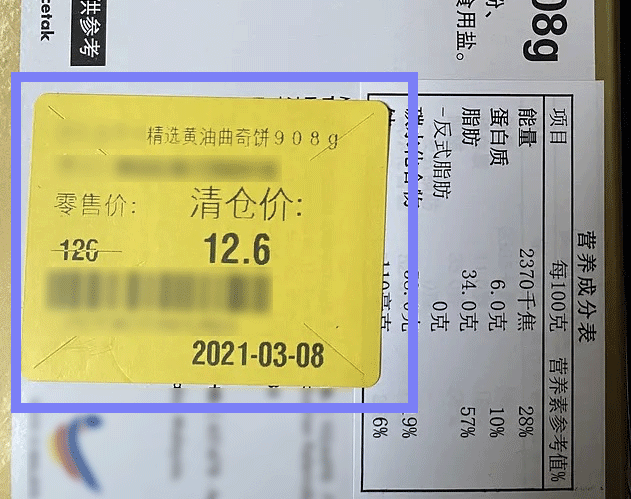经历疫情最艰难的一年,人与自然如何和谐共生成为全世界关注的话题。4月22日,第52个世界地球日的主题是“修复我们的地球”,这是疫情后的深刻反思,如何减少对自然和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如何对自然有更多亲近与了解,是人类共同面对的课题。
对中国自然教育行业从业者来说,疫情带来的并非只是坏消息。“疫情是大自然的一次警告,经历这一次,自然教育会变成一种全民需求。”百家游学会常务董事青梅告诉第一财经,过去一年,她非常明显地感觉到自然教育的市场趋势,从政府体系到民间机构,从学校到家庭层面,都掀起了一场自然教育的浪潮,“社会和学校教育的融合已经在实现了。”

青梅在此行业浸淫了十年,见证了自然教育在中国的十年发展,“这十年,很多热爱自然,有眼光、有素养的人走到一起来。”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环境机构、教育机构、自然保护区开启自然教育的学习和公众普及实践,试水市场化经营,探索自然教育的盈利模式。
2016年,青梅参与创办百家游学会,次年发起上海自然教育论坛。据第五届上海自然教育论坛今年1月发布的《2020上海自然教育行业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运营1至2年的自然教育机构相比去年增加8%,持平和盈利的机构超过六成,整个行业正朝着正向发展。
据《全国自然教育行业调查报告》显示,2010年以来,中国的自然教育呈现井喷式发展,中国目前的自然教育机构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浙江、福建、广东、云南和四川,超过半数的自然教育机构拥有自行管理的自然教育场地设施。
中国自然教育的兴起,源于美国作家理查德·勒夫出版于2008年的一本畅销书《林间最后的小孩》。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生活在钢筋水泥城市中的孩子离山川、溪流、森林和原野越来越远。他们一方面接受着科技时代的馈赠,另一面也被网络和电子产品包裹,很多孩子的日常生活就像书中一个美国孩子所描述的,“我更喜欢在屋里玩,因为只有屋里才有电源插座。”
理查德·勒夫第一次提出,美国日益增长的儿童肥胖率、多动症和抑郁症等各种心理疾病,都与“在大自然里玩得太少”这件事有关。这本书在15个国家的出版都引起了各国对儿童与自然关系的密切关注。2010年,“自然之友”将这本书翻译到国内,书中提到的“自然缺失症”第一次被国内关注,也由此掀起中国自然教育的浪潮。
中国妈妈推动自然教育
“什么是自然教育?这个词其实没有明确定义。”青梅说,自然教育的概念出现在一百多年前,在西方被称为“环境教育”。中国的自然教育吸收了欧美、日韩等国家的经验和理念,但又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习俗。
早期的自然教育,主张人们从体验生活中获取学习经验。随着全球变暖、各种环境问题出现,自然教育被放在环境教育和可持续发展教育中解读。
王西敏是中国自然教育的先行者,2008年获得美国环境教育及解说硕士,不仅翻译《林间最后的小孩》《生命的进化》,也发起全国自然教育论坛,推动中国自然教育发展。
身为上海辰山植物园科普部部长,王西敏认为,所谓自然教育,更像是中国当下语境产生的词汇,也可以称为“环境教育”和“可持续教育”。
他发现,中国自然教育领域有一个特点,吸引的是各行各业的爱好者,而且中国妈妈是很重要的推动群体,不仅带孩子参加,自己也组织举办社区活动,积极组织志愿者做自然教育。这股教育力量,几乎是自下而上的。

身在广东省中山市的吴娟就是从母亲身份转向自然教育领域的从业者。曾经做了十年记者的她之所以投身自然教育,发起荒野学堂,最初更多是想满足儿子的成长,“大自然是他们这一代孩子特别缺失的点。”2017年,她创立中山第一家自然类书店,以书店为平台推广自然教育。
疫情让吴娟看到来自家庭的旺盛需求,她们组织的活动总是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家长,经常人满为患,“我们最大的困境在于,自然课程开发的速度跟不上家长的需求。”

吴娟的儿子从幼儿园中班开始,跟随她创办的自然教育机构叮咚荒野学堂在大自然里四处行走。“面对野外复杂多变的环境,他特别大胆。”吴娟说,儿子今年10岁,从未上过课外补习班,却因为喜欢读书,兴趣和知识面都很广,常把自己从书上读到的内容拿到自然中去印证,把二手经验转化为一手体验。在自然教育中,她只是引导,大自然中的昆虫、鸟和植物才是孩子的老师。

青梅创立于2015年的陌上堂,意为一座流动在阡陌之上的讲堂。田间导赏活动“说稻做稻”包括“初秧”和“归仓”。她和自然导赏员带着孩子到田间地头,卷裤脚,撸袖子,赤脚体验从插秧到收割、脱粒到碾米的生产流程,追踪一粒健康的大米从田里到碗里的过程,引导孩子们探讨从田间演变而来的“水”和“稻”字。劳动过后的每一顿百家饭,孩子们都会把碗里的饭吃得精光。“我们把劳动教育、自然教育和品德教育融会贯通,节约粮食不再仅仅是口号。”青梅说。

作为生态旅游的一种新业态,自然生态体验教育的发展态势可谓迅速。越来越多的营地教育机构推出自然体验、自然探索、野外生存等一系列自然教育类活动。在中国各大城市则活跃着或大或小的自然教育民间组织,以不同方式开展规模大小不一的自然教育。
目前,中国自然教育从业者具有高学历、中青年为主体的特征。以百家游学会为例,在该机构担任过领队或接受培训的一百多名自然导赏员中,本科学历占99%,985大学毕业生占37%。在《中国绿色时报》2019年末的一份调查问卷中,94%的一线城市和88%的二线城市受访者至少每月到大自然中活动一次,八成以上受访者有意愿参加自然教育活动。
“自然教育除了具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大目标之外,形式手法可以无限多,承载方式可以不受限。说白了就是大家都需要,人人都能做。”北京盖娅自然学校副校长冬小麦认为,自然教育并非只是看看花,认认鸟,也不是单纯的户外玩耍,其核心还是“教育”的本质。
自然教育不仅让孩子们学习自然知识,建立与自然的联结,尊重生命,更是建立一种自然观,学会遵照自然规律友善地生活。
唯有盈利才可持续
“中国的教育体系中,目前没有自然教育的专业。很多从业者是学了其他专业,再回过来做自然教育。”王西敏说,他的美国同学在本科毕业后,很多进入国家公园、保护区、自然中心,因为对生态和教育都有专业背景,这批人才从事起自然教育工作,势必得心应手。而在中国,自然教育最迫切的问题就是缺乏专业人才培养。
日本的自然教育体系经过数十年发展,成为亚洲领军者,也是中国自然教育从业者学习的对象。日本最早的自然教育可追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野外教育,带领孩子战胜自然,偏向冒险和探索。上世纪七十年代,高度发达的日本也出现很多“三无”现代儿童——那些对周围一切事物无兴趣、无感动、无气力的孩子。30年来,自然教育在日本被广泛关注,并相继诞生4000多家自然教育机构。
日本的自然教育以“自然学校+社会+社区”为中心,加上日本自然保护协会、日本野鸟会等环保教育中心的助力,形成规范化的行业体系。中国大部分自然教育机构都在大城市,而大城市往往缺乏自然环境,人才、经费和市场都是目前存在的问题。
青梅观察日本和韩国的自然教育,发现日本哪怕有那么多机构,但覆盖面依然很窄,自然教育依然属于小众领域,“日本自然教育有很好的盈利模式,坚持以公益性质面向公众,通过周边售卖、特色产品形成有效的产业结构。自然教育只有形成商业生态,才能吸引更多人来支撑。”

王西敏也认为,中国自然教育机构只有盈利,才能改变之前公益机构只能依靠捐赠开展项目的局限,保障自身的可持续性。
就目前而言,中国自然教育行业依然存在很难盈利或盈利少、从业者专业性不强、薪酬相对偏低的问题。如何提高团队的商业能力、怎么研发课程建立课程体系成为很多机构未来几年面临的挑战。
说到人才的专业化,冬小麦想起自己的研究生导师说过的话,“一件事你如果做上15年,你也是专家。”她坚信,所谓“专业”,就是那些因为热爱、专注,愿意持久投入的人,这批不同视角和背景的人进入自然教育领域,也会更有建树。
从2000年开始,王西敏成为上海野鸟会发起人之一,也曾在国内不同城市工作过。作为资深的自然爱好者,他认为上海的自然资源是最为匮乏的,这也是他们做自然教育的劣势,加上上海的家长普遍更重视学习和升学,自然教育势必被边缘化。

青梅相信,越是条件有限,上海自然教育从业者的动力就越大,“贫瘠倒逼我们不断研究设计课程,在有限的资源里做出最好的教育效果。”今年她已经明确感受到来自政策、政府和学校的认可和支持,未来,百家游学会将面向上海中小学进行自然教育的培训和孵化。
什么样的自然教育是比较好的?王西敏也很难说出统一的标准,“但很重要的一点是,带孩子到户外玩耍。国际上有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叫重要生命经验。”他相信,拥有自然经验,也许十几年后,参与自然教育的儿童成长起来,中国自然教育行业又将发生巨大变化。
相关推荐
猜您喜欢
- 跨国公司关注中国十四五规划,看好新发展格局下市场潜力
- 生物安全法施行为中国带来三个“新”
- 第六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一组数据看平安中国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中国为联合国减贫目标作出重要贡献
- 生物安全法:建立传染病、动植物疫情防控国际合作网络
- 生产端和需求端共同发力 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 保险股AH溢价率两极分化严重 中国人保高达179% 中国平安低至1%
- 气温偏高致中国最大内陆咸水湖完全解冻
- 中国足额缴纳会费坚定支持联合国工作 并积极践行多边主义
- 国际锐评丨更均衡、更开放,中国外贸“开门红”不简单
- 吃着中国饭砸中国碗!起底“双面人”李亨利
- 中国科协2021重大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难题投票即将开启
- 中方:美方应停止鼓噪所谓“中国外空威胁”
-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综合施策消除冲突中性暴力
- 中国希望到2025年草原退化趋势得到根本遏制
- 报告:一季度中国旅游经济指数站上荣枯线,步入景气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