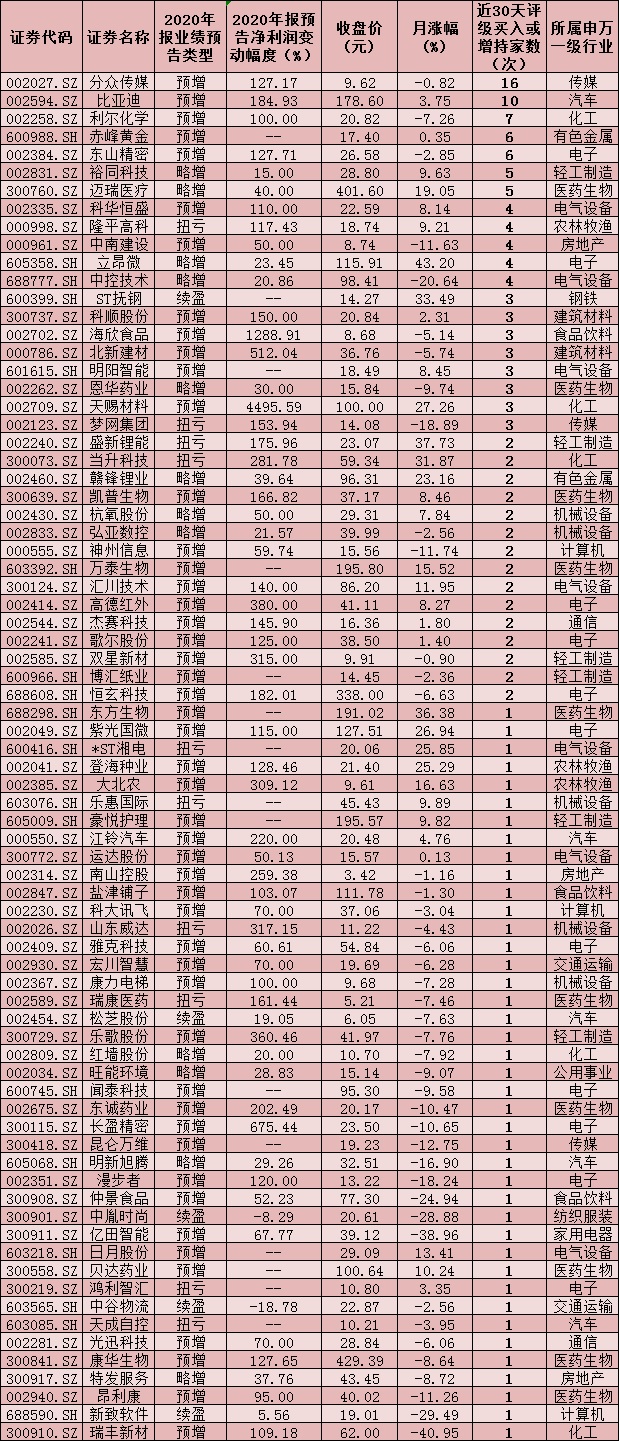三十而立,立于何?中国现代资本市场的三十年,该如何评价?哪些是经验,哪些是教训?哪些是看似经验的教训、哪些又是看似教训的经验?
尉文渊,全程见证了中国现代资本市场的第一个完整30年。1990年,他独挑大梁参与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并担任首任总经理,短短几年间,幼小的中国证券市场在交易层面就能够与全球同步。很难想象,今天仍在争议不前的T+0、放开定价、放开涨跌等等,在股市起步初期,就曾经广泛实践。
近日,第一财经记者与尉文渊进行了一次深度对话。在他看来,三十年资本市场改革扭来扭去、走走停停,很重要的原因是观念没有转变、思想不够解放。
“我们做市场管理,总是习惯性地站在监管者的角度,总是在审视着市场,拿自己监管工作的需求,去强加给市场。但是,换位思考,如果我是投资人,会怎么看这个问题?”尉文渊说,换个角度想一想,将豁然开朗。

“这是谁归纳的,太好了!”
第一财经:中国现代资本市场发展初期,既无基础又无条件,非常艰难。作为最早的开拓者之一,如果你见到35岁的自己,你会对他说什么?
尉文渊:1990年,我35岁。如果让我见到那时候的我,我会跟他说:“小子,你是个幸运儿,你碰到了这么一个大好的年代,难得的历史时期,千万别辜负了!”
第一财经:那么艰难,但你还是觉得当时是一个大好的时代,那现在呢?
尉文渊:同样是好的时代。
资本市场发展三十年,历尽曲折,无论上市公司、交易制度还是监管层面,仍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作为过来人,我很清楚,这三十年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新的发展平台。特别是这一两年,中央对资本市场做了大量战略部署,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很多都是超出我想象的。
比方说,“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9字方针,实际上讲的就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是我们多年都没解决好的事情。这9个字,我看到后心想,这是谁归纳的,太好了!它能看到很清晰的可操作性。按照这个方向走下去,长期困扰中国资本市场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就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再比如,在涨跌停、T+0交易制度方面,现在能看到明显地松动的趋势。这些都对市场化,搞活市场、盘活市场有很大作用。
现在,市场已经具有非常扎实的基础,具有进一步发展的巨大张力。
“不干预”,解决政府与市场难题
第一财经:“9字方针”当中,哪个是最让你惊喜的?
尉文渊:在最初期,这些问题的存在对资本市场发展都会造成很大困扰。
比如建制度。中国资本市场刚刚开张的时候,是在特殊时期、基于特殊需要推出的,基础弱、条件差。
为什么“老八股”后来会凋零?那是因为股市开业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拼凑”,为了能有那么几家公司上市,充起门面,降低上市标准。之后,随着市场发展,我们的工作也面临巨大的问题——没有“法”。公司法1994年才出台,证券法1999年才实施。建制度,在这几年已经取得非常大的进展。
关于“不干预”。1995年之前,我们曾经真的不干预。
交易所设立之初,为了突出社会主义交易所的性质,交易制度设计了清楚的限制,现货交易、不能买空卖空、严格限制涨跌停。不让市场过分波动,不让大鱼吃小鱼,不允许尔虞我诈。
后来我们有了全新的理解之后,把市场完全地放开,完全地自由交易。没人干预,市场处于完全由市场主体自我决策的状态。
第一财经:完全不管,没出问题?
尉文渊:没有出现太多问题。交易过程没有问题,问题主要是出在了上市公司层面。
那时上市公司法律制度不健全,早期我们连会计制度都没有。“老八股”那时候,前几年用的还是“资产平衡表”,还不是现在的“资产负债表”。那个时候企业的会计制度,是为了配合税务部门监控、管理的。
因为都是国有企业,不存在什么股东权益。早期做信息披露,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逮住什么就算什么,没有一套章法,也没有一套规矩可循。那时候,市场制度供给严重不足。
这次“不干预”的提出是有针对性的。监管机关主动表达这样一种意愿,是对解决政府与市场关系一种最核心的支持。
关于“零容忍”,当然是严格执法。如果没有对市场“害群之马”的威慑,对市场漏洞的完善,也就不会有市场的健康发展。
“你的困惑,也是我的困惑”
第一财经:三十年发展成绩斐然,“9字方针”方向精准,下一步发展张力无限。但是,我也很困惑地看到,你作为上交所首任总经理经历的那些问题,到今天还在讨论。为何?
尉文渊:你的困惑也是我的困惑。
你中间谈到了几项,跟我当时的工作是直接相关的。
初期我们的限制非常严格,当时不仅仅是为了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而是有很浓重的意识形态含义在里面。
后来经过一些认识的转变之后,1992年我们把市场完全放开了。放开过程,其实非常艰辛。我当时跟领导表态,是我自己独自做出的决定,出了问题就把我职务撤了。
结果,放开之后,1992年5月21号当天,上证指数翻了一番。人家讲说,这不正常啊?不是的。是前面那些不恰当的价格管制,压抑了股市的正常表现。
那时候股票严重短缺,股价没有不涨的道理啊!硬是给压下去怎么行。后来我们把它给放开了。
当时,这些我们是作为重大改革成就定性的,也得到了高层领导的认可、表彰。市场进入了自由交易的时代。那个年代,虽然我们的市场年轻,但自由交易方面已经是跟全球同步的。
但是很奇怪,到了后来,我们挨到了批评。认为出现了我们风险控制不利等一系列负面评价。到了1996年,好不容易放开的价格又收了回去。
在中国这个国度发展资本市场不容易。从传统思维方式来看,中国是农耕时代过来的,现代商业文明、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都比较晚。就连市场经济都是1992年、1993年才提出来。所以,天然地在传统观念影响下,大家对自由买卖、投机等自然排斥。
第一财经:你本人有没有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
尉文渊:最初我们制定交易制度时,总是有意无意从管理投机角度看问题。我当时算年轻人,但也会这样想问题。
比如,我们说要市场稳定,但是,股票市场怎么稳定呢?它是个风险载体,经济形势好了、上市公司业绩好了,就飞天涨上去,你稳它干嘛?假如上市公司造假了、碰到不可抗力因素灾害了,业绩不好了股价掉下去,你怎么稳定呢?但那时候我们就习惯性地要保持稳定的市场。
这些其实都是对市场规律、市场特点的理解认识不足,有偏差。这个偏差,很可惜,我们一直延续了那么多年。总是把对价格的干预,作为我们防范市场风险的手段。你看,我们现在几乎是全球涨跌停板制度的“独生子女”。
这些在特殊时期是可以的,但要真正走到市场化这一步,让中国资本市场大踏步发展,真正参与国际市场的融合、融通,那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些变化,比如涨跌停板幅度逐步放开。但还是很可惜,二十多年了才开始做这样的变化。而市场在那么幼小的时候,其实就采用过了。
“管理二级市场投机,永远不会有结论”
第一财经:T+0我们也是实行过的,后来怎么又停了?
尉文渊:T是today,当天的意思。股票成交完成之后,把钱交给卖出股票的人,把股票交给买入股票的人,是指这样一个交收的过程。
我们开始搞上交所设计的时候,算来算去,T+4。这还只是上海的同城交易。我今天买了股票,第4天能拿到股票,对手方拿到钱,第5天能卖出。
当时市场交易很不活跃,我们还不懂。后来想,这么低效率的交收制度,市场能活跃吗?那时候是严格的现货交易,拿不到股票是不能卖出的。那套制度当然效率低下。结果呢,做不下去。
其实股票实物的交收,有的时候“T+14”也完不成,还有时候直接把股票弄丢了。股票是投资人给证券公司,证券公司汇总之后给交易所,交易所将纸质股票汇总之后做登记过户。
这在上海都那么难,将来跑到新疆、西藏,怎么解决这些事情?然后后来我们搞了无纸化,把股票收了。实行股票账户制度,将纸质股票变成数字概念,通过数字的交换来解决股票的买卖和权利的转移。完成这一步之后,我们的交收制度,一下子,T+1。
为什么“T+1”?一方面是银行搞异地业务还有一些问题,更关键的是我们电子计算机那套体系,需要闭市之后统一再过一次户。但“T+4”到“T+1”,已经不得了了。
第一财经:从T+4到T+1都这么难,是怎么做到T+0呢?
尉文渊:A股T+0制度我是首创者,其实把它搞出来是很偶然的。
刚才我提到了技术的限制,1992年我们的电脑不堪重负,然后我们请了惠普公司,邀请澳大利亚的专家来给我们做系统升级。
他把程序写完之后跟我讲,他说,我可以当场实现即买即卖。我说这很有意思啊,这不就T+0了么?
但是,当时我突然觉得,这东西是不是太过了?连我这种在当时算是富有理想主义、创新精神的人,都开始担心,会不会形成一天连续买卖交易,鼓励投机呀?我一下就觉得,这事情,一时半时我消化不了。
我说,你先等等,我想一下这个事情。一晚上我睡不着觉,在想这个事情。你怎么想?你老站在一个管理投机的角度去看,当然“T+0”比“T+1”能提供更高的交易频次。
后来,我慢慢就理解一件事——管理二级市场投机,是永远不会有结论的一个工作。因为投资、投机本来就无法区分。一天成交就叫投机,几天算投资?很难量化。搞股票市场,如果有投机,那是生来就有的。就好像一个人生来有五脏六腑,你把脾脏拿掉,那是活不下去的。
你要把过多的精力,摆在那个地方,你会走偏,管理失效,反而会扭曲市场。这也是我在那几年工作当中体悟到的。
第一财经:这就是你前面反复提到的1992年“观念的转变”?
尉文渊:是的。那天晚上,我就在想,站在传统管理角度好像确实有顾虑,但是换位思考,如果我是投资人,我会怎么看这个事情?
你今天买了东西明天才能卖,和你今天买了东西随时可以卖的,品质一样,你选哪一个?是不是能够更好便利投资人的交易,帮他去抑制风险?市场是不是更有效?
换了这些角度去想,我豁然开朗。
我们做市场管理,总是习惯性地站在监管者的角度,总是在审视着市场,拿自己的监管工作的需求,去强加给市场。但换个角度,真地是不一样的。
第一财经:看上去很顺利,怎么又停了?出风险了?
尉文渊:当时做的好好的,市场也很欢迎。电脑化、无纸化,交收同步完成,当时只有中国内地可以做到。
但1994年有领导提出,这样鼓励投机,不符合国际规范。很可惜,又拉回到T+1。全世界的股票市场,没有一家是因为可以快而不快,甚至放慢的。只有我们是这么做的。
当时我比较痛苦的一点就在这。我们在市场的前沿形成了一套方法和观点,但有时候很难得到支持,很多波折。
不过,我感觉情况已经在变化,趋势、方向也很清楚,只是操作步骤可能还是要稳健一些。
我还想告诉大家的是,刚才谈到的交易制度这些改革,市场早就做好了准备,根本不必担忧。因为,我们早期在市场那么弱小的时候就实践过,实践了很长时间,而且实践得很广泛。
“散户是极其渴望学习、善于学习的”
第一财经:你认为投资者都准备好了?可我们超过1.7亿投资者中,绝大多数是散户啊?
尉文渊:在上交所开张的时候,我们没有机构投资人,就是个人投资者。市场所有围绕投资者做的工作,就是围绕“散户”。散户为主,是中国市场的基因。
从一开始,我们在资本市场就有“父爱主义”,不断向投资者强调,“股市风险莫测、务请谨慎抉择”。一天到晚告诫投资人不要误入歧途。后来发现,这些其实意义没有那么大。
我们对中国老百姓的估计,一直不是特别准确。以我这么多年的观察,中国的投资者群体可以用“强悍”形容。我经常开玩笑说,别老说“割韭菜”,谁割谁还不一定呢!不然为什么有1.7亿散户乐此不疲?为什么呢?因为那里有希望,那里有机会,作为幼小的个体来讲,那里有能够改变人生的可能性。这个市场给个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可能,他可以依靠个人的才智、学习,以及风险的承担,去追求成功。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散户“机构化”是化不掉的。
第一财经:所以,中国的散户投资能够经久不衰?
尉文渊:是的。我们早期的投资者,有些表达能力较弱、文化程度不高,比如杨百万,中学都没毕业,但早年他就看到国库券交易的机会,上海有柜台交易,安徽、贵州、四川没有,跑去低价买了,回来市场上卖掉。
散户是极其渴望学习、善于学习的,早期拿BB机、报纸,提高非常快。经过这些年的锤炼,中国投资者也已经成熟了非常非常多。我甚至可以大胆做一个判断,中国投资者可能是全球同类型投资者当中,业务素养最高的。
我们也没办过股民学校,回想起来,当时马路上有股票沙龙,我下班了路过就去听一听。那其实就是在传导信息,传导知识。
如果因为担心投资者不能承受而耽误改革的进程,这可能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财经:市场难道一点也不需要“管”?
尉文渊:那也不是。如果不是早期证监会管上市审批,还不知道有多少造假,闯下多大的祸。
交易所成立之后,领导跟我谈过,想让交易所管审批,我没有接,交易所当时还没有这个能力。在初期,市场环境、市场条件,方方面面都决定了,需要监管部门的审批审核。这个利益太大了。如果没有成熟的市场规范、共同遵守的默契,就贸然放开上市入口的严格监管,后果不堪设想。
不过,现在市场体系、法制建设、中介机构能力都在不断提升,上市公司自觉守法意识也比以前强得多。前几年提出来“证监会能不能不审”,也是比较恰当的。现在交易所比之前强大得多,参照国际做法,形成审核、发行、上市、交易的工作机制,运行挺好,继续推进是有必要的。
到了“迈开大步”的时候
第一财经:30年前,你可能没有想到后来会“真刀真枪”做起来,也没想到今天会发展成世界第二的资本市场。你对下一个30年,是怎样想象的?
尉文渊:我的基本判断,这个市场下一步还会以更加惊奇的速度发展。
因为,前所未有,中央将资本市场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前所未有,确定了这么多资本市场的改革发展政策。市场资源在形成良性循环,跟30年前比天壤之别。
我最近接受采访就说,如果当年给我这个条件,我能把市场做“飞”了。现在我可以说,按照现在这个条件,用不着三十年,这个市场就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你看上市公司增长的速度、投资者增长的速度、交易的规模、动员国际资本的能力,都是在短短几年以内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前些年我们是在爬行,在扭来扭去,在纠结、在挣扎中发展,现在则是真正到了一个迈开大步的时候。因为这个市场拥有了足够的发展空间和足够的信心。
第一财经:我从你的回溯中看得出,对今天资本市场取得的成就,你非常欣慰。我很好奇,如果让你可以从今天带一件礼物给35岁的自己,你会送他什么?
尉文渊:我了解30年前的我。如果你要我带一件礼物给他,那就给他一项充满挑战的使命吧,这是他内心深处最渴望的!
相关推荐
猜您喜欢
- 拥抱战略机遇期是资本市场的责任与担当
- 北京市2021年计划向市场供应集租房约5000套
- 经济日报三评蚂蚁集团被二次约谈:认清垄断危害性 维护良好金融市场秩序
- 注册制下IPO募资占同期A股比例超五成 资本市场更好支持科技创新有优势
- 易会满定调资本市场新征程:注册制、退市、直接融资都是关键词
- 期货市场势头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
- 三部门统一信息披露规则 推进债券市场互联互通
- 护航资本市场,证券犯罪刑期大幅提高
- 【央广网评】对症资本市场“毒瘤” 监管须依法下猛药
- 惨遭“血洗” 比特币全网24小时爆仓38亿!币价突破18万元/枚 创下三大历史记录
- 12月26日四大证券报精华摘要:年内资本市场股权融资超1.65万亿元 逾800家企业IPO申请进行中
- 资本市场或分流存款 银行如何应战?
- 促进居民储蓄向投资转化 市场如何规范 权利如何保障
- 监管力推储蓄变投资 市场期待产生赚钱效应
- 坚持对征信市场实施严监管、强供给、保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