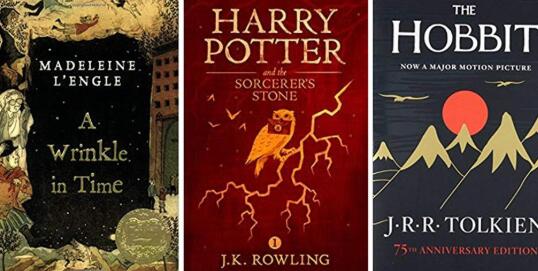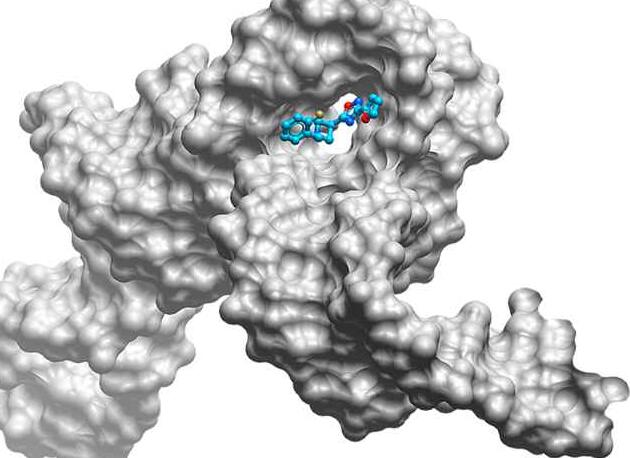“希望新冠之后,能重新探讨疾病的文化隐喻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关系,而不仅仅局限在对一次疫情的应对成功或失败之类的问题上。”2月27日凌晨,高晞在发来的邮件中强调。
高晞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期从事医学史和中国科技史研究。
1986年,高晞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分配去上海医科大学从事医学史教学,开设了“中外医学史”和“医学导论”课程。
当时医学史非常冷门,高晞还是决定选择这个领域从事研究。“医学是研究人的学问,医学史就是研究人对生命认识的历史,我对生命的知识史非常感兴趣,所以一直吸引着我。”
研究一做就是30多年,高晞出版了《德贞传——一个英国传教士与中国医学现代化》《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 》等论著,也见证了研究领域“火与冰”的切换。2003年“非典”是个转折点,疾病医疗社会史一下成为“显学”,各种学术著作不断出现,借这股东风,《瘟疫与人》等国外经典著作的译本也一版再版。
随着恢复过来的中国社会重新调整步伐,进入新一轮经济高速发展,“非典”的创伤逐渐被遗忘,疾病医疗史研究再次转为沉寂,有些学者重新换了研究方向。
直到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暴发,“宅”在家的学者们,手机再次被各路记者拨通。
污名化疫病是为掩饰罪恶
第一财经:古代麻风病人被称为“天谴”,备受歧视。新冠肺炎暴发后,国内一些地方也出现对武汉人或湖北人的恐慌。历史上对疫病的污名化由来已久,在你看来原因是什么?
高晞:“污名”一词来源于希腊文,是指一种标记或文身,被刻割或燃烧在罪犯、奴隶或叛徒的皮肤上,成为一种标识,以此明示他们是有污点或道德败坏的人。这种标识同样还警告这类特殊人物,避免在公共场所出现。古代印度修鼻术特别发达,因为印度对偷情男子的惩罚是割去鼻子,于是他们会尽快修复自己的鼻子,将印刻在身体上的标签隐藏起来。
疾病污名化几乎在所有的历史阶段与世界各文明圈中都存在,表面上看是对病,实际重点落实在“人”身上。以麻风病为例,中世纪黑死病(鼠疫)暴发前,麻风病是肆虐欧洲最严重的疾病,欧洲人采取的措施是将病人赶出城镇,这样做并非因为麻风病人会传染要隔离,而是恐惧病人面部布满可怕的结节,以及身体变形。他们认为这是“上帝”对世界“罪人”的惩罚,所以将麻风病人驱逐出城,令其失去基本的社会权利。14世纪鼠疫在全欧洲暴发时,麻风病突然莫名地消失了,科学家至今也没有找到原因。但社会对麻风病的污名却没有消减,1909年波兰有位女作家写过一部小说《麻风女》(Trędowata),多次被翻拍成电影,故事主要讲的是一个青年女教师嫁入上层贵族家庭而不被接受,最后还说她是有麻风病,导致她发疯。
第一财经:中国的情况呢?
高晞:中国传统社会也将麻风病人唤作“恶人”,会被剥夺祭祀权利。古代明确有不准与麻风病女子结婚的惯例,所谓“女有五不娶,世有恶疾不娶”。
历史上,对疾病的污名和恐慌还与疾病的社会和文化特性有关。比如15世纪在欧洲流传的梅毒,鉴于该传播方式的特殊性,涉及人性、社会道德和国家名誉,因此各国都以假想名来称呼它,意大利人称之为“法国病”,法国人说是“那不勒斯病”,荷兰人命名为“西班牙疮”,西班牙抱怨是“波兰疮”,于是由一国传到一国,很快就在欧洲蔓延开来,连英国亨利八世和查理五世都染上梅毒。后来,欧洲找到一个更为普遍而又可推脱罪名的说法,说“梅毒”是由哥伦布和他的同伴们从美洲新大陆带回来的,是美洲人对欧洲人入侵和掠夺的报复。到19世纪,西方世界又出现一种新说法,认为“梅毒”发源于中国。如此循环往复,目的都是想逃离被污名化,只是采取的方式是以一种污名化去掩饰另一种罪恶。
历史上抗疫主力一直是民间医生
第一财经:有种说法是,医学在中国历来都和政治有关联,比如《国语》里就说“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如果古代医学中掺杂了政治因素,是否会影响医学发展,尤其是面临大规模疫病暴发时?
高晞:“上医医国”的意思,不是指医生或医学要对国家负责,或者说古代存在医学政治的概念。“上医医国”是指医生的修养,即医生的视野和心胸要高远,要有能够“医治国家”这种崇高理想,而不是眼里只有病人,所谓“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亦是同样的道理。
自宋之后,中国医生都争当“儒医”,在个人的道德与品性修养、医学知识积累方面都向经学或理学靠近。因此,中国传统医学中糅杂的不是政治,而是经学。医儒不分是中国传统医学的特点,医者必先为儒家。“良医”是中国医生的至高境界。因此,在面临大规模疫情暴发时,民间医生便成为抗疫的主力,而不是国家(朝廷)机器。
中国历史上,疫情暴发会造就名医和名著,比如东汉张仲景,传说他曾任长沙太守,但却以名医身份留载。因为当时多次暴发瘟疫,家族中过大半人口都死于疾病,促使他转向研究医学,著成中医经典著作《伤寒杂病论》。
第一财经:发生瘟疫时,传统医学如何应对?
高晞:中国历史上,医生在抗疫时主要做的是:一、对患者采取隔离措施,在云梦睡虎地秦简中就有对麻风病人审查与隔离的记载,医生在民间的养病坊之类的医疗场所就诊;二、研究疫病,探讨疾病根源,创立新学说和医学理论,中医经典著作《伤寒杂病论》和《温疫论》便是疫情大暴发后的产物;三、发明种痘术对付天花,在牛痘术发明之前,中医人痘是对付天花的唯一手段;四、施医送药,研制对付疫疾的方子,中医中有专治霍乱、痢疾、疟疾、天花、伤寒、喉痹的各种方药。
宋朝以“救活率”奖惩官员
第一财经:中国历史上很多农民起义都是因为疫病暴发而起,但为何历代统治者在瘟疫应对上一直缺乏顶层制度设计,而是直到清代都延续交由地方政府处理的传统?
高晞:自上而下建立系统的防疫制度以应对瘟疫,是近代公共卫生兴起的产物,这也与实验医学的进步有关。随着近代医学的发展,医生和科学家认识到疫病是由某种因子导致的,或是污秽的“瘴气”,或是空气中流通的看不见的“小粒子”,明白疾病与生活环境和空气有关,这些认识改变了病与星相有关或源自上帝对世人的惩罚等传统看法。
而中国古代,一般相信瘟疫流行与“疫鬼”有关。“大疫”到来后,病人或病家在寻求医疗救助时,往往借助巫术性的医疗法和预防措施,比如“避疾”“祷解”“祝除”“逐疫(傩)”“辟除”等。曹植在《说疫气》里写到建安二十二年流行的瘟疫时,就说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
农民起义往往是借疫病之名,认为这是上天或神的预示。因为他们认为疫病是当朝遭天谴必亡的特征,以此否认当权者的合法性,强化起义的合理性。因而古代中国,无论是对病因的认识,还是对瘟疫暴发或流行的解释,都不可能产生近代意义的防疫意识,建立公共卫生体制。
当然,在清之前,也有中央政府对疫情采取主动应对和积极预防措施。宋代政府在疫病防治和救助中就承担了主体责任,政府先后颁布了190条与疫病相关的诏令,涉及疫情信息收集、通报与处理,时令与疫病流行的关系,以及派医诊治、施散药物、隔离病人、施送棺木掩埋尸体、保护水源、改善城市卫生、考核政绩等。
第一财经:古代地方官员出现瞒报疫情,或者防疫不当时,会有哪些追责?
高晞:宋代在这方面有着比较严格的制度,重视疫情信息的上报与处理,还有信息的传播和使用。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春,全国很多地方都疫病流行,但地方官吏的奏章里却很少这方面信息。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引起宋仁宗的警觉,随后发布诏令说,“岂非言路壅塞所致乎”,并规定凡是有关州县疫情报告的公文及臣僚奏疏,中央各部门不得阻留,要“直达于上”。宋朝政府对参与疫病救治的官员,按其救活人数予以升迁和奖惩。疫病发生时,皇帝通常还要发布“罪己诏”,进行反省下诏罪己,封神祭祀。
明清官民互动经验值得借鉴
第一财经:到了明清和近代,疫病发生时官方和民间互动更多了。你觉得这种互动中有哪些经验值得借鉴?
高晞:一旦疫情发生,地方政府与民间救助往往同时展开,有几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一、合作建立临时防疫抗疫场所,为隔离安置患者创造条件。明清之前,一旦疫情暴发,地方政府会征用诸侯空闲的官邸,收容安置病人。晚清时期的上海,每年夏季都会有民间团体设立的时疫医院,以对付夏季暴发的传染性疾病。中国红十字会创始人沈敦会,就是其中的代表。二、借助民间的慈善组织,免费发放医药、救济病贫人家。三、借助同乡会等各种社会团体,帮助地方政府施送棺木安葬死者。顺治年间,杭州的悲智社为病人送药、向死者施棺,并设义冢,帮助掩埋尸骨。四、中医义诊,提供应对时疫的方子。
第一财经:古人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但随着中国现代卫生制度的建立,国家权力开始介入到私人领域。在此过程中,你觉得应建立怎样的监督和约束机制,才能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取得平衡?
高晞:我想用一个历史故事来回答你这个问题。1910年春节前夕,东北鼠疫暴发。当时东北已成为日俄的势力范围,俄罗斯人在哈尔滨、日本在沈阳都建有医疗卫生机构,他们首先采取隔离措施,将患病的华人和感染华人一并赶入隔离区。在北京驻华使馆区,更是拉起隔离线,禁止华人进入,并要求清政府采取相同的措施对待非西方人管辖区内的华人。时任东三省总督锡良宣布封闭铁路,不允许在东北打工的劳工在春节期间返回关内过年。
中央政府委派的卫生专家伍连德抵达哈尔滨后,将疫区划分为四个区,在警察和士兵的保护下,对疫区的人员进行全面隔离、消毒,焚烧尸体,最终在3个月内消灭疫情。1911年4月在沈阳召开的国际鼠疫大会上,中国钦差大臣施肇基对来自11个国家的国际科学家说:“中国人民并不像某些东方民族那样具有某种偏见,然而他们十分厌恶那些对他们家庭生活进行非正当干涉或侵犯的人。因此,那种显然非常残忍的工作,例如快速且强制将鼠疫病人与他们的家属拆散,把某位家庭成员送进鼠疫医院又把其他成员送隔离营,这对我们而言实在是项艰巨的任务。”
1910年的这场抗疫运动,是中国医学历史的标志性事件,它的成功喻示着中国医学开始步入近代卫生行列。100年前的中国医生和官员非常艰难地将中国人民带入了近代社会,希望我们能够珍惜前人付出的代价。
第一财经:与“非典”相比,你觉得“新冠”之后医学史研究是否会有新变化?
高晞:“非典”使疾病史这门完全边缘化的学科成为显学,也是有点出人意料。这十多年来,有许多优秀的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者进入此领域,开拓出诸多新方向新题目,成绩斐然。只是,这股热浪后来逐渐退潮,我看到许多当年热衷于医学史与卫生史研究的学者离去或转向。
“新冠”之后,是否会再次激发医学史的研究热情,我不知道。但我相信医学史或疾病史的研究肯定会上一个新的台阶,因为本次疫情对人性的冲击力度超出了“非典”,我注意到媒体较多地从历史的维度思考与分析本次疫情,这是医学史发展的新契机。我想我们需要从更广阔的视野思考生命意义,反省个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探讨疾病的文化隐喻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关系,而不仅仅局限在某种疾病史,或是对一次疫情的应对成功或失败之类的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