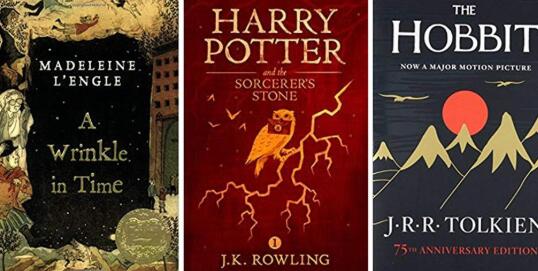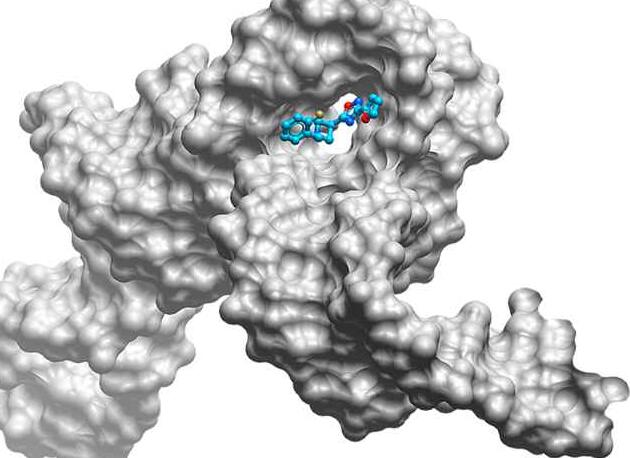一个作家的一生能写多少书?一年出三四本应该不少了,如此算来,一生写个200本绝对属于超级写家。但在艾萨克·阿西莫夫的简历面前,这个数字被证明上不封顶:他在40年间出书接近于500本。
读者帮他计着数量。在他出版第100本书、第200本书、第300本书的时候,都有仪式,他自己也乐于直接以编号给这些书命名。然而他自己的生日却是模糊的,双亲没有记住,后来是他给自己定了一个1920年1月2日的出生日。当然,这种“花絮”是科幻读者眼中的“美谈”,是一位传奇偶像身上少不了的趣味点。

“报复性”书写狂
一个写这么多书的人,是传奇,但也是无聊的。因为谁都能想象得到,围绕他的议论总是离不开昼夜不息地勤奋敲打打字机上的键钮;总是离不开他写的第一本书,以及他写的最著名、最有影响的书,这么两个主题。不过在阿西莫夫这里,还是有些别的事情值得一说,比如他学习英语这一点。他的母语是俄语和意第绪语,因为他是个俄罗斯犹太人。他在1923年被父母带到美国,住在了纽约的布鲁克林,而这对父母也是从来不讲英文的。阿西莫夫的英文全是自己读书、读报加上后来泡图书馆学来的,他学会之后,还教给了妹妹。
喜欢上科幻是他读各种科幻杂志的后果,可是,这个体裁跟他称得上疯狂的写作欲望未必有很大的关系。30~50岁之间,阿西莫夫疯狂地出书,出满了100本。有了这么一个庞大的“基本书库”,后边20年他又不住地从中翻新,才使得出书速度继续提上去。实际上,在这头100本书里,虽然他潜心打造了一个“银河帝国”,并出版了他赖以扬名立万的“基地系列”,但他写的已不全是小说了,而是颇有一些如《阿西莫夫事实之书》《阿西莫夫幽默宝典》之类非小说或难以归类的作品,显示了他的全面,更不用说他在写作之余痴迷化学实验,这可绝不是一种典型的作家风格。
无可否认,他是一个无比有才的人,polymath(博学家)这个源自文艺复兴时期的词用在他身上再合适不过——他就如列奥纳多·达·芬奇那样具备多种才能,善于多方面汲取知识,善于写作,更善于出版。不过,阿西莫夫本人在说到自己如此多产的缘由时,并没有说自己有多么热爱科幻,这方面的灵感是多么丰富,而是说他一直有一种焦虑,觉得视觉正在盖过书写,“看”正在排挤“读”的空间,而他是出于为读写文化伸张尊严,才“报复性地”著作等身——事实上三四倍于他的身长都不止。
报复性地著作等身,以及对读写的痴迷——这就不能不把阿西莫夫同他的犹太之根联系起来了。
“顽梗”的犹太人/地球人
犹太人向来有“书写崇拜”的名声。因为围绕旧约圣经及律法书的一系列文本,犹太孩子从学龄前起就要接触并沉浸其中;与此同时,他们传统上又禁止造像,从而在日常生活中甚少有目迷五色的体验,而是被文字载体所包围。文字让人惯于聆听和沉思,而犹太文本所包含的大量故事、教义以及律法的内涵,启发阅读者去沉思和辩难,那些善于钻研和辩难者,日后可望成为受人尊崇的专业宗教和律法权威,即“拉比”,他们有了威望,言论思考也被纳入到最初的文本中。所以犹太人的书是活的,会长大的。
阿西莫夫并不是什么犹太教徒,他的父母甚至没有给他过过犹太教传统中极为重要的成人礼。可是,热爱阅读,对书写的敏感,以及维护书写的尊严,这种特点在他身上很是突出。1950年的战后美国,电视电影来到黄金期,更刺激阿西莫夫产生了对书写的危机感。他在那年出版了第一本科幻小说《天空的卵石》,此作之前就作为他正在准备的“基地”系列而在杂志上发表过,文笔极成熟,不过当时还未满30岁的阿西莫夫还不是完全自信。小说一上来就写到主人公、一个名叫约瑟·舒瓦茨的60岁的裁缝,在未来的某一天从辐射过度的地球上突然消失了:看到“约瑟·舒瓦茨”这个姓名,就可知他十之八九是犹太人。似乎,像所有初试身手的写作者一样,阿西莫夫写的是自己最熟悉的人和事。
倒并不是说,一个非犹太背景的作家就不能故意给人物取这么个名字了。可是阿西莫夫后来自陈,他虽然没有明说那是个犹太人,“但我从未见到一个人认为他不是犹太人的”。约瑟·舒瓦茨出场的时候,口中吟着一首诗,是19世纪英国名诗人罗伯特·勃朗宁的作品。勃朗宁写过一系列叙事独白诗,这首便是其中之一,但和其他的诗相比十分独特的是,这一首的题目叫“本·埃兹拉拉比”。本·埃兹拉拉比是确有其人的历史人物——一位生活在12世纪的犹太拉比。在诗中,他对着一群不知是什么人的听众侃侃而谈,他说他已经老了,然而,他希望听众们和他一起变老;他说年轻是不好的,年轻人对人生没有洞察,只会狂躁愤怒,追求不切实际的伟大,最后沦为野蛮;相反,老人则会更懂得爱自己,更少关心世俗的事情,而注目上天。老龄让人深刻地活在当下。
本·埃兹拉的哲学特色,在于矛盾的对立统一,诗中的他虽然一副倚老卖老的腔调,可他最后却强调,任何的人生阶段都是整体的一部分。阿西莫夫让他的主人公读这样一首诗,或许主要想给约瑟·舒瓦茨安排一个与他的年龄相匹配的心境,但就在这种简单的安排中,阿西莫夫显露出了与他的犹太身份有关的“知性”风格。
写《天空的卵石》时的他是谨慎的,想象的野马尚未完全撒开四蹄,他的故事得依靠那些他最有把握的东西。他后来自述说:在这部小说里,他“写了一个顽梗的地球人群体,他们面对一个看不起他们的英国,他们中的一些人觉得,这种关系类似于公元1世纪的犹地亚和罗马帝国,他们也知道自己可能是对的。”这就完全承认,他是基于自己对犹太历史的了解而构思这一小说的,“顽梗”一词正是旧约圣经里上帝对犹太人的描述:你们这些硬脖子的,死也要犟嘴、要反抗、要跟我对着干的人哪!然而正是在这种对抗中,他们形成了“知道自己可能是对的”的自信。犹太人从来就不害怕身处少数;真理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这话在他们听来绝非狡辩。
地球在阿西莫夫的第一部正式意义上的科幻小说中就完蛋了。幸存下来的是一群智力超常的“百科全书编者”——一个被阿西莫夫赋予了意义的专有名词——他们被隔绝到银河系另一头的一颗行星上,以便在即将到来的黑暗年代里保全人类知识的最后残余。附近行星上来了许多敌对生命,他们除了自己的头脑之外毫无可以自保的依靠,这些未来的“书之人”开发出了更加先进的技术,开辟了秘密商队路线,最终将异星人类征服并且归并入自己的种群。人类最引以为豪的就是自己的知识了,而作为犹太人,他们历来最引以为豪的,就是掌握了人类知识中最重要的知识。
在自述中,阿西莫夫是这样说的:“我从未特别地想到过犹太人与机器人、毁弃的飞船、六个太阳的诡异世界有什么关系……然而它时不时地自己就会出来。”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下意识”;他把未来人类全体的灾难与当下一小群人类——犹太人——的灾难联系在了一起。在《天空的卵石》里你甚至还能看到“马萨达”这样的名字,这是公元66年,最后一批抵抗罗马帝国军队的犹地亚犹太人战斗和灭亡的地方,当然,是犹太人眼里光荣而神圣的地方。靠着这种设计,一向仅仅意味着过去,意味着与历史传统的紧密联系的“犹太”二字,同外太空和火箭飞船挂起了钩来。
自造规则的科幻宇宙
当阿西莫夫的银河帝国画卷随着一本本书的出版而彻底展开,他就自然地要被问及这样的问题:你信神(上帝)吗?犹太人据认为都是信上帝的,像阿西莫夫(尽管他也算是从以虔诚著称的东欧犹太社会里出来的人)那样,在故事中多处体现出犹太人的视角,却又完全以现代宇宙观来统摄故事而只字不提上帝,其中的矛盾自然会让人好奇。阿西莫夫的回答,既非“是”也非“否”,他说:“我没多想过上帝的事。”
这回答相当聪明,但并没有超出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可能想到的范围之外。他实际上是说,上帝与他无关。
因为上帝不是一个符号,或一个莫须有的存在;上帝意味着一种秩序,一套规则。喜欢科幻的人中有两类居多:一是不识愁滋味的、想了解灾难将会如何降临的年轻人,二是人生巅峰已过很久,开始真正心里踏实地“展望未来”的中年人。总之,两者都不太寻求像读一般意义上的小说那样,代入主角们的日常,感受他们对功名与爱情的渴望和犯蠢后的沮丧。他们喜欢科幻小说的地方,正是它们自造一些规则来统治它们自己的宇宙,其生灵依照这些规则去生和死——这样的一个宇宙,是无法见容一个犹太-基督教意义上的上帝的存在的。
然而设计和建立这些新规则的科幻作家,自己也和读者一样,是活在一套规则里面的——不过,他们对此高度敏感,总想要表达自己或赞成或否定的态度。和阿西莫夫一样天才的阿瑟·C.克拉克,1941年就职皇家空军,担任雷达技师,他坚持在自己的吊牌上标示“一个泛神论者”;罗伯特·海因莱因在《时间足够你爱》中,借一个人物的口说:人只有站在宇宙之外,才能观察宇宙的种种神秘。在这二位的心里,作为西方社会基础的信仰体系,都是需要深刻质疑阿西莫夫也一样。他本质上是个人文主义者,观照着地球人的问题;他还写过一本专著,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圣经。所以,他其实一生都厌恶必须就犹太-以色列的问题做些表态,但他所描写的很多情节却又不能不让人联系到犹太人——历史上的、传说里的或现实中的犹太人。当然,这对他来说不是什么难题,因为他能出如此多的书,足以表现自己在各个领域都各有专攻,互相并不串门:比如,他所汇纂的幽默集,就反映了他作为一个会说意第绪语的犹太人,对于独步天下的犹太幽默的深刻认识。
讲笑话是他的爱好——1974年,他在一部美国犹太科幻小说家精选集的序言里说,自己很擅长用意第绪语方言说犹太笑话。他更说过一个真实的笑话:他幼年时,经常躲在角落里,看自己暗恋的美国姑娘吃三明治,人家在面包上抹黄油,阿西莫夫咂着嘴巴默默地想,那是芥末,那是芥末啊……
来自欧洲的犹太人,无法想象黄油的味道。他们用来抹面包的传统的、符合教规的酱料,是芥末酱。即便阿西莫夫家里完全世俗,即便他从小就与宗教无涉,他也不能想象,一个牛肉三明治里怎么能夹黄油。
科幻与犹太思维
然而,阿西莫夫的小说里虽然没有上帝,却给我们探寻犹太人的思维空间开辟了一条理想的途路。因为要在现有的规则之外另造一套规则,首先就需要思考现实之外的其他可能,这正是犹太人所擅长的。尽人皆知他们爱提问,但却少有人知道,犹太人提问起来可以如此无视一切界限,他们最爱问的就是“What if”——针对任何一个表述,他们都能问一句“但如果……又会如何?”比如,1945年3月写出的短篇《死路》,就是基于“如果人类不得不求助于外星人,又会如何?”这一问题而来的;而《最后的问题》这一备受推崇的短篇,则是基于“如果电脑成了上帝,又会如何?”这一问题。
例子数不胜数。科幻大师常常被誉为神人,擅长实操层面的科研工作,以此来滋养写作。海因莱因、阿西莫夫和另一位科幻名家L.斯普雷格·德康,当年一同在费城的空军实验基地搞武器研究的经历就十分传奇;然而实际上,“科幻”一词中,“幻想”往往走在“科学”的前面。幻想是纯头脑之事。科幻大师和“灾难想象作家”之间的差异,就在于后者只是想象地球和人类万物会遭遇怎样的倒霉事,而前者可以就一切目前尚未发生的甚至子虚乌有之事提出大胆并精妙的想象。
在犹太思维中,未发生的事情似乎天然就被一个平行空间所收容,在那里展开了它们自己的故事——一颗没有丢下的原子弹,它在另一个空间里是丢下了的,从而出现了另一个版本的现实。而提问就是开端,就是触及这些空间的方法。在“苹果落地”的故事里,牛顿的思考“苹果为什么落地,而不往天上飞?”转换一下,就是很典型的犹太式发问:“如果苹果不是落地,而是往天上飞,又会如何?”科学和科幻,真就是在一个路口不同方向的张望。
顺便说,英国人牛顿没有犹太血统,但他的名字“艾萨克”,和俄国犹太人阿西莫夫的大名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即便在美国也不安全”,在自传中谈到反犹主义时,阿西莫夫写道。据他说,很多在美国的犹太作家要写科幻,都不敢用真名,因为担心他们被读者认出是犹太人后,故事中所描写的被流放的、受迫害的人类,也都成了对现实政治的影射。他们都改名了,而阿西莫夫则没有,他把作为犹太人的不安全感跟他想象中未来人类的不安全感融化在了一起。他从俄国带到美国来的大名留在每一份手稿中,它们被装箱,收在了波士顿大学的71个书架上。
科幻小说制造的不安全感更大且更丰富。科幻小说让人想象得越远,引起的恐惧也越彻底,关于无限扩张与膨胀,关于熵,等等。越深的恐惧催生越杰出的英雄,再由英雄吸引来追着故事读下去的死忠。这个套路固然永试不爽,寇克船长为1960年代开始的“星际迷航”电影招来了无数死忠,并使阿西莫夫成为传奇;然而深信神的人,却不会只想着寇克,而会注意到“原初系列”中反复传输的一个理念:要识别伪神。这个伪神,在圣经里亚伯拉罕和摩西的时代,是那些无生命的、具体的偶像,是臭名昭著的金牛犊,也是异教徒崇拜的巴力;而在现实中,它就是那些失灵的计算机。说不清这是对灾难的预言,是对人类的警告,还是相反——是诅咒。如阿西莫夫这样凭想象来干预人类的认知的写作狂人,总有一半身份是先知,另一半是潘多拉魔匣的启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