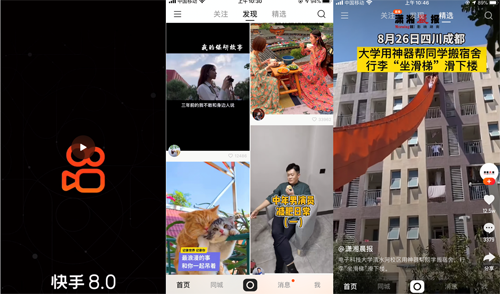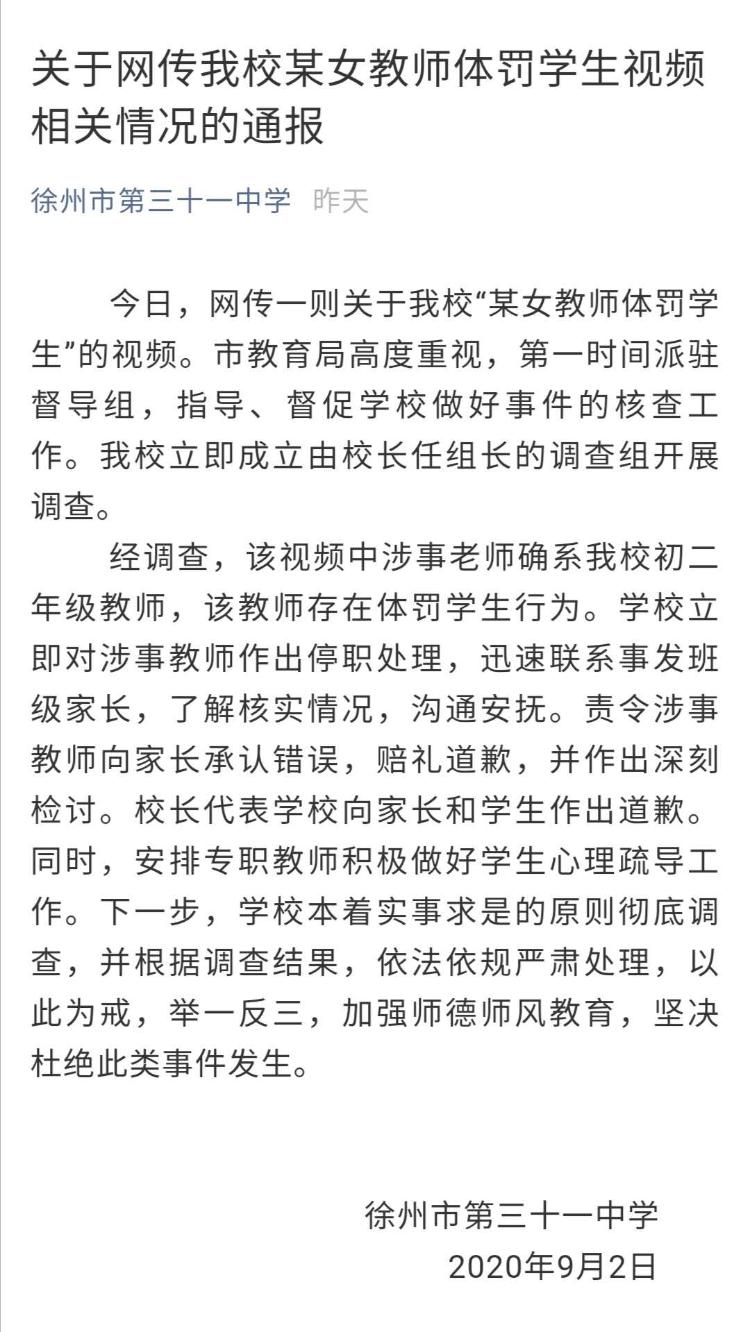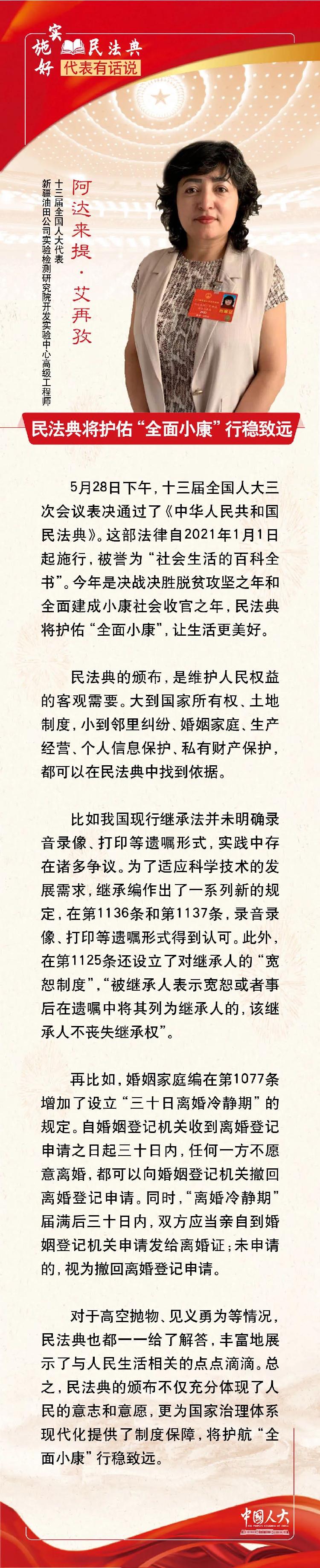直到今天,已经年届五十的郝同学仍然对初中校长充满了感激。
当年,郝同学是个体育生。体育生一般文化课成绩都比较差,但在打架方面却很有“优势”。一次,郝同学的朋友和别人打架,被校方处分,“布告”贴出来了,郝同学等“抱打不平”,趁着夜色把“布告”揭下来了。这位校长知道是郝同学干的,二话不说,又写了一个“布告”,责令郝同学等彻夜看着“布告”,以防再次被揭。
那一晚,校长办公室的灯亮了一夜,郝同学等在外边忍受了一夜蚊虫的叮咬。后来,郝同学说,校长是真的把他治服气了,也刹住了他的性子。他说,没有这位校长,就没有他的将来。郝同学的强项是短跑,后来,他的百米成绩进入了11秒之内,被曲阜师范大学录取,后来又从事教育行业。他充分理解了校长的苦衷。
之所以讲这个故事,是因为《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征求意见稿)》(下称“规则”)的公布。这个“规则”被坊间解读为重新赋予教师以“戒尺”,因而引起广泛的议论。
笔者认为,评论这个事情有两点很重要。一是,“规则”的出台很有必要。因为“规则”通过严格划定的惩戒范围和逐步升级的惩戒手段,给教师赋权,同时通过规定几种“惩戒禁忌”,明确教师在管教过程中的责任边界。二是,师道尊严,“师”的“尊严”来自于老师对自己责任的认识以及自己的以身作则。相信如果没有当时校长室的那一夜灯光,也没有郝同学的“服气”。
在教育手段上,失之于软是当前普遍存在的现象。这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家长的压力。家长把孩子当宝贝,别人、包括老师都说不得,更打不得。以前家长会对老师说,我家孩子不听话你就骂,再不行就打,现在这样的少了。有时候老师多说几句,罚站一会儿,家长可能就会去告状,结果可能是老师要受学校批评,重则丢掉饭碗。
既然把孩子交给了老师,就要充分信任老师。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曾给太子请了一位老师,有下面一段对话(大意)。这位老师问朱元璋:太子顽劣,可打否?朱元璋答:打不死就行。
现在的情况是“学生权”的上升带来的“老师权”的下降。如前述朱元璋与太子老师的对话,教师惩戒学生就如同父母教训不听话的儿子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随着西方的一些教育理念的引入,人们开始对教育惩戒产生疑问。随后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老师不敢管,不愿管。最根本的原因是老师不愿意担责。
现在提倡的是赏识教育,但这仅仅是教育的一个方面。分类指导、因人施教才是应有之义。不可能所有的学生都可以通过赏识教育达到教育的效果,尤其是对价值观、行为方式等还处于懵懂阶段的学生来说更是如此。
上述现象的产生除了与我们长期回避教育惩戒,对其研究不够、研究不深有关之外,还与我们的法律法规对教育惩戒权的规定不足有密切的关系。
比如,我国教育类的法律法规对教育惩戒权的规定过于原则化,仅在《教育法》第二十八条第四款规定了教师有对学生进行处分的权力。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教育惩戒权给予肯定,但没有明确提出教师拥有惩戒权,更没有明确提出教育惩戒权实施的条件,实施的方式、范围、限度及教育惩戒权滥用的后果以及所采取的救济途径等。
2017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人大制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陈舒指出,要赋予教师更多教育孩子的权力。2019年7月9日,《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的提出,将保障教师依法享有教育惩戒权。这次“规则”出台,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在制度层面上的“矫枉”。
有了“规则”,就等于给予了老师“戒尺”。但这把“戒尺”什么时候打,打在谁手上很重要;更重要的是,作为老师要具有打的资格,尤其是人格魅力,否则会适得其反。
这次“规则”的“征求意见稿”按力度把惩戒措施分成三档:一般惩戒、较重惩戒、严重惩戒。一般惩戒,从点名批评、罚站面壁,到打扫卫生、家长陪读,再到停课停学、限期转学;“较重惩戒”对应的是“学生违反校规校纪,情节较重或者经现场教育惩戒拒不改正的”,“严重惩戒”对应的是“学生违规违纪、行为失范,屡教不改的,或者严重影响教育教学秩序的,或者有欺凌同学、辱骂殴打教师等恶劣情节的”。
这样的分类施策,有利于教师在具体教务中,按图索骥,对号入座,可操作性强。但作为老师,一定要认识清楚自己的职责,就是教书育人。开除学生,并不是老师的本分,把不听话的学生教育成人才,作为老师才更有成就感。
另外,最重要的是,持有“戒尺”的老师应该考虑自己是否有资格持有“戒尺”。当一个老师课堂上不讲,课下开辅导班去赚取“外快”的时候,“受教”的学生只能给予耻笑,并且这会给学生的世界观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这就需要作为老师的自谨、自律。
社会环境在变,教育环境也在变,教育方法也得与时俱进。此次对惩戒规则征求意见,说明国家在教育环境的营造上,力图构筑一套界限明确、可操作性强的规章制度。要达到这一点,需要社会舆论环境的配合,家长的与时俱进,也需要老师的回归本真。没有“戒尺”的老师与“病猫”无异,德高望重的老师才能配得上老师这个称号。 (作者系第一财经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