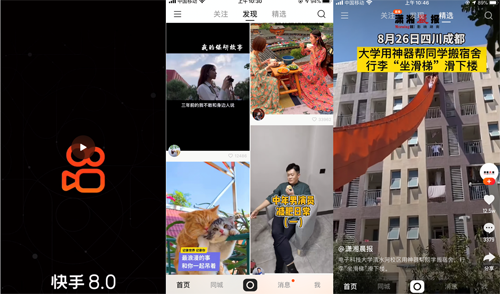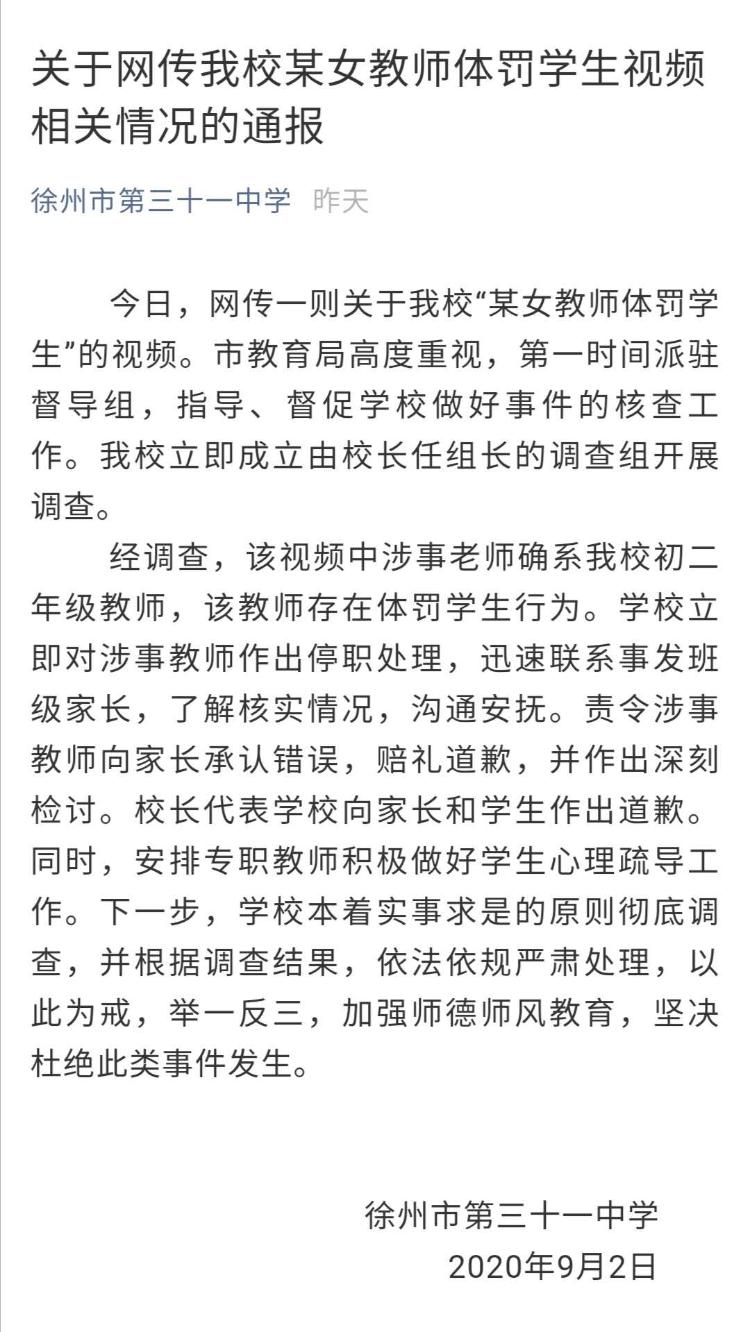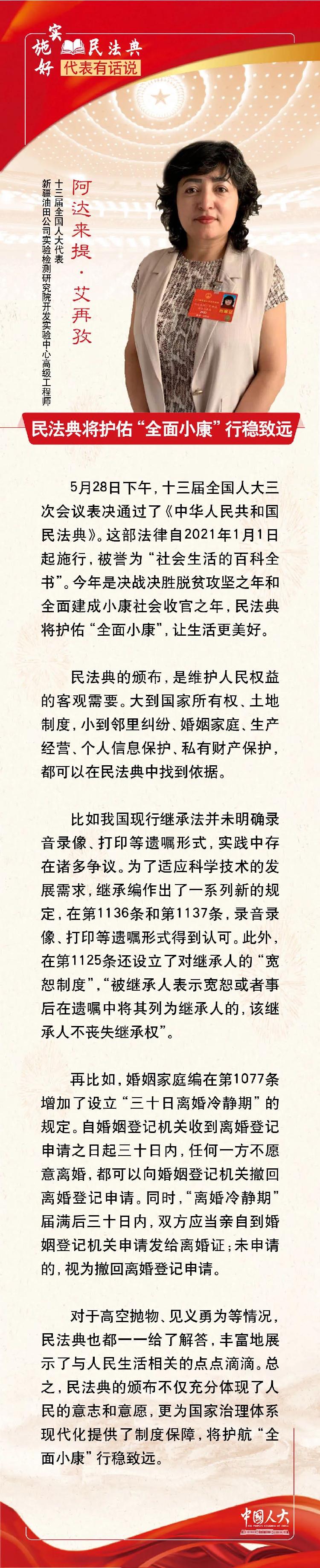在经历了2016年短暂的“同步复苏”(Synchronized Recovery)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2019年的全球经济定义为“同步放缓(Synchronized Slowdown)”——这个定义十分贴切,今年全世界90%的经济体出现了经济下行。
直观看来,关税和贸易壁垒是重要原因,中美又首当其冲。美国对中国进口的平均关税水平从2017年的3.1%上升为目前的21.2%,这在WTO诞生以来的全球语境下让人直感“穿越”。由于全球产业联结和架构在全球价值链之上,包括中美在内的贸易摩擦直接将全球主要经济体拉入了贸易下滑的区间,2019年上半年全球贸易量增长率为1%,为201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贸易下行的另一面是制造业疲弱。尽管导致制造业疲弱的原因还包括全球制造业周期性因素和服务业整体比重上升的结构性因素,但贸易摩擦将这些因素集中并且放大。贸易下行和贸易摩擦还导致投资走弱,投资走弱与进口走弱又相辅相成,其中企业信心受到重创是催化剂。
这一切都令人担忧。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所有这些担忧都还不是最值得担忧的核心。
通胀去哪儿了?
回顾一下上世纪8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故事,有助于我们来理解今天全球的最大担忧。
1979年,美国通胀率接近15%,失业率居高不下,前所未有的“滞胀”局面打破了“菲利普斯曲线”。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保罗.沃尔克上任第八天就宣布,把美联储基金利率提高50个基点到11%,再过两天又宣布把贴现率提高5个基点到10.5%。到了1981年夏秋之际,联邦基金利率高达19.1%,商业银行优惠利率21.5%,而通胀也终于在1981年降为6.5%,再过两年又降到4%以下。
比照今天的情境,这里有几个核心关注点:第一,和当时形成极大反差,今天的通胀消失了。第二,央行的政策(利率)空间消失了。最后,尽管同样面临“菲利普斯曲线”失灵,但由于前述两个原因, 让“金融巨人”沃尔克当时一战成名的模型——全球央行盯住通胀目标的模型在今天看来彻底失灵了。
今天,除了少数国家外(阿根廷、土耳其),大多数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通胀都处于历史低点,占全球91%GDP的经济体的通胀水平都低于政策目标。如果不需要担忧通缩,这也许并不是一个坏消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通胀去哪儿了?
经济学家对此做了大量研究。通胀预期可能是原因之一,由于过往的成功努力,通过对通胀目标的兑现,全球央行在制服通胀方面的公信力(参见沃尔克案例)让人们相信,没有必要去抢购生活用品塞满冰箱甚至堆满房间;其次,科技和数字化的快速发展,让最后一份数字化产品的可变成本几乎降至0,从而让低价成为可能;同时,科技巨头的平台(双边或者多边)策略往往是交叉补贴,通过免费获得规模之后实现“赢家通吃”,从而让免费无所不在;最后,全球化在过去几十年蓬勃发展,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例如在中国)配置资源,将成本降至最低,大幅提高效率,也让价格结构性持续下降成为可能。
如果说价格下降、通胀消失总体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坏消息,货币政策空间消失则是一个确定的坏消息。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利率水平都处于下限,或曰零下限(Zero Lower Bound)。危机后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尝试刚刚起步,就被经济下行压力牵制,美联储重启降息、ECB重启QE。以往每个利率周期,美联储都有空间从6%左右的利率水平持续不断降息,从而为经济注入动力;而今,这个空间根本不存在。而负利率正在成为新常态,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负收益率债券的规模已增至约15万亿美元。IMF预测,在2022年底前,约20%的政府债券收益率水平将处于负值区间。
让局面更加糟糕的是,在以上两个背景下,全球央行赖以安身立命的模型——“菲利普斯曲线”消失了。所谓“菲利普斯曲线”,大致意思是通胀和失业率反向变动,经济繁荣时,失业率低,通胀率高,央行加息予以应对,反之反是。而今,全球经济进入了奇怪的组合:主要经济体的失业率处于历史低点,然而,通胀却出奇地低,同时,经济动能疲弱,央行无法进入加息周期,也没有政策空间降息承托经济。
央行将如何应对这个困局?
针对“菲利普斯曲线”和通胀消失导致的央行通胀目标模型消失,全球央行提出了三个解决方案:更加灵活的通胀目标;更加长期的通胀目标;或者干脆以GDP+价格为目标。我个人倾向于第三种方式。但无论是哪个目标,都无法应对今天央行政策空间缺失的难题。
科技巨头?收入不平等?气候变化?MMT? Libra?
正当全球央行痛苦地思考以何种框架取代通胀目标时,全球局面正在迅速发生新的演化。
——随着科技巨头崛起,全球市场结构变了,大公司的利润(Mark-up)和市场占有率持续上升、中小企业份额持续下降,市场新进入比例持续下行。
——收入分配持续恶化。20世纪初,发达经济体最富有的1%占据国民收入的20%,上世纪70-80年代降至8%,如今又回到20%。在美国,1980-2017年间,底层50%人群的国民收入份额从20%锐减至12.5%,顶层1%则从近10%上升到20%;同时,最富有1%的人群财富占比达到45%;而最富有0.1%人群的财富占比则从1979年的7%上升到今天的20%。
——随着加州公用事业公司PG&E Corp申请破产保护,气候变化对经济的冲击有了更加具象的共鸣。未来一方面灾害性气候事件和更长远的气候趋势对财产、土地和基础设施造成物理和经济损害;另一方面低碳经济调整过程中气候政策、技术和市场情绪的变化,会带来资产价格变化和更广泛的经济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富有远见的观点指出,目前“菲利普斯曲线”的消失可能是暂时的,而且这条曲线可能不再呈现为线性(Linear)——当全球贸易壁垒持续上升(意味着全球配置资源效率下降,价格趋于上升),全球“赢家通吃”市场结构成型(意味着垄断者有机会涨价),收入分配继续恶化导致社会动荡(意味着政府治理和公信力对通胀预期的正面影响不再),气候变化导致全方位的经济损失和市场波动,在未来的某一个时点,消失的通胀会强势回归,而且很可能是以“滞胀”的局面(顺便说起,今天中国面临的猪肉价格导致的短期价格上升不在此列)。
这样的灾难性局面并非不可能,推波助澜的还可能包括最近十分热火的MMT(现代货币理论)和让整个世界陷入辩论的libra(全球性数字货币)。MMT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行动的思考角度是对的,但具体建议很可能导致灾难性的结局;同样,Libra(全球货币)也代表了未来的方向,问题在于,全球货币背后的全球央行应该来自IMF、BIS和各国央行,而非Calibra。
总之,当这本蓝皮书付印之时,整个世界已经进入了二战以来以来最动荡而复杂的新时代,需要重新设计目标和模型的远不止于各国央行。(作者系《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第一财经研究院院长、2019第一财经CFV联席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