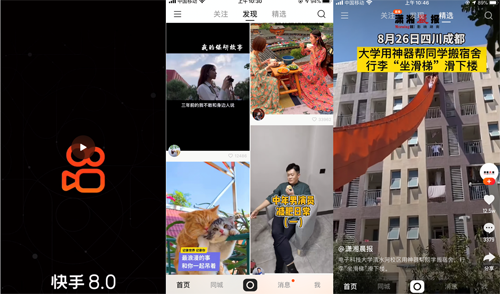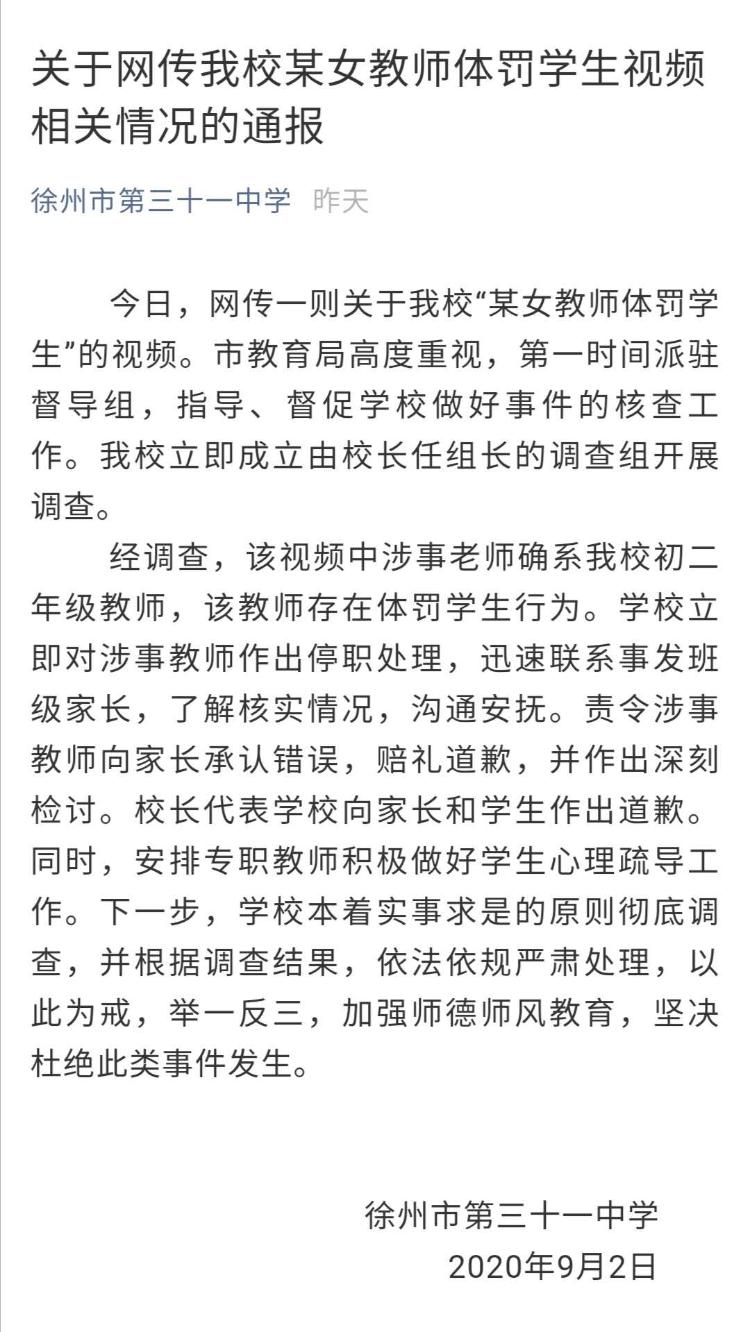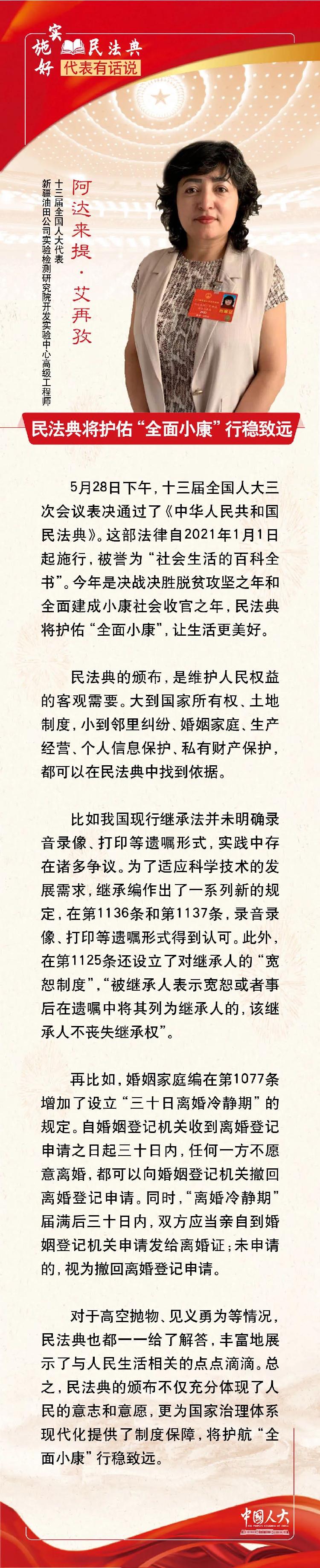在这世界上,有没有一心专为穷人“做主”的经济学?
10月14日,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结果出炉,由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组成的评委会此次选择了三位“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有)实验性做法”的获奖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福特基金会国际经济学教授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担任发展经济学教授的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其中前两位还是因学术结缘的夫妻。
诺贝尔经济学奖方面给出的官方获奖理由是,“人类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之一是减少各种形式的全球贫困。今年的获奖者进行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我们缩减全球贫困的能力。在短短的二十年中,他们基于实验的新方法改变了发展经济学,而这如今已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研究领域。”
具体而言,今年来自发展经济学领域的获奖者引入了一种新方法,获取了如何消除全球贫困的最佳方法的可靠答案:他们将问题划分为更小领域的、更易于管理的问题。例如,什么是用于改善教育成果或儿童健康的最有效干预措施?他们发现,通过在受影响最大的群体中进行精心设计的实验,是最好的研究方法。

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执行院长、金融学教授钱军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指出, 经济学在研究方法方面重视研究因果关系,困扰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即政策能不能导致某个结果,而前述获奖学者的贡献,恰恰是巧妙设计了实验/研究方法。
钱军亦谈到了他对此获奖研究方式的评估:在挑选实验目标时,有一定随机性,不是所有重大经济政策都可以通过随机实验的方式来验证效果,且发展经济学实验做的规模通常不会很大,因为设计大规模实验即费钱又很难精准;同时,在规模不大的实验下得出的结论,虽然很精准,并不一定能够在与实验地区有较大差异的区域大规模推演。
最年轻女性诺奖得主看中国发展
在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宣布之前,各方一直在猜测此次是否会有女性经济学家获奖,其原因在于,在诺贝尔经济学奖40周年即2009年时,出现了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而今年正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50周年。

不过,最终奖项揭晓时,出现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身后屏幕上的女性获奖者并非是大部分经济学人的“心头好”——美国经济学家安妮·克鲁格,而是出生于1972年、目前仅46岁的迪弗洛。
她成为了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是迄今为止第二位女性诺奖经济学奖得主。如前所述,巴纳吉是她的丈夫,也是她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论文导师。
历史上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都曾诞生过夫妻档,最有名的就是居里夫妇。对经济学奖来说,夫妻档还是第一回。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济学动态》编辑部副主任李仁贵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今年诺奖评选有个显著的变化是在获奖者的年龄下限上有所突破。迪弗洛还不到47岁,往届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约瑟夫·阿罗当时也有51岁(注:平均年龄为67岁),因此这是个比较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意味着学者从做出成就到获奖的时间缩短,这对年轻人是个鼓励。”
此外,李仁贵也表示,本届诺奖还出现了两个较小的变化。
他称:“一是从2013年到2018年连续六年诺奖得主都同时是引文桂冠奖入选者,而今年三位都不是;二是迪弗洛是克拉克奖(注:奖赏40岁以下的青年学者)的得主,从2009年到2018年十届诺奖得主都未获得过克拉克奖,今年是克拉克奖得主的回归。
钱军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目前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很多人都是巴纳吉和迪弗洛的学生。迪弗洛虽然年轻,却已经是经济学界三大重要刊物之一《美国经济评论》的主编之一。
在今年9月时钱军还见到了迪弗洛,彼时是在美国经济智库——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召开的中国经济论坛上,迪弗洛受邀作为主旨演讲者演讲。
在期间,她讲了以下几点:首先,在目前经济环境下,经济学家要如何重新获得民众信任,其次,在经济增长停滞后,政府可以做的事情。钱军回忆,彼时迪弗洛还谈到了她对于中国经济的一些看法,即她认为如果按照历史规律,未来中国应该在发展中让财富分配更加平均一些,让财富收入更加平等。
钱军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在他看来,以目前中国经济还在中高速发展的现状看,过分强调财富平均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的目标:看社会财富分配,不如看消费分配,而讲社会财富公平,不如讲社会发展最重要公平,那就是机会公平,譬如从幼儿园同等受教育机会公平。
减贫,他们是认真的
本届诺奖获得者最初的研究,也恰好是集中在教育领域。
他们探究哪些干预措施可以用最小的成本提升教育效果。在低收入国家,教科书稀缺,儿童也经常饿着肚子上学。那么,如果学生可以获取更多教科书,他们的成绩会提高吗?还是给他们发放免费校餐会是更有效的措施?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克雷默和他的同事决定在肯尼亚西部的农村地区进行田野实验以便回答这些问题。
在实验中,克雷默将大量需要深入帮助的学校随机分为不同的组,并给予它们额外的资源,只是形式和时间不同。
比如说,在一项研究中,一组学校拥有更多的教科书,而另一组则被给予了免费的学校餐食。实验表明,更多的教科书和免费的校餐都对学习效果没有任何影响。如果教科书因素有积极的作用,也只适用于最好的学生。
巴纳吉和迪弗洛则研究了印度两个城市的学生的补习辅导计划,其中孟买和瓦都达拉的一些学校获得了新的助教,可以为有特殊需要的儿童提供支持。实验清楚地表明,给最弱势的学生的针对性帮助,是中短期中最有效的方式。
简单来说,这些实验表明,许多低收入国家最主要问题不是缺乏资源,而是教学不足以适应学生的需求。在肯尼亚和印度进行的这些早期研究之后,实验也在其他国家陆续展开,但关注点转移到了诸如卫生、获得信贷的条件和新技术的使用等重要领域上。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他们的工作成果,田野实验已经成为发展经济学家们在调查减轻贫困措施的效果时的标准方法。
而今年诺奖得主的实验设计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是无论是干预组还是对照组的参与者都是在日常环境中做出实际决定,这意味着对新政策效果的测试结果可以直接应用。
第二,这些诺奖得主的研究背后有一条重要观察,即许多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是个体选择的结果,因此要做出巨大改进必须了解人们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三位诺奖得主不但测试了某种干预是否奏效,而且还测试了原因。
譬如在教育领域,各方现在得以对贫困国家的核心问题有清晰的认识,即课程和教学无法满足学生的需求。在这些国家中,教师和教育机构的缺失程度普遍较高。
巴纳吉和迪弗洛等人的上述研究表明,即使以中期来看,对弱势学生的有针对性的帮助也具有积极的作用。这项研究是相互影响与合作进程的开始,这些新的研究成果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大规模项目用以支持学生,现在这些计划已惠及超过10万所印度学校。
其他田野实验还调查了教师缺乏明确的激励机制和责任感,这反应在旷工率高的现实上。激发教师动力的一种方法是将他们雇用在短期合同中,如果他们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可以延长合同。迪弗洛和克雷默等人比较了不同聘用条件的老师的教学效果,结果发现以短期合同聘用老师的学生的考试成绩要好得多,但长期聘用的老师的学生却没有显著影响。
总体而言,这项新的基于实验的低收入国家教育研究表明,总体而言,额外资源的价值有限。但是,使教学适应学生需求的教育改革具有重大价值。改善学校的管理水平和要求尸位素餐的老师承担责任也是符合成本效益的措施。
在卫生领域,一直以来的重要问题是,是否应该对药物和医疗保健进行收费,如果是,应支付多少费用。克雷默和其同事的一项田野实验调查了价格如何影响人们对预防寄生虫感染的驱虫药的需求。他们发现,有75%的父母在药免费时给孩子服用了这些药,而在大量补贴下只需要他们花费不到1美元购买药物时,只有18%的父母买给了孩子。随后,许多类似的实验也发现了同样的事情:穷人对预防性保健的投资极为价格敏感。
此外,服务质量差是贫困家庭在预防措施上投入很少的另一个解释。一个例子是,卫生中心负责接种疫苗的工作人员经常缺勤。 班纳吉和杜芙若等调查了流动疫苗接种诊所是否可以解决此类问题。结果发现,在获取这一服务的村庄中,疫苗接种率为18%,是没有获取此服务的村庄的6%的三倍。而如果家庭给孩子接种时能被奖励一袋扁豆的话,这一比例增加至39%。由于流动诊所的固定成本较高,因此尽管赠送扁豆会增加费用,但每次疫苗接种的总成本实际上减少了一半。
钱军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目前这三位研究发展经济学研究学者的的重点是非洲和印度,不过要从消除贫困的实际经验来看,在人类历史来看,最成功消除贫困的国家就是中国:从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的不到2%(1978年),到2018年中国GDP占比约为16%。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让7亿多贫困人口成功脱贫,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总数的70%以上。
如此说并非贬低他们的经济学研究,钱军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但整个发展经济学圈对中国在扶贫和经济发展上的了解还是不够。更多的发展经济学中值得关注的还是中国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