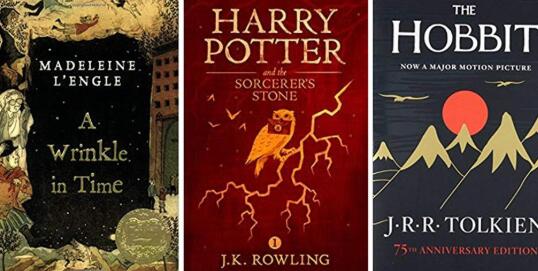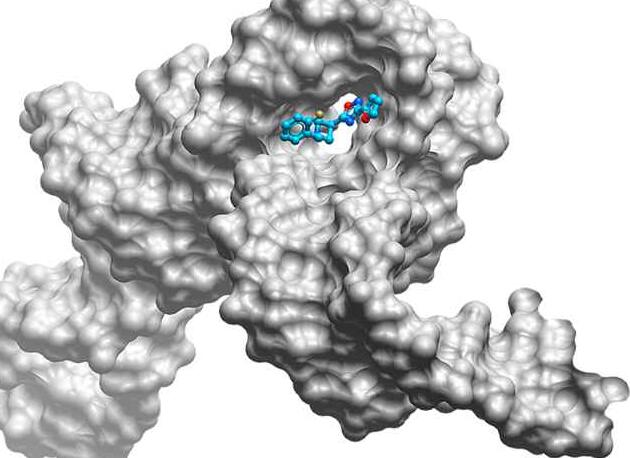“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帮助和关心,我回家了。”3月13日下午6时许,熊卓琴终于回到了位于东湖高新区的家中。为了照料身患新冠肺炎的父亲并进行自我隔离,38岁的熊卓琴在江汉区一家旧家具市场的民房内居住了超过45天。
熊卓琴的老家在武汉市黄陂区。作为家中较有出息的孩子,毕业后在武汉东湖高新区光谷自由城小区安家,并在国企谋得一份职位。
这次疫情当中,父子二人可谓历经坎坷。1月21日,武汉疫情爆发之际,熊卓琴一直陪伴父亲在医院排队就医,终获床位。父亲成功住院救治后,熊卓琴蜗居于一座破旧的旧家具市场内,在缺少防护和生活物资的情况下,开始了漫长的隔离生活,长达40余天。
从隔离点江汉区的旧家具市场到光谷自由城小区的家中,百度地图显示,如果驾车,两地相隔29.7公里,要经历14个红绿灯,共计37分钟。
3月10日,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滞留在汉外地人员服务保障组发布《关于做好市内交叉滞留人员安全回家工作的通知》文件称,市内交叉滞留人员是指有本市户籍、本市居住证、或有自有住房,在1月23日公共交通停运、道路通行管制后,因探亲、就医、务工等原因,跨行政区滞留的人员。
上述文件指,对市内交叉滞留人员,可向其所在社区、户籍(居住证、自有住房)所在社区同时提出回家申请,对非“四类人员”(确诊、隔离、发热病例及密切接触者)且无发热症状的申请人员,相关区防控指挥部均应审核同意。
随后,第一财经记者分别联系上熊卓琴滞留所在社区以及他位于光谷自由城的所在社区。两地社区相关负责人均表示,正在积极帮助熊卓琴回家,并严格落实相关手续和政策。3月12日,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熊卓琴终于踏上归途。
记者与熊卓琴聊了这段时间以来的求医过程以及隔离期间的生活状态。以下是熊卓琴的口述,记者整理行文。

终获一张临时床位
从陪父亲就医到最后获得床位救治,前后花了5天时间。
1月21日,我把父亲从黄陂老家接到武汉。当时是晚上才到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并在附近宾馆开好房休息。
那时候的发热门诊内,人满为患,医生、护士穿好了防护服,戴好了隔离帽等防护装备。从挂号、问诊、交费、取药以及输液等每个就诊流程都需要排队,有的流程队伍排到几百号,甚至上千号。
一大早我们就会过来排队,护士会在纸条写号码,每天等候就诊的时间比较长,十几个小时是家常便饭,父亲往往要等到凌晨才能输液。有时候晚上排到深夜,就基本不回宾馆了,在医院走道内就地而眠,因为第二天打针还要排队。主要是当时需就医的发热患者多,医院接收能力有限,护士要配很多药,医护力量不足。
当时,我们每一名病人及其家属,几乎都跟在疫情一线一样,暴露在可能被感染的环境下。我在医院工作的同学,及时送来了一些口罩。但仅靠一层口罩呆在医院,我确实有些担心。
1月24日,父亲咳嗽得越来越厉害,呼吸不畅,病情危重,他虚弱地坐着输液时,连头都抬不起来。父亲感觉自己快不行了,他说干脆就不治疗了。
我很生气地对他说,“在医院已经来三天了,排了这么久的队,你现在跟我说你不治了?你对得起我吗?”。其实我是在鼓励他,我当时咨询了做医生的同学,新冠肺炎可以治愈。我说,“你要对自己都没信心,那肯定就没辙,要是不坚持,就彻底没希望。”
父亲复查CT发现,肺部感染面积增大。我当时觉得情况比较危急,就去找医生能不能开住院单。医生说可以开,但是不能保证有病床。我到住院部实地查看,那边确实没有空余的病床。没办法,只能等。
急诊科一位吕姓医生看父亲病重说,“可以安排吸氧,但吸氧的地方环境条件比较差,问我能不能接受?”当然接受,随后父亲进行吸氧治疗。
接着,一位主治的刘医生对我说,这种紧急情况下,她建议我去找院领导,看他能不能帮忙想办法尽快找到床位。当务之急,能救命最好。
26日晚上10时许,吕医生突然打来电话,说附近新华医院有临时病床,那边在腾退,可以安排父亲过去,“条件是比较艰苦,但是有病床。”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我喜极而泣。本来是不抱希望的,很无奈,只能硬撑着,现在先有床位住着,不用现在这么奔波、劳累。
当晚,我们来到武汉红十字会医院。由于需要转院的病人较多,直到凌晨两点钟,父亲才被120救护车转运到新华医院。
当晚父亲终于在新华医院病床上得到安顿。随后,不停转送病人的吕医生,还专门赶到父亲的病床前关心询问,“你们的手续都办好了没有?能不能安心住?”这让我十分感动,心里终于踏实,紧绷地神经稍微松懈。
我算是是家里的顶梁柱,很少遇到什么困难自己不能坚持的情况。那时候每天早上起床,我都要大哭一场,哭完洗把脸出门,再到医院去排队,毕竟痛苦归痛苦,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这种状态持续了几天。我觉得要是自己表现出一丝一毫坚持不下去的状态,可能给父亲就是一个直接毁灭性的信号,我只能硬撑着。
1月28日,为了确保自己健康,我去医院门诊部做了CT,结果显示正常。听新闻里面的专家介绍,病毒有“人传人”的风险,出于安全的考虑,我觉得不能马上回去。而疫情可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长期在酒店待着不是长久之计,且父亲尚在住院,我也不能走远。
于是,我来到医院附近的旧家具市场内,给门口招牌上显示的商户老板打电话,求人家好心收留。对方找人过来把一个破旧房间打开供我居住。至此,我在这里做隔离。
这里是一个待拆迁的地方,属于居民区与市场的交叉地带。市场内太脏了,卫生基本无人打理,缺少消毒措施,一次性口罩等垃圾、污物满地。
长时间待在房内,每天24小时我都不敢开门,时刻戴着口罩,连睡觉也不敢摘。我的口罩消耗量很大,现在仅存的一点口罩都是之前外地朋友寄来的。
隔离生活可想而知。之前我在超市买了泡面、挂面和一袋5公斤的大米等生活物资。我还买了一个电饭煲,不管什么食物和调料,都往里面丢。煮的食物吃多了,有时候作呕,想吐,没有任何口味。
这段时间,我吃面条比较多。小区封闭式管理后,买菜较困难。我之前参与过社区团购,但菜的分量较大,比如团购肉一般在10斤左右。我没有冰箱,没地方储藏,一餐也吃不完。后来也没再参加团购。
前几天,大米吃完了,我在京东上下单买了一袋。好心的京东快递员,从封闭的卡口处给我递来了大米。隔离生活持续直到现在。
我以前身体比较胖,快150斤,现在感觉瘦了很多,明显的感觉是“裤腰大了”。以前的裤子都是紧绷。现在不系皮带,裤子会往下掉。
我住的房间比较阴暗,只有早上有零星的阳光从窗户缝隙射进来,在那里站一会儿。40多天见不到阳光,现在看到阳光都有点刺眼。这里没有热水器,洗澡也很不方便,半个月没有洗澡了。
这段时间,我们公司已经逐步恢复工作。在房间内,我每天还要处理工作。我是搞通信的,之前负责的小组还参加了武汉市洪山区、江夏区的疫情防控指挥部5G视频会议系统建设。
疫情期间,我通过手机与同事时刻保持联系。虽说本人没有亲自过去,但是有很多沟通、指导等协调工作,都是在隔离的房间内完成的。
内心既恐惧又自责
从1月21日至今,我已经52天没有回家。
这期间,妻子很希望我回去,她比较胆小,而且我家那一栋,住户基本回老家过春节了,同一楼层长期没人。家里就他们娘儿俩,外加疫情和孤独感,造成妻子的心理压力过大、焦虑。
我其实内心比较愧疚的是对老婆和孩子。疫情发生的几十天来,没有给他们提供一丝一毫的帮助。不管是买菜、还是指导孩子上网课等,没有给他们做任何支撑。
老婆有时候也在电话里抱怨,我都能理解。作为一个男人在外隔离都觉得难,她也曾跟我抱怨,但一直都在坚持。老婆之前对我发过脾气,我也对她发过脾气,我觉得我也需要人理解。
2月10日,听说市区医院有核酸检测试剂,我赶到新华医院做检测,结果显示是阴性,我感觉很踏实,对自己很有信心,还准备做完第二次核酸检测再骑自行车回去。
但万万没想到,刚好那时候,武汉加大封控力度,社区做了封闭式管理,回去的希望也彻底破灭。我还每天坚持看新闻,专家对病毒的认识越来越清晰,病毒的潜伏期有14天。但有新闻报道出来说,有特例病人的潜伏期达24天。
我就一直扪心自问,不断自我怀疑,自己会不会是不是这个特例?因为我处在这场疫情当中。如果说一直呆在家里,从未出门,没去过医院,自然不会有这样的怀疑。但我去过这些相关场所,对自己要有严苛的要求,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要保证自己100%身体健康,后来做了决定,既然回不去,就安心在这里继续隔离,继续隔离24天,因此一直到现在。
我在医院虽然呆了很多天,很庆幸没有被感染。最幸运的一点是,当我们需要看病的时候,还能去医院。虽说很艰难,但当我们需要病床的时候,通过各方的努力,也有获得救治的病床,最后顺利出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