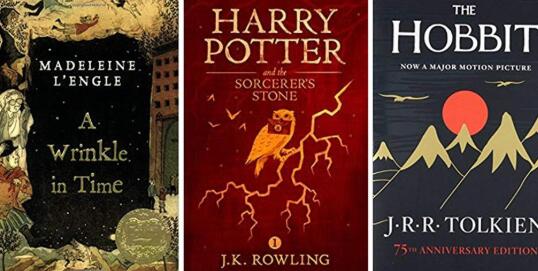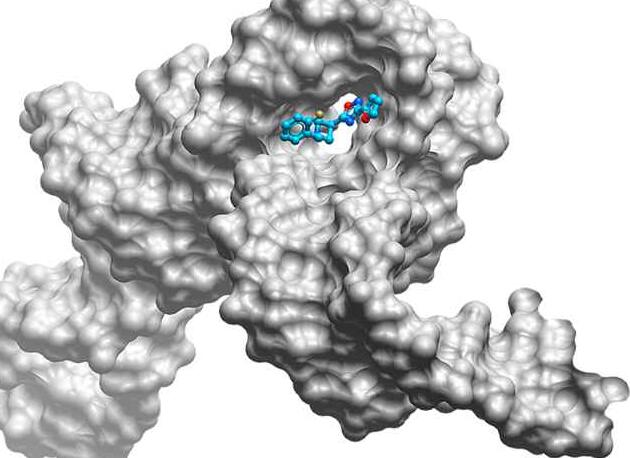何霞(化名)说,自己的不幸,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感染了新冠病毒,且在医疗条件很不完善的斯里兰卡病发,而不幸中的万幸,是自己的病情非常轻微,而且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们在帮助自己。
“否则,我可能就回不来了。”说到这,何霞的声音哽咽了。
何霞是湖北鄂州人,在去武汉参加年会后,她登上了前往斯里兰卡的飞机,开始了一段美好的旅行,而就会回国的前一天,她开始不舒服,在去往机场的大巴上,导游的体温计测出她在发烧,并被斯里兰卡当地的救护车直接送到了医院。
之后,当地媒体报道,她是斯里兰卡首例新冠病毒患者。
异国他乡、言语不通、无亲无故、陌生的人际,何霞就这样开始了在异国的治疗之路。
回国前发烧了
何霞说,每一年的春节期间,她都会选择通过旅行的方式度过,今年也不例外,她早早制定了去斯里兰卡的旅行计划。
斯里兰卡是位于印度洋的热带岛国,人口2144万,相当于两个武汉常住人口的规模。经济以农业为主,最重要的出口产品为锡兰红茶,就在2月6日,斯里兰卡总统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还在总统府约见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程学源,代表斯里兰卡政府和人民向中国捐赠首批锡兰红茶,以表达对中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慰问。
在去往斯里兰卡之前,何霞于1月17日先去武汉开年会,和同事聚餐,直到18日中午退房,离开武汉,飞往成都,再从成都飞往斯里兰卡。
“中间停留了大概一天的时间。”何霞事后一直在琢磨,自己在武汉的一天时间里,究竟有哪些场合可能被传染。
事实上,即便是在海外旅行,国内与日俱增的疫情也在灼烧着每一位游客的心。
何霞说,她所在的旅游团都来自湖北,他们在国内的家人都暴露在可能被病毒感染的危险之中。原定,1月25日晚,旅游团就会踏上回国的航班,24日,导游已经开始要求游客在宾馆原地隔离。
“就在25日早上,我开始觉得冷,眼睛痛,当时还以为是空调太低了,我睡了一觉,醒来后,感觉好多了,中午,大家集合去机场,我们导游还沿途组织大家买口罩,准备带回国内,也买了体温计给大家量体温。”何霞说。
这也是何霞此次旅行以来第一次量体温,她发现,自己发烧了。
“我当时没想太多,觉得可能是感冒了,但我还是第一时间告诉了导游。”何霞说。
导游听到有游客发烧的消息后,有些紧张,立即联系所在公司和当地大使馆。大使馆建议何霞立即入院检查,并联系了当地的医疗机构。
在异国他乡入院
事实上,斯里兰卡的医疗水平十分有限,在这里,只有一家拥有隔离病房的医院——科伦坡疾控中心医院,就这样,何霞住进了科伦坡医院。

(斯里兰卡科伦坡疾控中心医院病房)
这一天,正是星期六,入院以后,何霞并没有第一时间见到医生,医院只给她送来退烧药。
同前一天一样,1月26日,何霞依然没有见到医生,不过医院对她做了鼻腔和唾液的采样,进行第一次核酸检测。护士按时给她送来三顿饭和三次口服药物,一切都是最常规的治疗方法,只是她的发烧和腹泻没有得到任何缓解。

(口服药物)
直到1月27日,何霞入院的第三天,她终于看到了自己的主治医生,但一大问题摆在面前,双方语言不通,何霞英语有限,而医生的英语发音也并不标准,这使得何霞更难以听懂。没有CT,没有拍胸片,主治医生只是用听诊器判断她的肺部是否有问题。
与国内的医院相比,科伦坡医院虽没有人山人海,但条件十分有限,何霞每天经历着十余次的腹泻和反复的发烧,“每天只有简单的药物治疗,我越来越慌了。”何霞说。
1月28日晚上,何霞的唾液采样检测结果出现了,她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得知这个消息,何霞失眠了,她看着四周的医疗设施,想着导游、同事们,以及旅游团的其他人会不会被传染,她觉得恐惧。
1月29日早上,护士的态度也转变了,“她把我的早饭放在门口就迅速离开了,看得出,她很紧张。自我确诊之后,明显感受到医护人员的情绪变化,我都能理解,换作是我,也会是这样的反应。”何霞说。

(科伦坡医院的医护人员)
然而,让何霞最为不解的是,确诊以后,她的治疗方案并没有改变,依旧是原来的退烧药,同时,也没有更先进的医疗设备介入,依然是主治医生每天的听诊器。而此时的国内,一直在讨论着何种药物有效,治疗方案接连推向疫情前线。
确诊后的治疗
“我开始打电话给我一切能找到的人,希望能把我转送回国治疗,给导游,给我之前投保的保险公司,幸好我还是这家保险公司的VIP客户。”何霞说。
导游和保险公司又先后给大使馆打电话,保险公司甚至提出包机送何霞回国,大使馆也开始与地方沟通,但最后还是被斯里兰卡拒绝了,因为她属于乙类传染病,只能留在当地治疗。
此时,保险公司开始发挥主导作用,他们专门为何霞建立了“斯里兰卡紧急援助小组”,带给她所需要的各种日用品和中式餐食,并为何霞介绍了一位北京协和医院的教授及另外一家医院的呼吸科教授进行远程协助。
尽管与两位教授相隔万水千山,也不能直接用药或治疗,但却给何霞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安慰和鼓励,让她有信心战胜自己的病情。
两位教授也一致判断,何霞是轻度感染,痊愈几率很高。“我紧绷的一根弦终于松了。”何霞说。
1月30日,何霞开始退烧,斯里兰卡的主治医生给何霞做了第二次核酸检测,其中,鼻腔检测呈阴性,口腔检测呈阳性,医生告诉何霞,她已经开始好转了。
在等待康复的日子里,何霞先后做了三次核酸检测,每两天一次,直到2月4日的第六次检测结果显示全部为阴性,但是仍要继续隔离观察。
2月6日,何霞又做了一次检查,这是第七次检测,这次会将取样一式两份,一份留在当地,一份送往新加坡的检验室,如果两地的检测结果一致且均为阴性,何霞距离出院就更近了一步。
“我能感受到,我的身体在慢慢的恢复,病毒也在慢慢的退去,现在还有点咳嗽,但协和医院的教授说,这是痊愈前的一个过程,让我多喝水,斯里兰卡的医生说,我要彻彻底底康复之后,才能免除隔离。”何霞说。
尽管在生病期间,何霞被严严实实的隔离了起来,但她依旧遇到了很多的热心人在帮助她。
“比如我的医院护士长,她每天都来看我,还在超市给我买了衣物用品;当地旅行社的导游帮我四处奔走,大使馆帮我联系了医院,让我觉得祖国后盾的温暖;我投保的保险公司工作人员,每天都在询问我的病情,给我加油打气;两位中国教授几乎24小时在线,帮我讲解病情;我的斯里兰卡主治医生,尽管我们语言不通,医疗条件有限,但他也在尽心尽力的医治我。”何霞说。
何霞的主治医生,同时也是当地的医学专家,与远在北京的协和医院教授就何霞的病情及新型冠状肺炎的治疗方法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我每天都在关注国内的疫情报道,最近才得知与我一道开会的两位同事也被感染了,我的家人目前很好,我每天都要给他们打两次电话,但不敢让我80多岁的老父母知道,我怕他们承受不住。”说到这,何霞的声音又开始哽咽了。
如今的何霞,依旧在和病毒战斗,直到痊愈的那一天,重新徜徉在阳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