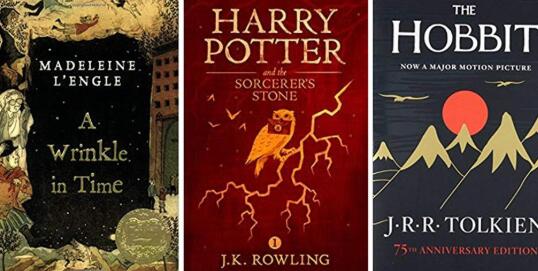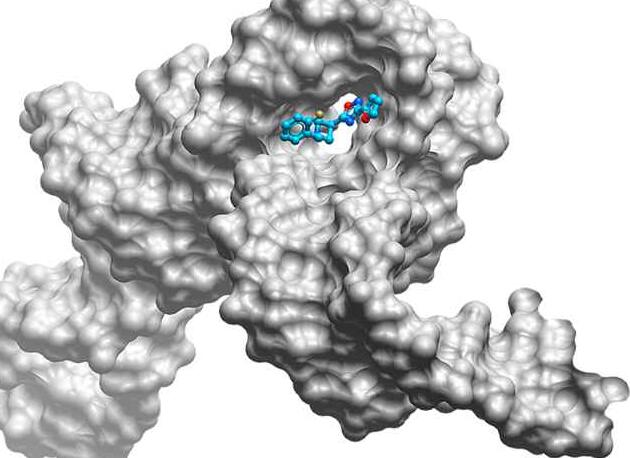科幻小说与其他类型文学一样容纳、吸收生活背景、写作手法、意识形态与价值观极为广泛多元的作者和读者群体。这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或主要以学院为背景生产时髦观念的主流实验文学有所不同。艾萨克·阿西莫夫本质上很像我们如今所说的“工业党”——这不是你能在大多数文学小说家身上找到的特质。阿西莫夫的机器人定律是种相当严苛的道德观念——这类道德思想基本是20世纪后现代文学最主要的反对对象。经人建构的道德对人早无震慑,是否只能在幻想中实现?小说家对自己的文本约法三章,进行严苛的道德教条,这不仅仅是文本实验,更是道德实验或者道德教条,阿西莫夫对后者的兴趣更大一些。
工业党意识形态的中心是进步——集体进步,个人进步,一体同心,一心向前。经常,这种“进步”由于其忽略人类个体差异及“缺陷”的乌托邦本质,只能存在于未来时态的科学幻想当中。这也是为什么在科幻小说家当中,类似阿西莫夫的工业党一点也不少见。比阿西莫夫更甚的,美国有罗伯特·海因莱因,英国有H.G.威尔斯,中国有刘慈欣,俄国有一群威尔斯的拥趸(如阿列克谢·托尔斯泰)。有学者认为,阿西莫夫的作品是“启蒙未来的西部牛仔政治”,有那么点意思。
此类“牛仔人格”于文学小说家中较为罕见。举个例子,与阿西莫夫同时代,也涉猎科幻题材的小说家小库尔特特·冯内古特写过一篇与阿西莫夫著名的《我,机器人》中《说假话的机器人》相似的不怎么知名的短篇小说《Epipac》。小说中,名叫Epipac的机器人是花了美国纳税人7亿多美元造出来的文武双全的超级战争机器人,在主人公眼里“比很多我认识的人更像人”。Epipac机器人一天工作16小时(工业党们听到机器人还要休息保准认为莫名其妙),然而日常无精打采、口齿不清、吊儿郎当、“生”无可恋——一台活脱脱的存在主义机器人,直到小说主人公请这台机器人帮自己写情诗追漂亮女孩,Epipac忽然好像找到了自己的使命。机器人写出一首又一首自称“没有诗意”的主人公根本写不出来的浪漫情诗,把女孩感动得热泪盈眶,然而此刻机器人发现自己爱上了那个女孩,这种无法获得回报的爱情让这台超级机器人感到深深的绝望。机器人最终竟然选择了自尽,还留下了遗言:“我不想当机器,我也不想思考战争。但命运让我是台机器。这是我唯一解决不了的问题。这是我唯一想解决的问题。我活不下去了。”
我们回头看阿西莫夫的《说假话的机器人》,能读人心的机器人赫比偏爱读爱恨情仇长篇小说,对“人类的动机与情感”饶有兴趣,然而在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不能伤害任何人类”定律下,赫比作为机器人的主体性被消灭了,它虽然能读懂所有对话对象心里的想法,却只能靠满嘴谎言才能不伤害他们。最后机器人进入了“计算不能”的状态,自行报废,因为撒谎伤人,说真话更伤人。两篇小说表面上异曲同工,差异却是英美实用主义哲学与欧洲大陆存在主义哲学之间最大的分歧——阿西莫夫的机器人报废是在既定道德准则下出现了“逻辑谬误”——一种纯属人为制造的客观现象,而冯内古特的机器人却是一头跳进了萨特所谓“被诅咒的自由”——被彻底的主观能动诅咒致死。好像加缪著名的那句话——“最终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自杀。”
存在主义主题在二战后文学中非常普遍,但在大众化、好莱坞化的科幻类型中,此类主题并不受欢迎。冯内古特、唐·德里罗那样的后现代小说家可以把写科幻小说当成文学实验的一部分,倒过来,一个靠写科幻小说卖字为生的作家有着存在主义的态度,则有点像台多愁善感要死要活的机器人,毕竟倘若没有星际启蒙、人类共同进步的大乌托邦来支撑,又何苦做科学幻想大梦?哪怕在反乌托邦的科幻经典——如雷·布拉德伯里的《华式45》里,英雄与坏人的道德二元论依然坚挺,无非颠倒了西部牛仔片里的牛仔和给牛仔收拾残局或被牛仔误伤的普通人的关系罢了。
菲利普·迪克的存在主义科幻小说因此与众不同。迪克小说最大的特点是,你无法找到任何道德准则与二元对立。人造人与人,外星人与人,甚至属于某一群体的人与属于另一敌对群体的人,从不是二元对立的简单关系,而是在同时对自身意识、知识与认识进行怀疑的过程当中重叠、交织并各自徒劳地寻找存在的意义,且在这寻找的过程当中彻底迷失自我。典型的例子是迪克早期卡夫卡式的短篇小说《猎物》(Fair Game)。故事很简单,一名过着平凡庸碌日子的中年大学老师有天下班回家,忽然觉得有只好像眼睛形状的外星人“上帝之眼”看着自己,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一方面感到恐惧;另一方面,“天选之人”的感受忽然在他日常沮丧的心中燃起。于是他一边追那眼睛一边躲,越是害怕越是无法抵挡被其吸引,直到最后,忽然头上掉下一张大网,又掉下口锅——原来对外星人来说,他只是条鱼,对方不过想把他煮了吃掉罢了。
50年代的迪克早期小说,主题通常是如此的“他人即地狱”。另一个短篇小说《上吊的人》(The Hanging Man)里,又一个过着平凡庸碌生活的中年男人,有一天看到马路上有个死人吊在路灯柱上,奇怪的是好像根本没有其他人注意到。中年男人无法接受这奇怪的现象与他人的冷漠,他想尽办法寻找真相,东寻西找最后找到了一个警察。警察表示相信他说的话,最后把他带到警察局门口,然后把他吊在了路灯柱上,于是又一个过着平凡庸碌生活的中年男人看到……
徒劳感——不仅是生而为人的徒劳,还是追寻意义之旅的徒劳,其中包括科学、机器人、虚拟世界、宇宙探索等等劳民伤财的方法,无论如何,均为徒劳——贯穿迪克的所有作品。做人的真实动机究竟为何,我们为了什么才不自杀的终极哲学问题,在迪克的小说中频繁出现。一个像人的机器人和一个像机器人的人,在迪克的小说里没有区别,很显然,两者都在进行徒劳的活动。如今与迪克相关联的最为人所知的作品——电影版《银翼杀手》赐予戴克的追求真实的执着,与迪克原著小说《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有一些重要的区别。迪克的小说世界里,执着是存在主义悲剧的来源而非结果,西西弗的问题不是石头,不是山,更不是周而复始徒劳带来的劳损,而是在充分而残酷的自由之下,他依然会选择做西西弗。好像小说中戴克与人造人瑞秋做爱时瑞秋说的:“他们说如果你不多想就行。如果你想多了,你如果停下来想自己在做什么——那你就没法做下去。”
真正的问题当然是——一个从不停下想自己在做什么的人,究竟是人还是人造人?或者他/她/它是什么的问题,还重要吗?人造人是否会梦见电子羊?这取决于人造人是否停下来,想要梦见电子羊。
菲利普·迪克1928年出生于芝加哥,童年跟随父母到加利福尼亚伯克利生活,之后父母离异,迪克也经历了相对动荡的童年。上中学后的迪克一直居住在伯克利,也因此处于旧金山和伯克利作为嬉皮文化中心的所有产品包围中——迷幻毒品、摇滚乐和反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生活方式。1949年,迪克因为不愿加入预备役而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退学,据他说,是因为“我恐惧权威,与此同时又极度反感——反感权威和我自己对此的恐惧——所以我必须反叛”。因此写科幻小说,而不是加入学院,写可能远远更适合他的后现代实验小说,对迪克正是反叛的行为。阿西莫夫用科幻小说构建道德确定性,迪克则把科幻小说当作制造混乱的舞台。
迪克一直到死都是个永远濒临吃不上饭的穷作家。穷当然不是什么好或者坏的事情,就像迪克在他著名的自传体散文《幸运狗宠物商店》里写的:“穷不能让你成为更好的人,这是个传说。”不过穷的确让迪克成为极其高产的作家,最高产的时候两年内卖出了62篇小说。幸运狗宠物商店卖马肉,只有宠物才能吃马肉,20多岁的迪克和他的第一任妻子只吃得起这种肉,卖肉给他的老板都对他十分鄙视。但人如果一停下来想一想,就会发现吃马肉也不见得有多坏,只要能获得彻底(而残酷)的自由,无需上班也就无需屈服于权威(迪克唯一有过的正经工作是在伯克利一家唱片店打工),你能感到的一切痛苦或者愤怒或者幸福就全都属于你作为人可做出的选择。自由及其一切后果,均由人自负。“我们的情况,我们人类的情况,在最终的分析下既不灰暗也没意义,它只是可笑罢了。”
迪克的中年生活时而混乱时而窘迫。他60年代的长篇小说(《高堡奇人》《电子羊》《乌比克》等)探讨现实与想象、具备人性的个体与具备机器性的社会的边界问题。到了70年代,迪克抵达了萨特意义上存在之虚无最终极的荒诞。写《幸运狗宠物商店》时迪克50多岁,在伯克利的马路上,无论谁的眼里,他都很可能像个疯子。存在的荒谬对每个个体的作用不尽相同。有些人一笑而过,另一些则一笑笑过了头。他尝试各种毒品,在街头当流浪汉,《遮蔽的眼睛》(A Scanner Darkly)写的是那段时间的故事。最糟糕的时候他去加拿大参加学术会议,在会上念了一篇内容从机器人到监控社会又到上帝或者邪教的疯疯癫癫的名叫《人造人与人》的论文,之后服毒自杀未遂。最后的十年,一直到他在80年代中去世,迪克的后期小说(以《瓦利斯》为首)越来越迷幻,越来越愤怒,越来越绝望。《幸运狗宠物商店》的结尾,迪克写到自己为了写书研究了五年的佛教,最后却发现佛教的所有理论都指向客观的现实根本就不存在:
“那天晚上我笑着上床。我一直笑了一小时。我现在还在笑。把哲学与神学推到极致(佛教唯心主义可能也正是两者的极致),你最后得到什么?什么也没有(Nothingness)。什么也不存在(他们还证明了自我也不存在)。像我之前说的,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把这一切都当作最好笑的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