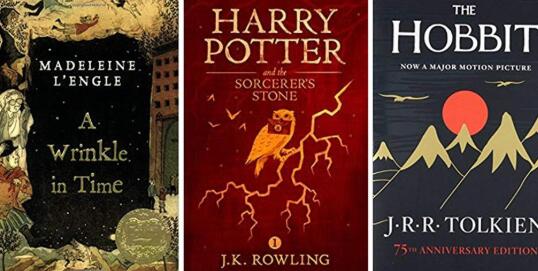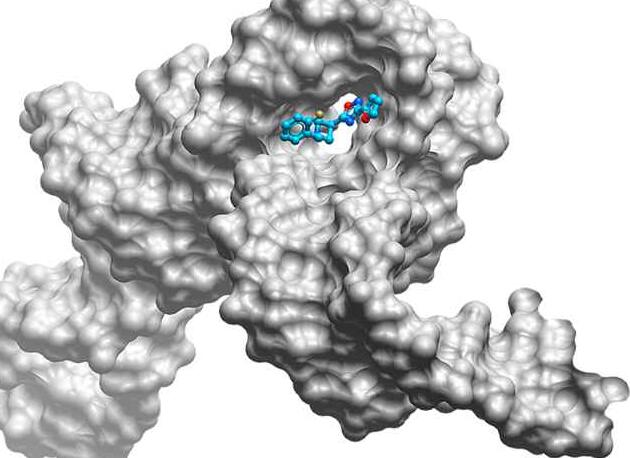已经有好几个朋友在新年到来之际跟我说,2020,看上去是一个蛮科幻的年份。的确。不过大概人类每隔20年都会预设一个自我感受比较科幻的年份,以YY一下各种或美好或阴暗的欲念。比如往前推20年的2000年,便曾经是一个非常标志性的科幻年份,再往前推20年的80年代也是(想想《1984》)。
在科幻三宗师之一的艾萨克·阿西莫夫百年诞辰之际,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儒勒·凡尔纳创立这一文学类型近200年以后,科幻在今天的“生存处境”。
科幻还是奇幻
记得世纪之交的时候,媒体曾蜂拥采访叶永烈。我们这些看着《小灵通漫游未来》长大的人,很想知道他怎么评价自己的“科幻”与真实的2000年之间的异同。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叶永烈的得意,他忙于历数小说中已经实现的“幻想”,只对自己没能预测到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感到遗憾。事实却是,很多当年小说里最吸引我们的东西,至今都没出现,或至少没能推广,比如智能机器人、气垫车,还有比人还大的西瓜。
脍炙人口的科幻没能实现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没有出现比人大的西瓜,是因为我们实际上并不需要那样的西瓜。那只不过是某个特定历史时期,饥饿(或者广义地说,物资匮乏)综合征在想象层面上的反映。而智能机器人,则是因为人工智能的研究上出现了难以预料的瓶颈,直到最近才在算法上有所突破,但也还是离比如菲利普·迪克想象的那种几可乱真、引起了严重伦理问题的“仿生人”非常遥远。
自从大数据成为常用词,对未来的预测在2010年代又重新热闹起来,这很好理解,掌握了更多数据和更强大的分析手段的人,总认为自己更能“看见”未来世界的模样。未来学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爆红了一段时间后,曾一度有些沉寂,人们似乎不像当初那么相信托夫勒、奈斯比特那些人了,尽管他们的确也预测对了很多东西,但预测错的好像更多。直到《人类简史》《未来简史》这样的书突然成为爆款,未来学似乎又复活了——这些书虽然冠以“历史”的名头,在我看来本质上却更接近当年的托夫勒、奈斯比特,不妨称之为“大数据时代的新未来学”。
大数据给预测业注入了新的自信,对科幻,却并非好事。维特根斯坦说过:
“整个现代的世界观都建立在一种幻觉的基础上,即认为所谓的自然律是自然现象的解释……所以,当代人们站在自然律面前,就像古代人们站在神和命运面前一样,自我感受上把它视为某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事实上他们两者都是正确的,也都是错误的:虽然古代人们的观点更为清楚一些,因为他们承认有一个明白的界限,而现代的系统则力求显得似乎一切东西都已经得到解释。”
英语世界两大奖星云奖和雨果奖,似乎有越来越不分科幻与奇幻的趋势。而自从超级英雄和机甲战士大行其道,“科幻”一词的定义对普通读者/观众来说更形模糊。事实上,21世纪恐怕是一个对奇幻愈加渴望,而对科幻尤其是硬科幻渐趋冷感的时代。一方面,大数据呈现出一种维特根斯坦所说“自然律”式的“硬指标”,并且通过自我反馈机制,越来越为我们构筑起一个貌似更加“确定”的未来,科幻的容身之所因此受到挤压;另一方面,这样强迫症似的确定性压力,在追求刺激的人性深层,却反而激起了对于更加天马行空无所羁绊的想象的需求,这使得奇幻、穿越大行其道,相比之下严谨得多的硬科幻,对大多数人就显得未免乏味。

与阿西莫夫齐名的科幻宗师阿瑟·克拉克有句名言:“任何足够先进的科技都与魔法无异。”注意,他说的是“足够先进”,也就是说,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实用科技,而是远远超出当下实用性的先进科技,这样,它就(至少暂时地)突破了现实逻辑,一只脚踏进了通常被认为不合逻辑的“魔法”世界。科幻,不就是要描绘这样一些处于魔法世界临界点上的“足够先进的科技”吗?那么科幻,最好就是既有部分现实的色彩,又有部分魔法的色彩,当它们能够被成功地捏合在一起,这就是一部好的科幻。
然而今天说起“魔法”,人们大概只会想到“奇幻”。的确,《哈利·波特》描写的不是魔法世界是什么?可罗琳阿姨之所以大行其道,比此前所有奇幻作家都受欢迎,恰恰因为她很大程度上以实用逻辑来规范魔法,让大多数人喜闻乐见。实用主义世界观正是以罗琳为媒介,大举入侵魔法世界,将其改造为一个和漫威星空本质上一体化的中产阶级道德宇宙。
光明还是黑暗
如今在真正死忠的硬科幻迷中,最响当当的名字,大多属于“黑暗派”,或者有个更“学术”的称呼——“赛博朋克”。其中的佼佼者,无疑是菲利普·迪克和威廉·吉布森。
阿西莫夫、克拉克、赫伯特和海因莱茵那代人的想象,宏大而富有历史感和宗教感。克拉克的《太空漫游》系列,在远古人类与星际旅行之间建立了神秘的呼应;阿西莫夫《基地》里的银河帝国,多多少少将犹太人在20世纪经历的苦难投射到未来的全人类;赫伯特的“沙丘世界”重构了一部极其复杂的未来版宗教《启示录》;海因莱因笔下的星际文明史,则与美国的历史各种异曲同工。

你可以说,他们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悲观主义者,因为在他们看来,基于“人性”,不论在空间上扩展至银河系,还是在时间上跨越至千万年以后,人还是会做出差不多的选择、进行类似的斗争、经历一轮又一轮的苦难。比如银河帝国无非是宇宙版的罗马帝国,其臣民同样要匍匐在元首、王子、总督、大臣的统治之下;沙丘世界的人们依然在有神论、无神论、万物有灵论等等之间徘徊与挣扎;《异乡异客》中来自火星的救世主,崇信革命与暴力,与天斗与地斗与一切牛鬼蛇神斗……
在他们的“幻想”中,未来很大程度上只是扩大升级版的历史与现实,光明与黑暗始终就像今天一样交战不息。而对赛博朋克来说,就几乎只剩下黑暗和绝望,一切都在高科技化的同时无尽衰败下去——想想《银翼杀手》那个科技感与荒原感难分难解交织在一起的世界。
当然,今日的科幻也有“光明派”,比如多次获大奖的罗伯特·索耶。对于人类能够找到与外星人适合的交流方式,能够进入别人的记忆甚至当下思维从而大大增进相互理解、从此抛却所有因互相隔绝的意识而造成的冲突、斗争、伤害,甚至能够因上传意识而达到某种意义上的“永生”,索耶都表现得极为乐观。接受采访时,他说:“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并不舒适,所以我探索其他可能性,包括更透明、更具日常责任,这样的社会比我们现在的更好。”
但在赛博朋克的拥趸看来,迪克和吉布森悲观的“高科技荒原”无疑更深刻。正如数字化时代“教父”尼葛洛庞帝在他25年前那本《数字化生存》中详尽描绘了比特和互联网将会带来的各种变革,却唯独忽视了一件事情——所有这些看似去中心化的技术一旦彻底被专制权力掌控,会发生什么。当卫星图像的分辨率达到厘米级,当监控摄像头的分布深入到穷乡僻壤的每一个角落,当最普通的家庭电器(比如冰箱电视机)和最简单的APP应用都可以打着大数据服务的名义肆意搜罗、分析人类一切日常活动最细致详尽的信息,当“斩首”的美军导弹在伊拉克上空呼啸而“定点清除”的无人机群反过来黑压压地扑向《天使陷落》中的美国总统……赛博朋克们所忧心忡忡的技术的法西斯化,似乎已不限于一个阴暗的想象。
不过赛博朋克也并不一味陷于暗黑破坏神的世界难以自拔。吉布森与索耶面谈时——是的,分别代表悲观和乐观两大流派的两个加拿大人,曾当面交流过这个问题——说:“只有与大多数西方人目前享有的极端特权相比——充足的食物、大量的休闲时间、足够的任何东西——我描绘的世界才可以被称为悲观。”吉布森显然还是希望通过对衰败景象的描绘,来激发出一些斗志,正如从《终结者》到《黑客帝国》,那个叫作“反抗军”的存在都不可或缺,哪怕那只是西西弗式的没有胜利可言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