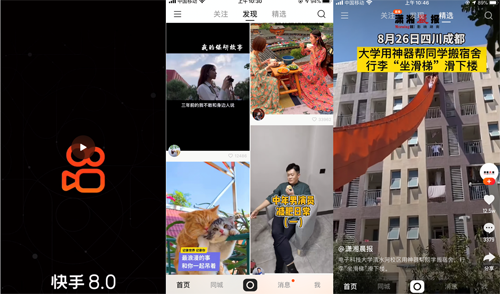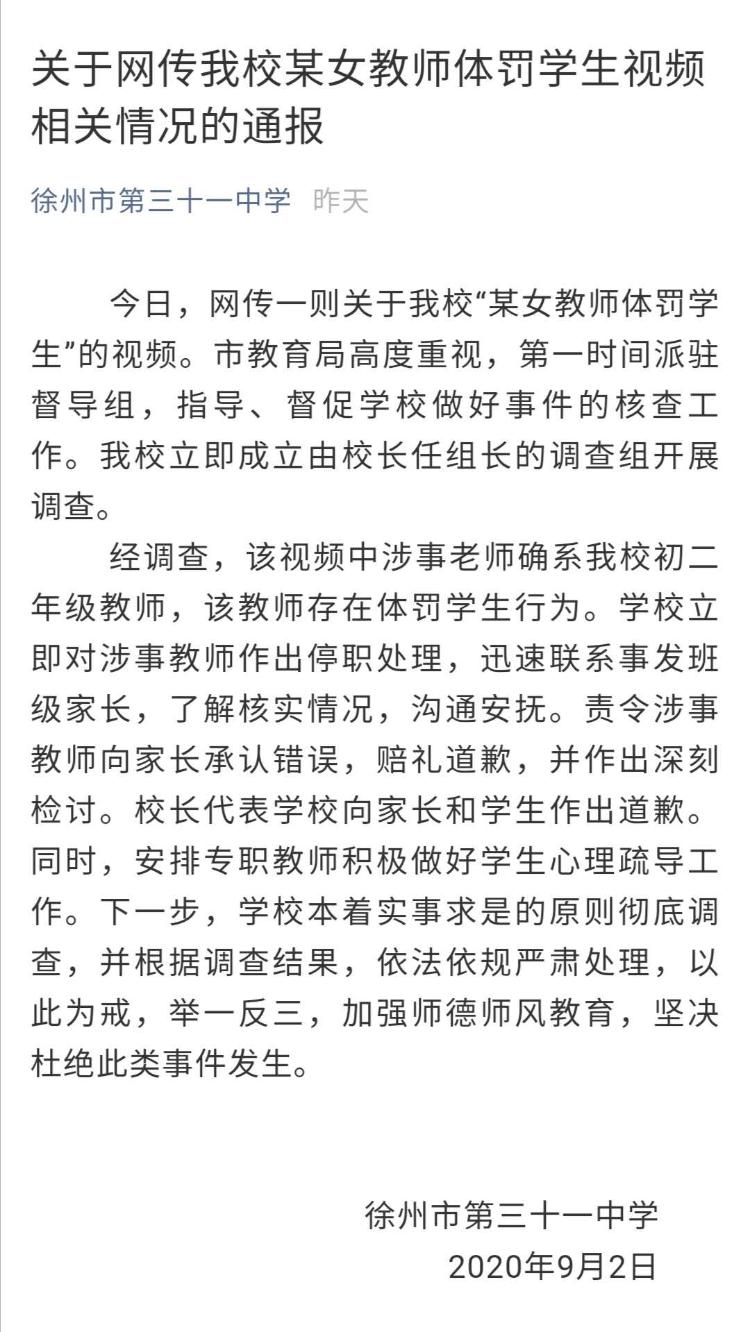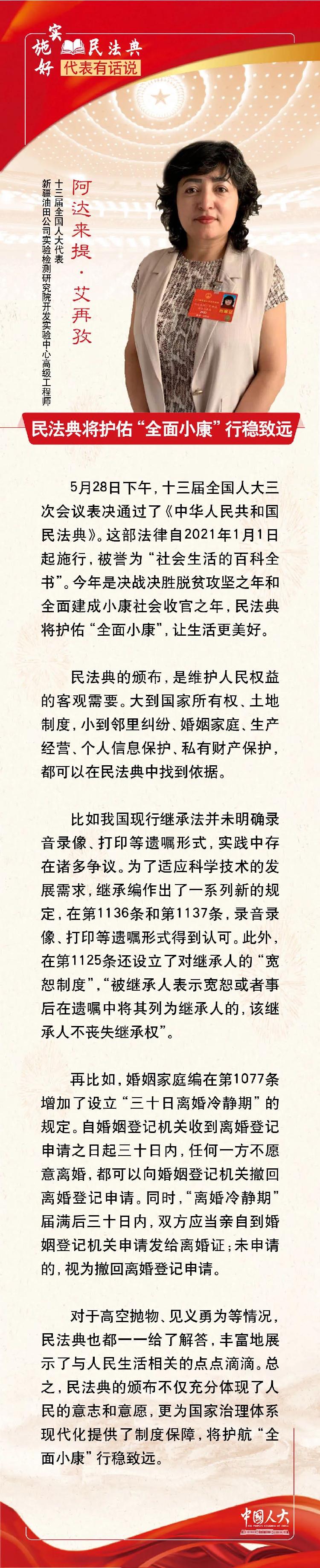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经济政策工作的定调,体现出稳增长与防风险并重的双底线思维。
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三大攻坚战的表述顺序有较大调整,引发市场诸多猜测。有观点将此解读为明年宏观政策稳字当头,金融防风险的紧迫性有所弱化。经过过去两年的金融强监管与去杠杆,我国金融风险由发散状态转为收敛,但这并不意味金融体系的风险隐患已彻底清除,高风险金融机构、地方隐性债务、房地产融资等领域所潜藏的风险仍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需要我们保持高度警惕,以及提前准备好应对预案。
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多年来对金融危机的预警、传染和干预机制有着深入研究,证券时报记者就此专访马骏,听听他对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有何良言善策。
金融风险易传染
建立系统性风险干预机制
证券时报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保持宏观杠杆率的基本稳定,一些观点认为,这意味着去杠杆要让位于经济稳增长,甚至最近也有声音开始反思和质疑去杠杆政策,您如何看待杠杆率指标的作用?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我们该如何平衡稳增长和稳杠杆?
马骏:杠杆率指标具有显著的危机预警能力。近年来,在系统性风险问题上的一个重要争议是,我国杠杆率过快上升这个因素是否实质性地提高了我国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在我牵头的研究团队近期出版的新书《金融危机的预警、传染和政策干预》中,我们用60多个国家20年的数据对影响金融危机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基于我国2017年的宏观指标,如果国内非金融部门信贷/GDP上升1个百分点,我国发生银行危机的概率会提高0.4~0.68个百分点。
证券时报记者:从国外历史上所发生的情况看,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出现往往始于局部风险的暴露,这说明金融风险有着很强的传染性和扩散性,能否介绍下金融风险的传染模式通常有哪些?
马骏:历史上出现的几次大的金融危机,传染都起到了非常大的助推作用。从国外的经验教训看,金融危机至少有三种不同的传导机制:第一种是通过价格传染,也就是资产抛售的传染。例如,一家银行如果因为资本金不足或流动性不足等原因,被迫要卖出一些资产来满足监管指标要求,卖资产的过程中就会压低这些资产的市场价格,相应的,其他持有这些资产的银行就会面临资产价格下降的压力,从而也会导致一些银行出现资本金不足或者是流动性紧张的问题。
第二种是恐慌性的流动性冻结。例如,一家银行出现风险后,其他同类银行往往也会被市场认为会“出事”。为了防范交易对手风险,同业就不借钱给这些被认为会有风险的银行,或者这些银行需要用很高的成本才能在同业市场借到钱,也可能出现储户挤兑这些银行的情况。
第三种传染机制叫做网络效应。
例如,一家银行由于某种原因出现流动性危机,无法按约向第二家银行支付资金,第二家银行因为突然收不到钱,或许也无法向其他银行支付,从而使风险呈网络型扩散。
证券时报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金融监管部门近日也指出要“稳妥处置突出金融风险点”、“稳妥处置高风险金融机构”等。面对潜在的金融风险的威胁,结合国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经验教训,我们应如何进行有效干预?
马骏:经济发展史也是一部金融危机史。历史经验表明,危机过程中有效的政府干预可以帮助降低危机的影响,避免更大规模的传染,而政府“不作为”或“乱作为”则可能严重加剧危机。
我们花了两年的时间研究了五次全球最大金融危机的整个干预过程,通过研究历史上政府对重大危机进行干预的经验教训、金融危机的传染机制,以及中国金融体系的特点,我们对我国如何建立系统性金融风险干预机制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要明确干预的前提,不能无原则干预。如果不是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事件尽可能不要干预,否则会造成更大的风险。当然,如何判断它是不是系统性金融风险还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在危机尚未爆发前,政府监管部门应当积极处置道德风险问题,严格执行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纪律,这将有助于缓解危机中由于权衡道德风险问题而难以果断决策干预的困境。
二是建立金融风险预警等级体系和分级响应干预机制。中国地域广阔,不可能完全靠中央政府、“一行两会”进行金融风险的识别和干预,地方政府层面也要发挥自己管理、干预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职责,构建地方层面化解区域性金融风险的机制。例如,为了有效应对由于地方隐性债务可能导致的风险,应该尽快打通同一地区政府平台的资产负债表,让资不抵债的部分平台在本级政府层面通过与有可变现资产的其他平台整合来予以化解,而对市政府无法在本级消化的平台负债必须尽快安排其与省级平台整合。
三是提前备好干预“菜单”、可能有必要接受干预的机构名单和干预问题机构的流程,以防一旦出事后手忙脚乱。
四是准备好判断最优干预力度的方法。央行或政府背景的平准基金可能在极端情况下需要通过干预市场来稳定资产价格,但要避免政策干预明显用力过度,这可能导致对纳税人资金的浪费、或过早消耗了有限的“子弹”;也要避免不断出台力度过小、对市场没有作用的干预措施,连续、无效的干预会让政府丧失市场可信度,使得未来的干预更加困难。
化解地方隐性债务风险
平台公司可兼并重组
证券时报记者:近年来,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持续备受关注,城投平台公司庞大的存量债务也被市场担心会潜藏较大风险,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马骏:地方政府有大量的隐性债务。根据多个学者的调研、估算,我国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可能高达显性债务的几倍。我国一些地区的平台类机构债务率高企、期限严重错配,长期依靠借新还旧来维持运行,部分平台已经开始要求银行展期。在经济下行、房地产价格预期持续低迷或下降的背景下,许多过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作为还债重要资金来源的地方平台类机构违约风险会加大。
在全国上万个平台类机构中,只要几个公开违约,就可能导致连锁反应形成“扎堆”。因此,应尽快制定系统性防范和化解地方隐性债务风险的措施,有效防止出现一批平台违约倒闭的系统性风险。
证券时报记者:对于制定系统性防范和化解地方隐性债务风险的措施,您有何意见和建议?
马骏:从我们调研的情况看,对于债务化解风险压力较大的地区,建议可以考虑支持省市内一部分优质平台兼并重组其他平台,优化存量负债结构。从宏观层面来讲,通过支持省市内一部分优质平台兼并重组其他平台等平台整合的措施,将债务重新配置到财务状况更为健康的负债主体,有助于提升整合后主体的财务指标、负债结构及信用评级。
通过这类平台整合,一方面可降低未来几年内全国范围内爆发地方平台违约的概率,为后续优化体制机制系统解决地方隐性债务问题赢得时间;另一方面,由于清理了大量体量小、不规范、不透明的平台,也可缓解未来小平台负债增量的问题,有效控制债务规模的持续增长。目前部分省份的一些地级市已开始通过整合地方平台试图防范和化解平台风险,并取得了一些可复制的经验。比如,有的地级市将二十几家平台整合成三个平台;整合之后的平台可以做到资产覆盖负债,现金流覆盖利息支出,信用评级提高,融资成本明显下降。
从实施层面来看,由于多数平台为地方政府全资拥有的机构,整合过程只要市领导全力推动,过程并不十分复杂,一般几个月到一年时间内便可完成;原来独立公司多数变为新集团公司的子公司,人员安置方面也没有太大阻力;在投资银行和专业机构的指导之下,进行尽职调查、新投资者引入和新资产注入,总体都比较顺利。此外,地方政府利用整合的机会进行系统梳理,有效提升了整合后平台的专业化水平和规范化运作能力。因此,建议有关部门在成功案例的基础上,出台鼓励地方平台整合的指导意见,争取在债务风险较大的省区引导一批市、区、县级平台进行整合(包括合并、注销和转型),有效降低未来几年由于借债主体规模过小和质量太差导致的违约风险。
除了省市内的平台可以考虑兼并重组外,还应鼓励优质平台企业跨地域兼并高风险地区的平台公司。由于发展程度不同,我国不同地区的政府财力和融资平台财务实力、运行能力存在较大的差别,在我国目前基本“每个地方只负责本地基础设施建设”的体制下,实力较强地区的平台能力没有被充分利用化解中西部地区债务风险,满足其投资需求。建议建立体制机制打破现有的投资格局,鼓励部分优质平台企业跨地域兼并高风险地区的平台公司。
此外,还可以支持一部分优质平台进行上市或收购部分上市公司及其他资本运作,充分盘活国有资产。在目前二级市场低迷的环境下,存在大量被市场低估的优质上市公司,为地方平台资产及结构调整提供了有利契机,应支持一部分优质地区平台公司进行借壳上市或收购部分上市公司,作为地方平台公司进行资产结构调整及提升融资能力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