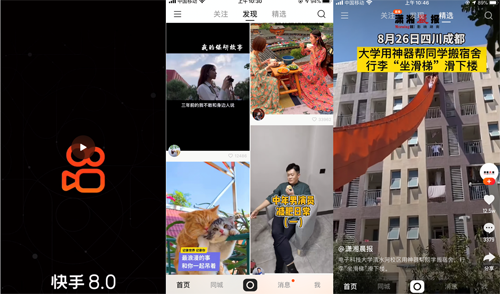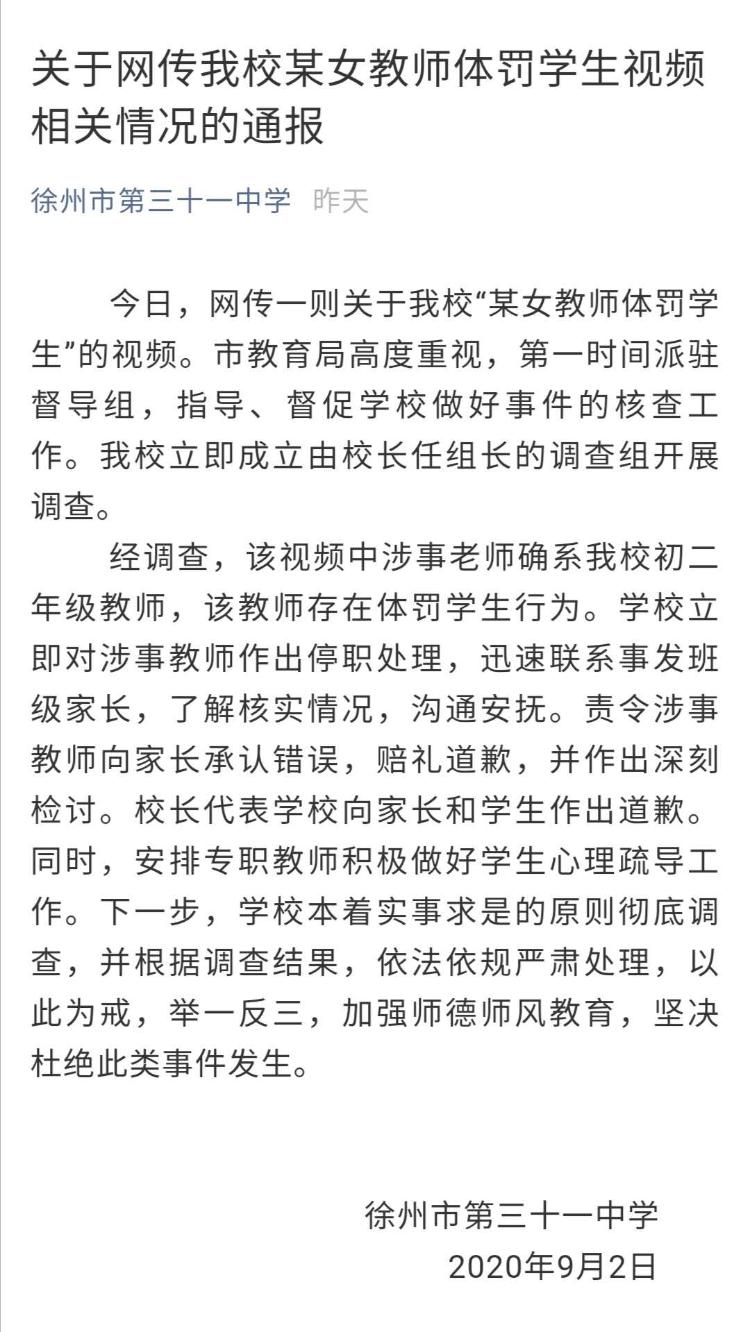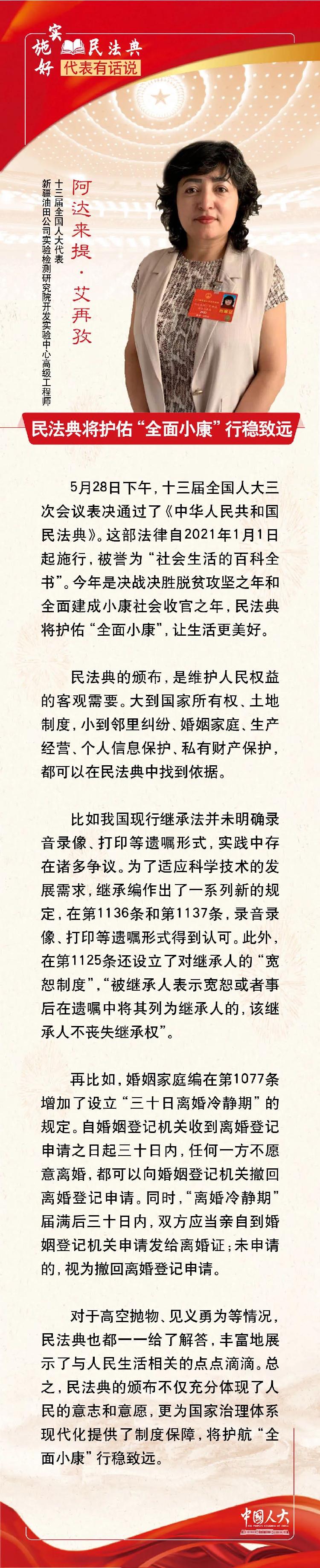在银行理财产品销售领域,纠纷较为常见。但走过三轮审判的案例就不多见,而且三次审判的判决结果迥然不同。
判决结果不同的关键,实际上在于银行与投资者的法律关系认定、权责划分。
改判的背后,涉及投资者适当性义务的相关法规逐渐完善过程。从判决书中看不到“投资者适当性”等表述,到“是否履行适当性义务”成为辩论核心。
双方属何种法律关系
“再审(即三审,下同)的结果更多是在二审基础上,进一步明晰双方权责。”有律师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在他看来,整个案件的关键在于一审、二审中,法院对投资者、代销银行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只是代销的法律关系,二审法院则认定双方为金融服务的法律关系,两种不同法律关系,导致两次判决结果完全逆转。”
判决书显示,银行在就案件进行应诉、提起再审时,均主张自己只是基金管理人的代理人,与胡某(即上述纠纷案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之间从未达成任何书面或者口头形式的理财顾问服务协议,双方是基于代销法律关系而形成的代理人与相对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代销法律关系下,银行对投资者的决策没有影响,而且只有合理告知或风险提示的义务。也因此,一审法院认为银行已经尽到了合理的风险告知义务,判投资者败诉。”前述律师称。
而二审法院参照《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下称《办法》)对“理财顾问服务”的定义,认为胡某的购买决定依赖于银行提供的理财产品信息,银行也为胡某提供了资金划转服务,认定双方为金融服务法律关系。
“与代销法律关系不同,金融服务法律关系下,银行的服务和投资者的购买行为是有因果关系的,银行除了要做风险提示,也要承担适当推介义务。”前述律师称。
再审法院也认可二审法院对双方法律关系的认定结果,并根据胡某是新三板投资者,又在2015年从事大额股权投资等行为,确认胡某应系具备一定经验的金融投资者,最终判决胡某自担60%损失责任。
“适当性义务”
相关法规逐渐完善
三审三判背后,也是涉及投资者适当性义务相关法规完善的过程。
据了解,在早期,由于相关规范性文件并不完善,法院考量金融机构是否存在过错,主要偏重于风险提示义务方面,适当性匹配义务并没有被视作一项必要因素考量,金融机构也往往把抗辩和举证的重心放在风险提示是否完全履行上。
因此,当时类似的金融消费纠纷往往以投资者的败诉而告终。“最关键的原因是,与投资者相比,银行的证据充足和完备性明显更高。”有律师表示。
而二审法院对此案的判决之所以被外界广泛关注,除了对双方法律关系的认定扭转外,还在于法律适用的变化。
判决书显示,二审法院对双方关系的认定主要基于《办法》,对于“适当性义务”的解释也源自《办法》、《个人理财业务风险管理指引》,并据此认定银行没有履行正确评估及适当推介义务。
二审法院认为,虽然相关监管部门的规章并非法律法规,法律层级比较低,但其中涉及“适当性义务”的解释是民法中平等原则及合同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体现,在相关法律法规还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应当据此认定银行的权利和义务。
到再审判决时,法律法规完善度已经截然不同。一方面,早在2016年底,证监会就公布了《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统一了此前散落于各规范中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强化了金融机构的适当性义务,明确了金融机构违反适当性义务的法律责任。
此后,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匹配的讨论明显增多,投资者以此为抓手主张违反适当性义务的责任承担纠纷也呈上升趋势。
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又在今年7月就《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征求意见稿)》(下称《纪要》)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经过4个月的征求意见,已于上周正式发布。
《纪要》强调,卖方机构在向金融消费者推介销售时负有适当性义务,如果未尽适当性义务导致金融消费者遭受损失的,应赔偿金融消费者的实际损失。
此外,《纪要》明确指出,金融监管部门颁布的规章与法律和国务院发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相抵触的,可以被法院引用作为审判依据。
虽然《纪要》并非法律法规,也非司法解释,不能直接引用于案件审判,但法院审判在具体分析法律适用的理由时,可以根据《纪要》的相关规定进行说理。外界广泛认为,这将对现有金融纠纷案件审判造成重大影响。